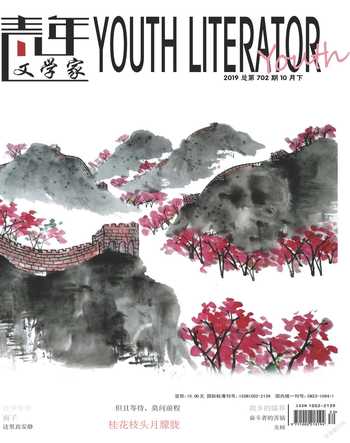從晚清竹枝詞看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
摘? 要: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入侵,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也開始傳入中國。西方近代文明最初是在租界投入使用的,但隨著租界的影響,西方近代文明也逐步向內地滲透,進而對晚清民眾的生產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晚清竹枝詞記錄了西方近代文明在當地百姓生活中產生影響的生動畫卷,也從側面見證了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國的傳播。
關鍵詞:竹枝詞;近代文明;傳播
作者簡介:郜衛博(1984-),男,山東菏澤人,中共貴州省委黨校黨史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30-0-03
一、租界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后,晚清政府作為戰敗國被迫和英國簽訂條約,并開放一批口岸與外國通商。自此以后,西方人和商船紛至沓來。在一些通商口岸,為了方便西方人的通商和居住,西方列強又強行開辟了一些租界,此為西方列強在中國開辟租界之始。租界的存在是對中國主權的挑戰,也嚴重損害了中國人的尊嚴。但租界的存在既影響了中國早期的近代化進程,同時又成為西方近代文明的轉播與擴散地。
以上海為例,鴉片戰爭后,英、美、法等列強先后在上海縣城以北的地方劃定了專供西方人居住的租界區,后來又多次擴展。上海由原來一個不起眼的江邊小鎮成長為近代大都市的過程與西方列強開辟的租界有著密切的關系,是租界的存在加快了上海的近代化過程。如佚名的《春申浦竹枝詞》所言:
春申浦繞滬江城,浦上潮來晝夜聲。試望洋樓高聳處,花旗飄拂晚云明。
北門城外本荒丘,古樹蒼涼一望收。真是桑田滄海變,荊蓁掃盡起高樓。
荒墳平后作夷房,玉碗金魚盡發藏。殘骨不知拋何處,只留翁仲泣斜陽。[1]
第一首作者于題下注云:春申浦,昔楚相春申君黃歇所封之地,故名。又有黃歇浦、滬江等名,夷人所居。花旗,英國名。由整首詩來看,此詩所描寫的地方當為上海城北,是歷史上有名的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封地,故此地以春申君的名字命名。誰曾想千年之后,歷經滄桑的此地到處洋樓高聳,花旗招展,成為英國的租界。第二首作者于題下注云:上海北門外本屬荒蕪,夷人通商后,市漸云集。這首詩敘述租界的開辟與上海城市崛起的緣由。上海城北租界開辟前本是一片荒丘,放眼望去盡是古樹蒼涼的景象,然自與夷人通商后,此處荒地發生了滄桑巨變,西方人在此地掃盡荊蓁,建立了供其居住的租界。第三首作者于題下注云:夷人通商后,墳冢悉為平去,大馬路西有一大冢,掘有石槨,尸僵不腐,服古衣冠,不知何代貴官也,亦無墓志。夷人掃去,上造洋房,留翁仲為門柱,尚存。這首詩是講述西方人建立租界的經過,在原來的荒墳地基之上建造樓房,把原來的荒丘墳地改造成為頗具現代城市雛形的租界,從而對上海商業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
西方人建立租界的目的是為了通過與晚清中國的貿易而獲得更大的利益,但自從與洋人通商后,上海的市場也逐漸活躍起來,正所謂“市漸云集”,如一位1873年滬游上海的旅客記錄下了對租界的感受:“洋人租界地方,熙來攘往,擊轂摩肩,商賈如云,繁盛甲于他處。”[2]上海由開埠前一個不起眼的小城鎮逐漸蛻變成遠近聞名的近代商業城市,租界商業繁盛的推動作用功不可沒。如下面這兩首竹枝詞所言:
新關樓閣益崔巍,圣主當年賦稅開。一自通商恩準后,絲商茶客似云來。[3]
自開海禁五洲通,水陸舟車疾似風。百貨遍流全世界,商家發達正無窮。[4]
鴉片戰爭后,晚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五口通商的條約,西方人為了其通商的便利,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促進了當地商業的發展,而“一自通商恩準后,絲商茶客似云來”一句描述了當時通商口岸的商業繁榮景象。不但內地貨物可以通過通商口岸銷往國外,而西方商品也隨著近代水陸舟車的便利可以遍流全世界,無數商家通過與西方的貿易交往日益發達起來,為上海商業城市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因此,西方租界的存在對上海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大都市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進而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歷程。
西方人在近代中國開辟租界以后,除了在租界維持其享有的特殊權利之外,同時也將西方近代文明帶進了租界,使租界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地,因此,租界也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縮影。租界的存在不但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完整,也給當時的百姓造成了很深的心靈創傷。但不可否認租界對當時的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如費成康所言:“通過迫使清政府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列強取得在中國的10多個通商口岸開辟租界的特權。后來部分租界未被開辟,真正出現租界的口埠共為10個。在這10個口埠中,上海、天津、漢口、廈門4口的租界較為發達,對當地直至附近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5]通過租界的傳播作用,西方的一些近代文明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加快了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進程,對晚清民眾的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二、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
租界是晚清中西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民眾通過對租界的觀察與了解,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通過中西社會的對比,從而發現晚清社會的落后之處。晚清竹枝詞則記錄了當時租界內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晚清社會帶來的變化。辰橋在《申江百詠》中便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影響做了詳細的描繪,如:
火樹千株照水明,終宵如在月行中。地埋鐵管通街市,真個銷魂不夜城。
注云:地火皆由鐵管通至馬路,于是各戲館及酒樓、茶肆俱可接點。其燈每盞有玻罩,或倒懸,或直豎,或向壁上橫穿,各隨所便。人行其間。真如入不夜城也。
天際無端獻玉盤,雨中猶見月團團。萬家燈火無顏色,疑是明皇入廣寒。
注云:又有電氣燈,一名自來月,高與樓齊,一燈可照百步,其光如中秋月。自此燈作而地火又黯然無色矣。[6]
這兩首詩是對當時上海租界地區安設路燈景象的描述,作者將路燈照耀的街市比喻為皓月當空的不夜城,“不夜城”這一稱號也成為上海的一個標簽,可見其對當時百姓夜間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時也豐富了百姓的夜間娛樂生活。租界內由最初的地火演變為后來的電氣燈,體現了當時的技術革新,同樣這一技術創新的基礎設施也為人們在夜間的出行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黃浦塵埃滾浪頭,幾回淘汰化清流。黑龍倒吸滬江水,能使高漂最上樓。
滬江水濁,西人乃設局于下海浦高池數區,以鐵絲網篩隔之,水皆澄清,而租界中亦如地火之法用鐵管通接。水本下流,聚既多則逆激而上,雖三層樓亦可取用也。[7]
不須鯉寄與鴻傳,電線音馳萬里天。領地語言傳頃刻,勝于羽箭疾離弦。[8]
這兩首詩分別講述的是租界內飲用自來水及電線基礎設施的應用,通過過濾滬江的濁水而一化為清流之水,提高了用水效率,用鐵管接通可以將水直接送到三層樓之上,是現代自來水管的鼻祖。而電線則改變了中國自古以來的通信方式,正如一位游滬旅客對電線的描述所言:“電氣何有達,天機不易參。縱橫萬里接,消息一時諳。竟竊雷霆力,惟將 線索探。從今通尺素,不籍鯉魚函。”[9]以前國人通信的方式或是通過官方的驛站或是委托朋友捎信,有時要等上幾個月,但自從電線架起以后,雖間隔萬里,可瞬息傳遞,從而提高了通信的效率。
仰觀天象近蘭臺,堅筑巍巍百丈臺。更有輕靈鉛筆在,先期三日報風來。
西人于徐家匯筑天文臺,高入云漢。上有鉛筆一枝,自能書寫,如某日某洋有大風,三日前可預知,舟行何處即可飛電傳報。
窮源窮理豈無窮,格致能參造化工。要識會心原不遠,長消祗在五行中。
西人興格致書院,每月出書一本,曰《格致匯編》。大都講五行之消長,雖極幽眇,必得其理而后止,用心亦可謂勤矣。[10]
這兩首竹枝詞是對西方人天文及格致之學情況的描述。第一首講述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預測天氣的方法,能提前預知幾天后的天氣狀況,較之我國古代的仰觀天象的方式更為精確,是現代天氣預報的發端。第二首是對西方學術輸入中國現象的描述,王韜曾與友人的書信中談到格致書院的性質:“近以滬上中董事公舉,承乏格致書院,忝居掌院。擬廣招生童,前來肄業,延請中西教讀,訓以西國語言文字;學業有成,則視其質性所近,授以格致機器象緯輿圖制造建筑電氣化學,務期有益于時,有益于時,為國家預儲人才,以備將來驅策。” [11]由此可知,格致書院是由中西人士合辦旨在培養西學人才的新式書院,所學科目為格致、機器、象緯、輿圖、制造、建筑、電氣、化學等,完全有別于中國傳統書院的科目,旨在培養興辦洋務所需的各類人才,格致書院的創辦對于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影響深遠,同時也培養了一批近代所需的各類實學人才。
英法租界最清潔,掃凈街衢信認真。好個章程工部局,馬車過處灑飛塵。
英法租界有工部局,專管街道灑掃等事。每日兩次,于各馬路用馬車載水,車后有機器,隨過隨灑,如落細雨,則一塵不飛矣。
倏聽高樓報警鐘,捕頭齊涌似狂蜂。祝融雖虐也銷勢,萬丈皮條欲化龍。
西人救火最出力。如遇火警,捕房先擊警鐘,以聲數分地段,于是捕頭擁水龍出,其龍皆皮條為之,雖水遠 可接也,更有滅火藥水,藥水過處火即立熄。[12]
無分夜雨與朝晴,短棍持來踽踽行。切莫墻邊私出溺,被他拖去□□情。
巡察街巷之夷人曰巡捕,每遇爭斗及在街上小便者,便被拖至巡捕房,問明始放。[13]
這三首竹枝詞分別提及西方工部局、沿街巡捕以及火警的設置與職能。西方人工部局的設立旨在維護街道干凈,并用噴水設施沿街灑水,對于維護公共環境的衛生十分重要,有利于人們的身心健康,類似于今天的環保局。而沿街巡捕的功能則在于維護交通及公共秩序,晚清社會受其影響,后來建立了仿西方巡捕的警察體制,對于指揮交通及維護公共秩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人的救火制度及設施也同樣被普遍引進中國的大中城市,對于防止火災及維護人們的財產安全起了重要的預防作用。
欲聞西國有盧醫,聽肺揺腸事總奇。偶爾此間窮藥石,不妨一割釋猜疑。
泰西醫生有聽肺管,病在何處必先聽肺,亦如中國按脈也。又有揺腸皮條,如急救生鴉片,即用皮條數揺,黑水出自愈。如或有醫而不效,必將死人隔開細閱,使后不至復誤。
市井爭開拍賣風,宜今宜古各流通。好將壟斷翻新樣,不在區區劃一中。
洋行中貨物多拍賣。拍賣者,貨物雜陳,一西人朝外立,手持鐵錘,聽人估值。如一人估值最昂,后無人再估重價,鐵錘一拍即售之去,故脫貨較易。
廣采新聞播遠方,謄清起草倍倉皇。一年三百六旬日,日日千言錄報章。
自壬申年申報館開設后,繼起者有滬報、匯報、匯報、萬國公報、字林報、晉源報、文匯報等館,皆廣采新聞流傳中外。[14]
第一首竹枝詞是對西醫在中國興起的描述,中國傳統醫術是通過把脈來診斷病人的病情,而西醫則通過聽肺管來窺探病人的病情,西人聽肺管為國人所未見,又有揺腸皮條,可將病人所食生鴉片之類的事物搖出體外,因國人對西醫又了解甚少,故將西醫稱作盧醫,對聽肺揺腸之事總感覺好奇。如遇醫而不效的病人又對其進行人體解剖,一探究竟,為日后醫此類病人積累經驗。中西醫術有別,西醫的傳入對于醫治中醫不能解決的外科病癥起了重要的互補作用。如《上海新報》曾報道:“上海傳教士1865年在虹口設立了同仁醫院,在初設的一年之內,共醫治病人男性6370人,女性9478人,另有外國人76人,總共醫治人說數為15924人。” [15]第二首竹枝詞是講述西方的拍賣行業在中國的興盛狀況,拍賣行業的興起促進了貨物的流通,從而保證了貨物客觀公正的交易,對于推動近代商業的興起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第三首是講述西方報刊業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如對中國近代社會影響深遠的《申報》,最初是由英商美查等人創辦。在其創刊號發表的《本館告白》中曾闡述了其辦報宗旨云:
新聞紙之制創自西人,傳于中土,向見香港唐字新聞體例甚善,今仿其意設《申報》于上洋。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務求其真實無妄,使觀者明白易曉,不為浮夸之辭,不述荒唐之語。庶幾留心時務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謀生理者于一此 亦不至受 其欺。此新聞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16]
《申報》所涵蓋的內容極其廣泛,上至國家之政治、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下至風俗之變遷以及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正所謂“廣采新聞播遠方。”晚清新聞紙出現之前的社會,信息的傳播主要靠人們之間的口耳相傳,流傳途徑與速度都過于單一,不時有虛假信息。然自《申報》等各類報刊出現后,“日日千言錄報章”,信息的傳播非常及時,對社會各色人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無論留心時務者還是外出謀生者都能有所裨益,故新聞紙對于促進晚清社會邁入近代化起到重要的輿論推動作用。
蠅頭細字看分明,萬卷圖書立印成。若使始皇今復出,欲燒頑石亦經營。
石印書局以同文館點石齋為佳。其法將每頁書用藥水于石上印過,宛然成書板矣,故雖《圖書集成》、《廿四史》、《佩文韻府》等書,亦易開印。[17]
點石齋石印書局最早由英商所辦,“石印書籍以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局為最先。該局為英人美查所設。美查初與其兄弟販賣華茶,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后因所業失敗,思欲改圖。其買辦贛人陳華庚見上海報紙之暢銷,乃以辦報之說進,并介其同鄉吳子讓為主筆。美查贊同其議,乃延錢昕伯赴香港調查報業情形,以資仿效。時日報初興,競爭者少,其兄所營茶業亦大轉機,故美查歷年經營頗有所得,于是先后添設副業。點石齋石印書局即其一也。”[18]前者所辦報業為《申報》。石印書局采用西方先進的印刷技術,提高了印刷的質量與速度,正所謂“蠅頭細字看分明,萬卷圖書立印成”,這種石印技術的傳入,促進了中國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
每逢七日例停工,任爾閑游租界中。卻是歸仁來復候,如何沉醉入花叢。
西人每七日中例停工一日,耶穌教曰禮拜,天主教曰主日,凡西署洋行及一切上下人等均專事游玩。[19]
這首竹枝詞講述西方人的工作休息制度,于一周中休息一日,雖然這一制度最初源于西方的宗教信仰,但這種勞逸結合的工作體制符合人類勞逸結合的生活習慣,因此,后來成為全世界通行的工作休息制度。
三、余論
以上從多個方面描述了西方近代文明被引進租界的情況,像物質層面的路燈、電線、自來水等;以及對公共秩序的維護起重要作用的巡捕與工部局制度;直到影響民眾精神文化層面的石印書局、《申報》等。租界內西方人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來設計自己生活的,基本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中國本土的縮影。晚清國人在親眼目睹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優越,以及反觀中國傳統文明的落差之后,積極引進西方近代文明來改變晚清的積弱積貧面貌,從這一點來說,租界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擴散基地,通過租界這一窗口,把西方先進的近代文明引進到全國大中城市,對晚清的民眾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釋:
[1]佚名:《春申浦竹枝詞》,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頁。
[2]黃浦江頭冷眼人:《論洋涇浜小本經紀 宜體恤事》,《申報》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初七日,公歷1873年2月4日。
[3]佚名:《春申浦竹枝詞》,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54頁。
[4]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光緒32年 版,第1頁。
[5]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頁。
[6]辰橋:《申江百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79—80頁。
[7]辰橋:《申江百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80頁。
[8]李默庵:《申江雜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75頁。
[9]葛元煦著,鄭祖安標點:《滬游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頁。
[10]辰橋:《申江百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80頁。
[11]王韜著;汪北平,劉林編校:《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37頁。
[12]辰橋:《申江百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81頁。
[13]佚名:《春申浦竹枝詞》,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49頁。
[14]辰橋:《申江百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82頁。
[15]《上海新報》1866年12月29日,轉引自劉志琴等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卷一,第218—219頁。
[16]《申報》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三日,公歷1872年4月30日。
[17]辰橋:《申江百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82頁。
[18]張靜廬輯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上海: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270頁。
[19]辰橋:《申江百詠》,見顧炳權:《上海洋場竹枝詞》,第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