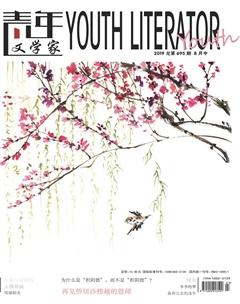沈從文《燈》的敘事特點
王櫻城
摘? 要:沈從文短篇小說《燈》采用了嵌套的敘事方法,一個燈的線索貫穿全文,兩個敘事文本進行對照,小說整體呈現(xiàn)出反烏托邦的敘事特點。作者在引導(dǎo)讀者充分認可敘事真實的同時,反過來強化小說的虛構(gòu)意義,特殊的敘事策略形成了小說敘事的藝術(shù)張力,顯現(xiàn)了很自覺的現(xiàn)代小說意識。
關(guān)鍵詞:敘事;嵌套;反烏托邦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3-0-01
這是一篇真實情感與虛構(gòu)敘事交織的小說,屋子的主人“我”可以被理解為沈從文的發(fā)言人,讀者能與講故事的人一起參與到故事中,分享感受話語氛圍。小說中,作者介紹了“我”與一個家鄉(xiāng)軍人在特別情況下生活在一起的一段經(jīng)歷。小說中的“燈”既是不自覺的文化意象的暗示,又是全文的線索。小說的結(jié)構(gòu)以一盞舊式煤油燈貫穿敘事的首尾,圍繞“燈”的敘述形成非常舒緩的回憶情調(diào),憑借對老兵的經(jīng)歷以及與自己家庭的親密關(guān)系的介紹,將家族的變遷和時代的動蕩,和對過往的種種感慨融合在一個的敘事結(jié)構(gòu)中。
小說刻意制造了一個嵌套的敘事手法。它的嵌套結(jié)構(gòu)不是可有可無的,其本身就是小說意旨的一部分。以老兵的故事和“我”與青衣女人的對話兩個敘事文本的對照,結(jié)局以對“燈”的來歷以及是否真的有這樣一個人物的追問,借助敘述者之口主動消解了主敘述層大部分文字所敘述的真實性,將小說引入真假難辨的無窮遠處,使過去與現(xiàn)代、鄉(xiāng)村與城市、老兵和現(xiàn)代都市人之間產(chǎn)生了微妙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當(dāng)沈從文強調(diào)自己在寫故事的時候,他所強的并不是故事的真實性,而恰恰是借虛構(gòu)的故事和遙遠的過去來征服都市讀者。”[1]沈從文在《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丈夫》等小說中都采用了和《燈》類似的嵌套敘述模式,比如在《丈夫》中也出現(xiàn)了與“燈”這一意象功能相似的“小鐮刀”,“小鐮刀”指代的妻子在主體敘事和嵌套敘事中均有出現(xiàn),卻在不同時空下展示了鄉(xiāng)村與城市的兩種光景,使嵌套的敘事文本更顯真實;在《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末尾,作者也承認了故事的虛構(gòu)性。這些故事最終的目的仍舊是為了要說服讀者相信這個“故事”,正如《說故事人的故事》題目所反映出的敘事手法——“故事里的人講故事”。作者在小說敘述引導(dǎo)讀者充分認可敘事真實的時候,反過來強化小說應(yīng)該具有的虛構(gòu)意義,特殊的敘事策略形成了小說敘事的藝術(shù)張力,顯現(xiàn)了很自覺的現(xiàn)代小說意識。由此,有關(guān)小說真實性與虛構(gòu)性如何辯證共生的問題再度引發(fā)論者思考,這也體現(xiàn)了作品自身的敘述魅力。
沈從文在《湘西散記》中寫到 “我已來到我故事中的空氣里了,我有點兒癡。環(huán)境空氣,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實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凡烏托邦敘事總是關(guān)于幸福生活的敘事,而小說整體呈現(xiàn)出反烏托邦敘事的特點,背后是作者對人際關(guān)系和道德秩序的呼喚。小說既通過常見的烏托邦敘事來堅持傳統(tǒng)的烏托邦精神,又以此去反對所有現(xiàn)實化的越界的烏托邦行動。顯然烏托邦不能被現(xiàn)實化,但烏托邦敘事卻又絕對是必須存在的。[2]在這篇文章中烏托邦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首先,老兵身上所具有的舊式鄉(xiāng)村美好人格特性成為沈從文心中的理想烏托邦品格,但這些品格只存在于美好淳樸的過去和鄉(xiāng)村中,在現(xiàn)代都市中難以尋覓;其次,老兵企圖把自己的榮耀和幸福建立在“我”身上也成為一個不能被實現(xiàn)的烏托邦想法。如果不能在人際交往中保持自身的獨立,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他人上,也會造成人際關(guān)系的疏離,使老兵離“我”而去成為必然。
老兵是一個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都市社會里的具有古典風(fēng)度的軍人形象。[3]他對日新月異地現(xiàn)代社會充滿陌生感,觀念仍舊停留在過去封建宗法制社會中。他身著舊式軍裝,進房門喊報告保持軍人做派,感慨油燈在現(xiàn)在社會的消失,對大學(xué)生畢業(yè)后不去做縣長和知事老爺感到不解……他單純、正直、善良、熱情、忠誠,為人處事都具有鄉(xiāng)下人的原始質(zhì)樸氣息和健全的人性。他抱著舊軍人滿腦子的夢想,按“麻衣相法”揣度什么樣的女人適合做“我”太太,并沉浸在過去的光榮時代里,企圖把中興一個軍人世家的榮譽寄托在我“身上”……當(dāng)老兵的主觀精神和客觀現(xiàn)實世界產(chǎn)生沖突時,種種夢想破滅,老兵選擇了一去不返的逃避,他無力承受現(xiàn)實,只好失望出走,逃避到自己熟悉的舊日生活中去。整個關(guān)于老兵的故事體現(xiàn)了老兵身上殘留的逐漸消逝的舊時代美好精神品質(zhì)珍貴和作者的惋惜,表達了作者對舊式理想人格的推崇、傷逝和對現(xiàn)代都市蒼白生命的精神關(guān)照。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里一貫從整體性中顯示出鄉(xiāng)村世界與都市人生相互對立又互為參照的敘事構(gòu)型,道德狀態(tài)與人格氣質(zhì)上鄉(xiāng)村優(yōu)于都市、下等人勝于上等人也表現(xiàn)出鮮明的反世俗價值取向,體現(xiàn)沈從文根植于鄉(xiāng)土的鮮明民族品格和現(xiàn)代生存方式的思考。
參考文獻:
[1]吳曉東.從“故事”到“小說”——沈從文的敘事歷程[J].長沙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1,26(02):82-89.
[2]王鴻生.反烏托邦的烏托邦敘事——讀《受活》[J].當(dāng)代作家評論,2004(02):89-98.
[3]宋秋盛.人生的困境與存在的荒謬——沈從文小說《會明》、《燈》、《新與舊》主人公的分析[J].湖南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4,6(04):15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