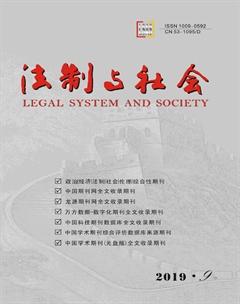淺談被遺忘權(quán)
摘 要 目前在互聯(lián)網(wǎng)應(yīng)用發(fā)展大好的勢頭下,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和加強相應(yīng)的規(guī)則,強化個人數(shù)據(jù)保護。其中以歐盟于2018年頒布的《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為例。刪除權(quán)(被遺忘權(quán))也因此進入人們的視野。
關(guān)鍵詞 互聯(lián)網(wǎng) “刪除權(quán)” 個人信息
作者簡介:阮夢雅,上海政法學(xué)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學(xué)。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biāo)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237
一、 有關(guān)信息權(quán)利保護的疑問
著名編輯拉希卡曾提到,銘記代替遺忘,將人類的過去如同紋身一般刻在了數(shù)據(jù)皮膚上。人類實在花了太多力氣去克服遺忘,數(shù)字時代的到來似乎讓問題得到了完美的解決。既然一直以來追求的目標(biāo)都已達成,還談什么被遺忘的權(quán)利?下面我將舉兩個例子:
1.教師史黛西·施耐德在社交軟件上上傳了一張手拿酒杯、頭戴海盜帽的醉酒照片,而被校方以“行為與職業(yè)形象不符合”的理由取消了教師資格。
2.費爾德瑪在通過美國邊境時,邊境士兵利用網(wǎng)絡(luò)搜索到他曾服用致幻劑的相關(guān)文章,拒絕其再進入美國境內(nèi)。費爾德瑪承認自己當(dāng)年服用致幻劑的確觸犯了法律,但以為那段蒙上塵土的過去是與現(xiàn)在的自己再無關(guān)聯(lián)的過錯。年過70的他絕不會想到,40年前的文章如今會成為責(zé)難自己的證據(jù)。他說:“這像是一場可怕的突襲。”
對此或許你會有這樣的思考:我們都知道不要沉浸于過去的道理,既然有向前看的心情,為何不能擁有擦去那些不需要的、陳舊記憶的機會?隨著技術(shù)的革新,數(shù)據(jù)與利益劃上等號,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對此趨之若鶩——盡可能的收集與挖掘個人數(shù)據(jù),期待從中得到巨額利益,而至侵權(quán)處罰于不顧。
2013年斯諾登違背保密協(xié)議向大眾揭露了國家安全局的棱鏡計劃。他表示只因撥錯一次電話,就能以項目名義懷疑你甚至調(diào)查有關(guān)你的一切。只要連上網(wǎng)絡(luò),你便無法保護自己。避開事件的升溫、發(fā)酵以及各國的反映,單單是事件本身就讓人感到窒息。
這讓筆者想起了邊沁于1785年提出的圓形監(jiān)獄。觀察者能夠通過位于監(jiān)獄中心的瞭望臺觀察罪犯的一舉一動,并憑借巧妙的設(shè)計讓罪犯無法察覺,從心理上讓其感覺時刻處于監(jiān)視中,進而不敢輕舉妄動。
現(xiàn)實中不是囚犯的我們因網(wǎng)絡(luò)而被迫與屏幕那端的“中央塔樓”聯(lián)系起來。身處高樓大廈之中,以為那層鋼筋水泥足以抵擋一切目光,殊不知數(shù)據(jù)共享早已綁住了我們的手腳,無時無刻不在“監(jiān)視”著我們。就此,對于“我能否在數(shù)據(jù)時代擁有被遺忘權(quán)利”的疑問也被提上了日程。
二、被遺忘權(quán)的歷史沿革
(一)大眾媒體時代“被遺忘”的意識
大眾傳媒的發(fā)展,伴隨著報刊的內(nèi)容由嚴肅轉(zhuǎn)向通俗。公眾人物的桃色新聞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充斥著大幅版面。
1983年“被遺忘的”意識以“數(shù)據(jù)自決”的概念闖入人們的視野,并且在德國立法中得到體現(xiàn),為保障個人隱私,允許數(shù)據(jù)主體對個人數(shù)據(jù)的處理和公開享有一定自主決定的權(quán)利。之后,英國1984年與荷蘭1989年分別出臺的《數(shù)據(jù)保護法》都涉及公民享有要求刪除自己個人信息權(quán)利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法國在立法上也對遺忘權(quán)(Right to oblivion)作出解釋,希望賦予青少年與犯罪情節(jié)顯著輕微的人保留其犯罪記錄,進而回歸社會的機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于信息保護的意識初露苗頭,期待以保密或刪除的方式擁有信息自決的權(quán)利,從而得到保護和救濟。而被遺忘權(quán)與隱私權(quán)的不同,也決定了其獨立的結(jié)果。權(quán)利客體上,隱私權(quán)認為信息被公開就不再屬于其保護范圍;被遺忘權(quán)則保護已經(jīng)公開的、可以被他人查看的個人信息。權(quán)利內(nèi)容上,隱私權(quán)強調(diào)隱私的不被披露;被遺忘權(quán)則側(cè)重個人信息在被侵害后的補救性保護。權(quán)能上,隱私權(quán)往往在受侵害后才得以主張;被遺忘權(quán)則是不以侵害為前提的主動權(quán)利。
(二)自媒體時代“刪除權(quán)”的具體化
歐盟1995年《個人數(shù)據(jù)保護指令》第12條對“刪除權(quán)”作出規(guī)定,未經(jīng)同意而獲取的個人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主體享有要求數(shù)據(jù)控制者予以刪除、更正的權(quán)利。
隨后,自媒體時代來臨。人們信息傳播權(quán)利不斷增強,從反面來看這也體現(xiàn)了數(shù)據(jù)自由流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隱私權(quán)的侵害。相應(yīng)的立法上更著重于明確處理個人數(shù)據(j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2003年德國《聯(lián)邦數(shù)據(jù)保護法》指出應(yīng)當(dāng)更正有誤的個人數(shù)據(jù)。2004年法國《數(shù)據(jù)處理、數(shù)據(jù)文件及個人自由法》則指出需要保持個人數(shù)據(jù)的更新,對于不準(zhǔn)確、不完整的陳舊數(shù)據(jù)應(yīng)予以更正或刪除。2010年歐盟委員會在《全面性的歐盟個人數(shù)據(jù)保護方法》中強調(diào)在法定義務(wù)之外,個人應(yīng)享有更正和刪除數(shù)據(jù)的權(quán)利。
人們信息保護的意識不斷加深。在此前單純的保護認識基礎(chǔ)上,保護意志從個人信息權(quán)概念中抽象出來以“刪除”的形式體現(xiàn)在法律中。個人信息權(quán)強調(diào)信息主體對個人信息的支配、決定和保護,是一種由信息主體享有并排除他人非法利用的權(quán)利。涵蓋在信息權(quán)利內(nèi)涵之下的刪除權(quán)則通過對其范圍、基本原則即救濟的具體化規(guī)定,更加嚴格有效的保護數(shù)據(jù)。
(三)大數(shù)據(jù)時代不斷發(fā)展,“刪除”與“被遺忘”概念的過渡
2012年,歐盟公布的《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草案正式規(guī)定個人享有“被遺忘權(quán)和刪除權(quán)”(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erasure)。除數(shù)據(jù)保留有合法理由,數(shù)據(jù)主體(主要針對未成年人)可以要求數(shù)據(jù)控制者永久刪除其個人數(shù)據(jù)。
2013年美國加州也通過了賦予未成年人要求社交網(wǎng)站刪除自己上網(wǎng)痕跡權(quán)利的“橡皮擦法案”。
2014年“谷歌訴岡薩雷斯案”由歐盟法院作出的終審判決影響甚大。法院認為正是搜索引擎的存在使獲得他人個人隱私資料易如反掌,致使個人權(quán)利被束之高閣。至此“被遺忘權(quán)”概念成為正式的法律用語,以其深入人心的特點得到人們的廣泛使用。
歐盟的《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在2014年的修訂中卻最終采用了“刪除權(quán)”(right to erasure)的概念,讓被遺忘權(quán)的權(quán)利主體不再僅限于未成年人。2015年又將相關(guān)表述改為“刪除權(quán)和被遺忘權(quán)”(right to erasure and to be forgotten)。于2018年5月25日最新生效的《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第17條的則采用“刪除權(quán)(被遺忘權(quán))”(Right to erasure(‘right to be forgotten))的表述。
或許“被遺忘權(quán)”的確深入人心,但也存在不接地氣以及概念過于模糊的問題。名稱的修改體現(xiàn)了務(wù)實的態(tài)度,人們從追求其理想化的效果(刪除信息以至其被遺忘)中跳脫出來,將重心放在了信息主體權(quán)利的保護和救濟上。
三、被遺忘權(quán)概述
如前所述,最新的《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于2018年5月25日生效,該條例引起廣泛關(guān)注不僅因為設(shè)定了嚴厲的保護標(biāo)準(zhǔn),而且其適用于全世界范圍的內(nèi)所有面向歐盟從事經(jīng)營活動的企業(yè)。
所謂被遺忘權(quán)(刪除權(quán))是指在約定或法定事由出現(xiàn)時,信息主體有權(quán)要求數(shù)據(jù)控制者對其個人數(shù)據(jù)進行刪除,且控制者應(yīng)在合理范圍內(nèi)控制其已公開的數(shù)據(jù)。
《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第4條規(guī)定“‘個人數(shù)據(jù)是指已識別到的或可被識別的自然人的所有信息”。從而明確被遺忘權(quán)的權(quán)利主體是自然人(排除法人和其他組織)。而被遺忘權(quán)所指向的客體是自然人的一切信息。有學(xué)者指出將“一切信息”作為被遺忘權(quán)客體的范圍過于寬泛,必然會引起諸如與言論自由的激烈碰撞或是使司法實踐具有不確定性的問題。
美國先后制定了多部性犯罪者信息公開法并建立公開性犯罪者信息的數(shù)據(jù)庫。中國也于2019年8月宣布將建立全國兒童性犯罪數(shù)據(jù)庫。在此基礎(chǔ)上反映了對被遺忘權(quán)適用的客體需要作進一步的限制才能更有利于權(quán)利保護。
被遺忘權(quán)的義務(wù)主體即信息控制者,是能夠單獨或共同決定個人數(shù)據(jù)的處理目的和方式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機構(gòu)、行政機關(guān)或其他實體。 控制者在理論上被分為一般數(shù)據(jù)控制者和公開披露的信息控制者。《一般數(shù)據(jù)條例》第19條的規(guī)定明確了公開披露的信息控制者除非證明不可能完成或者包含不成比例的工作量,要在一般數(shù)據(jù)控制者承擔(dān)的刪除個人信息義務(wù)的基礎(chǔ)上,負擔(dān)告知已接受個人數(shù)據(jù)披露的接受者的義務(wù)。可想而知,后者的行為對信息主體的利益將具有更徹底和直接的影響,在此基礎(chǔ)上會帶來極高的成本以及實現(xiàn)的難度。
《個人數(shù)據(jù)保護法》第17條第3款在特定情形下排除了刪除權(quán)的適用,例如言論自由的行使、公共利益的保護(包括遵守法定義務(wù)、保障公共衛(wèi)生領(lǐng)域公共利益、滿足檔案管理、科學(xué)或歷史研究、統(tǒng)計目的需要)等情形。2018年的《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也將“修正權(quán)”(Right to rectification)和“刪除權(quán)”在一節(jié)內(nèi)容中分開,使救濟不再呈現(xiàn)單一性,不能以信息過時或不準(zhǔn)確為由而直接要求刪除。
四、目前被遺忘權(quán)存在的困境
(一) 被遺忘權(quán)權(quán)利保護與言論自由的碰撞
審查信息是否符合刪除條件本身就涉及隱私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問題,而通常情況下被遺忘權(quán)的義務(wù)主體指向搜索引擎公司,其實際上難以擔(dān)此重任。實踐中,搜索引擎公司在收到信息主體刪除數(shù)據(jù)的申請后,就從中立的服務(wù)提供者轉(zhuǎn)變成了判斷信息能否刪除的審查者。為了避免審查不力帶來的損失,搜索公司必然選擇擴大刪除范圍進而侵害言論自由。
“隱私權(quán)”自其出現(xiàn)以來就與“言論自由”有所沖突。以歐洲與美國為代表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觀點。嚴格推行《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的歐盟站在公民以主張刪除個人信息而保護隱私的立場。而美國則認為自愿進入公共視野的言論,不再屬于隱私權(quán)保護的對象,被遺忘權(quán)的存在侵害了言論自由。但美國于2015年實施的“橡皮擦法案”可以反映出其在隱私保護方面的讓步,以及為被遺忘權(quán)本土化所做出的努力。
(二) 被遺忘權(quán)的權(quán)利構(gòu)造與其權(quán)利保護目的之間的內(nèi)在張力
傳統(tǒng)社會的信息多以有形方式存在,一場雨或是一把火就可以達到永久刪除以至遺忘的目的。而大數(shù)據(jù)時代背景下,上傳的數(shù)據(jù)可以瞬時覆蓋全球。甚至是已被刪除的數(shù)據(jù),人類都找到能使其復(fù)原的方法。立法者在“被遺忘權(quán)”和“刪除權(quán)”概念之間的取舍(參考第二部分),也涉及這方面的原因。被遺忘權(quán)是信息主體期待通過數(shù)據(jù)控制者刪除其個人數(shù)據(jù),使外界無法查獲,以最終達成遺忘的目的。這種期待是理想化的,而不具有現(xiàn)實性。即便以刪除權(quán)代替了被遺忘的概念,核心問題仍在于表面上的刪除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刪除。
注釋:
瑞栢律師事務(wù)所譯.歐盟《一般數(shù)據(jù)保護條例》GDPR:漢英對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參考文獻:
[1]彭支媛.被遺忘權(quán)初探[J].中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4,30(1):36-40.
[2]于浩.被遺忘權(quán):制度構(gòu)造與中國本土化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8,50(3):149-157+176-177.
[3]王茜茹,相麗玲.被遺忘權(quán)的演化進程研究[J].現(xiàn)代情報,2015,35(9):160-164.
[4]吳飛,傅正科.大數(shù)據(jù)與“被遺忘權(quán)”[J].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5,45(2):68-78.
[5]萬方.終將被遺忘的權(quán)利——我國引入被遺忘權(quán)的思考[J].法學(xué)評論,2016,34(6):155-162.
[6]夏燕.“被遺忘權(quán)”之爭——基于歐盟個人數(shù)據(jù)保護立法改革的考察[J].北京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5,17(2):12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