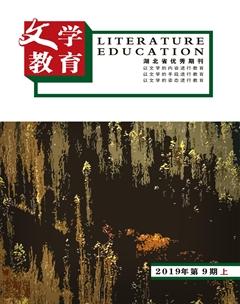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反戰觀
內容摘要:史詩均寫戰爭,《摩訶婆羅多》作為史上已有寫本的最長史詩也不例外。本文從史詩的布局、結構和結局三個維度對史詩的戰爭觀加以探討,再經由與荷馬史詩、中國漢族邊塞詩歌的對比中發現:東方文學中對戰爭的人道主義關懷與西方文學中對抗爭精神、進取精神的贊頌形成鮮明的對照,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流露和秉持的是一種堅定的反戰思想。
關鍵詞:《摩訶婆羅多》 和諧 梵我合一 反戰
《摩訶婆羅多》與《羅摩衍那》,并稱印度兩大史詩。它們是印度古代文學史上,繼吠陀文學之后的又一座文學高峰。《摩訶婆羅多》講的是“偉大的婆羅多族的故事”。全書分18篇,以列國紛爭時代的印度社會為背景,講述了婆羅多族兩支后裔俱盧族和般度族爭奪王位繼承權的斗爭。這是貫穿全書的主干故事。
史詩都寫戰爭,現存于世的史詩沒有不寫戰爭的。戰爭是史詩的永恒主題。因為它是民族融合,民族沖突時期的產物,所以不能不寫戰爭。關于這部史詩的戰爭觀,現在通行的教材都認為它歌頌的是堅守正法的般度族一方。劉安武在《印度兩大史詩研究》中說:“史詩詩人們對這類征討性的戰爭,特別是堅戰所進行的戰爭是肯定的,是贊揚的,是將其作為英雄行為和輝煌武功來歌頌的。”[1]同樣“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鄭克魯主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外國文學史》(2015)認為“這部史詩的基調是歌頌以堅戰為代表的正義力量,譴責以難敵為代表的邪惡勢力。”[2]還有,蔣承勇主編、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世界文學史綱》(2000)也認為史詩是“對以般度族長兄為代表的氏族上層勢力進行的歌頌。”[3]但細讀文本會發現,拿戰爭目的來說,發動這場戰爭是為了王位繼承權,可以說純粹就是內訌,本身無所謂正義非正義,因此也就談不上歌頌哪一方,譴責哪一方。拿戰爭手段來說,在戰爭中代表正法的般度族常常是通過非法手段取得勝利的。就連史詩中頭號反面人物的難敵被般度族怖軍用鐵杵擊斷雙腿時,史詩作者對般度族的這種非法行為是斥之以強烈譴責,而對難敵卻傾注了巨大的同情心。關于當時的情景,史詩是這樣描寫的,“天空雷聲滾滾,大地戰戰兢兢。宇宙間,到處回蕩著怪獸的哀鳴;森林中,成千上萬的禽獸大聲號唳;般度軍中,戰象狂吼,戰馬蕭蕭。可怕的征兆——無頭的和血淋淋的形體出現在大地的上空。”[4](6.40-43)面對這種情景,可以說是足以讓人聞風喪膽。當難敵控訴完黑天大神之后,從天上飄落了一陣花雨,并傳來了天女贊頌難敵的歌聲。由此看來,史詩作者主要是通過兩族的毀滅性爭斗來表達印度人民對戰爭和暴力的厭惡、痛恨、反對,對美好人性的向往。接下來我們進入文本,從史詩的布局,結構,結局三個方面來具體探討史詩的戰爭觀。
首先,從布局來看,全詩共18篇,真正描寫戰爭的只有5篇,相當于總篇幅的四分之一過一點。由此可見,戰爭描寫不占主要地位。這雖然不能說明史詩是反戰的,但至少說明,這部史詩它不歌頌戰爭。
其次,從結構來看,《摩訶婆羅多》與其他民族的史詩不同,它是讓人的惡劣本性先膨脹,戰爭結束之后讓戰爭的雙方參與者都意識到一個印度教一直以來想讓人明白的道理,即人活著為“利”、“欲”而爭斗毫無意義,為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完全不值。史詩中大戰結束之后,我們看到的并不是熱烈慶祝勝利的場面,而是用大量篇幅描寫了戰勝方對大戰的懺悔。代表正法的堅戰心中十分痛苦,他對那羅陀大仙說,“雖然我成了王國之主,但親戚兒子全死了,這勝利無異于慘敗。”在《夜襲篇》中是這樣描述的:“貢蒂之子堅戰發出痛苦的悲訴,‘不幸看來像幸運,幸運看來像不幸。這種勝利不像勝利,這種勝利是失敗。已經取得勝利,卻像落難者那樣憂愁煩惱,我怎么能認為這是勝利?倒是更像被敵人戰勝的失敗者。”[4](10.11-13)再來看看史詩是怎么描寫戰后的戰場的。《婦女篇》中有這樣一段話:“大地遍布成堆成堆砍斷的頭顱、手臂和各種肢體,雜亂無序。婦女們看到無頭顱的軀體和無軀體的頭顱,亦俱亦喜,困惑不安。他們拼接頭顱和軀體,仔細察看,發現對不上,痛苦地說到,‘這部分不是他的。她們逐一拼接利箭砍斷的手臂、大腿和腳,滿懷痛苦,一次又一次昏闕。有些尸首已經遭到鳥獸吞噬,婆羅多族婦女們認不出自己的丈夫。”[4](16.50-54)這些描寫真是觸目驚心。拼接頭顱和軀體,讓人不寒而栗。主人公堅戰對待戰爭的態度更能說明問題,勝利后他不是立刻作稱王稱霸的準備,而是決定到森林中苦修,以贖罪過。在眾人的再三勸說下,才勉強答應治理國事。后來,當聽到黑天大神死去的消息,便喪失了對塵世最后的一點留戀,帶著四兄弟、黑公主以及一條象征正法的狗去雪山苦修,完全放棄了戰爭的成果。
作戰后放棄戰爭成果,這是個不同尋常的結構,其實印度史詩的智慧就在這個地方。印度人打完仗之后,他不是鳴炮奏樂,歡慶勝利。而是覺得一點意思都沒有。印度人認為,人間發生的一切事情,特別是重大群體行為,就像人間戲劇,人扮演的只是演員的角色,總導演是天神,天神指揮一切。在此情形下,人是無法抗拒命運的。例如當兩軍列陣于俱盧之野時,兩族堂兄弟突然都覺得不該骨肉廝殺,特別是般度族的阿周那非常動搖。但毗濕奴化身的黑天大神不答應休戰,這時候他親自出馬上陣,出來督戰。長篇大論20余萬字的《薄伽梵歌》一個基本的意思就是告訴人們,人你要完成自己的義務,義務是神所賦予的。其實,這仗其實是天神讓他們打的,但打仗的目的是讓人們自覺地意識到打仗沒有意義,也就是說打仗是為了今后不打仗。這是印度神一貫使用的伎倆,欲擒故縱。讓你和平,先讓你嘗嘗不和平的滋味。印度教認為人如果不通過滿足某種欲望來克制這種欲望,人將永遠為欲望所支配。并認為人的生活是有周期的,理想的人生應該經歷四個階段:首先是梵行期——學習知識,接著家居期——成家立業,再后來是林居期——刻苦修行,最后遁世期——遠離世俗,達到解脫。由此可知,人首先是要經歷世俗的生活,才會進入解脫,回歸永恒。代表正法的堅戰最終放棄王位,追求解脫其實是厭戰思想的最好注釋。
《摩訶婆羅多》的這種厭戰思想,還反映在結局上。在《升天篇》中,堅戰來到天堂,見難敵早已端坐中央,并且四周還有神女環列。也就是說,正法方和非正法方在勝利和失敗之后都有一個共同的歸宿,升天。這個一反常規的結局立馬印證了我們之前提到的觀點,這場弟兄之間的戰爭根本就沒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它只不過是人類利欲熏心的展示,最終都必須走向解脫這條路。綜上所述,《摩訶婆羅多》的戰爭觀實際就是兩個字:反戰。
沒有對比,就沒有發言權。為了進一步加深對這部史詩所持戰爭觀的了解,接下來我們拿《摩訶婆羅多》與《荷馬史詩》、我國唐代邊塞詩作比較,來分析探討東西方史詩迥然不同的戰爭觀。
《摩訶婆羅多》與《荷馬史詩》作一比較。之前已經提到,但凡史詩都寫戰爭,而戰爭的核心在英雄,因此我們以這部史詩中最典型的英雄人物毗濕摩和《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做一比較分析,從英雄的視角來觀照各自不同的戰爭觀。
古希臘人認為:“人同自然的劃分是知識和智慧的起點,是人之所以為人,自覺其為人的起點。”[5]正是從這種人與自然分離的觀念出發,《荷馬史詩》重在描寫英雄與命運的沖突。在荷馬看來,命運的力量是強大的,但完全是可以對抗的。荷馬筆下的英雄,性格鮮明,不甘做命運的奴隸。史詩開篇即言,“女神啊,請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致命的憤怒吧。”[6]阿喀琉斯出生之時,神告訴他有兩種命運:要么在家中好好呆著,這樣就可平平安安、幸福長壽,要么走向戰場、但命定早死。可是他卻毅然選擇了第二條路,與命運抗爭。也就是說他打算用有限的生命抗拒不可捉摸的命運,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的自身價值得以最大限度的展示,閃耀出人性中勇敢、智慧和進取精神的光輝,這就是阿喀琉斯也是希臘所有英雄的追求。阿喀琉斯對戰爭的態度表現出西方海洋文明所特有的抗爭型進取型文化的特征。
而古印度人追求的卻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正是在這種思想統攝下,印度人要求人們以理性、情感和行動去領悟自我與宇宙的合而為一,實現人與最高自我的結合。它要求人們既要履行人生的責任義務,又要超越于人生。在史詩中,這種思想是通過英雄人物的思想、言行以及他們的沖突來體現的。老英雄毗濕摩就是這種和諧精神的典范。他完美地實現了作為族長的義務,作為武士的職責,作為婆羅門的超脫。為維護國家大局的穩定,他放棄王位繼承權和作為人最基本權利的天倫之樂,并養育和教導了婆羅多族三代君主;之后在般度、俱盧兩方發生分歧、矛盾激化的時候,他從大局著眼,從中調節、斡旋,并且始終支持代表“正法”的般度族;在自身無力阻止悲劇發生之時,他又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履行了一個剎帝利應盡的義務;最后,臨死之時,仍苦口婆心勸說兩方握手言和。因此毗濕摩面對命運時才會顯示出安詳和坦然。以這種思想為基礎,毗濕摩就表現出一種寶貴的厭惡戰爭、追求和平的精神。這與希臘英雄好戰進取的精神,歌頌戰爭的情景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精神在今天這個暴力沖突仍未止息的時代,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的。
接下來再拿我國唐詩中的邊塞詩與《摩訶婆羅多》作比較,來進一步領會東方戰爭觀的精髓。唐代邊塞詩中,李白、杜甫、高適的詩中均顯示出人道主義的關懷。如杜甫的《兵車行》“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又如高適的《燕歌行》“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殺氣三時作陣云,寒聲一夜傳刁斗。”邊塞荒涼孤寂的意象與詩人反戰的傾向融為一體。
由此可見,東方文學中對戰爭觀點的人道主義關懷與西方文學中對抗爭精神進取精神的贊頌形成鮮明的對照。古印度的梵我同一以及中國的天人合一,這共同表明東方追求一種和諧的自然狀態。
參考文獻
[1]劉安武.印度兩大史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0
[2]鄭克魯編.外國文學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64
[3]蔣承勇編.世界文學史綱[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441
[4][印度]毗耶娑.摩訶婆羅多.黃寶生等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5]楊適.中西人論的沖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01
[6][希臘]荷馬.伊里亞特.羅念生譯.羅年生全集.第五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
(作者介紹:侯建芳,河西學院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世界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