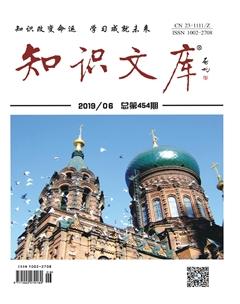淺談翻譯的雙重特征
倪娜
關(guān)于翻譯到底是科學(xué),技巧,還是藝術(shù)的爭論可謂曠日持久。近些年來,機(jī)器翻譯代替人工翻譯的呼聲越來越高,與此同時(shí)對于機(jī)器翻譯的質(zhì)疑之聲也從未減少。2018年博鰲論壇上的AI同傳的現(xiàn)場效果并不完美,人工智能是否能取代同聲傳譯,機(jī)器翻譯是否能代替筆譯譯員耗費(fèi)無數(shù)心血完成的譯文,這個(gè)問題又再次被人們熱議。如果機(jī)器翻譯成功了,那么證明翻譯的科學(xué)性起主導(dǎo)作用。但翻譯學(xué)是一門經(jīng)驗(yàn)科學(xué),翻譯經(jīng)驗(yàn)是基石。語言是有生命的,是不斷變化的。就目前的實(shí)踐看來,機(jī)器翻譯雖然一直在不斷完善,但并未達(dá)到我們要求的水平。由此證明翻譯并不完全是一門科學(xué),還需要技巧與藝術(shù)加工。
翻譯到底是科學(xué)?技巧?還是藝術(shù)?這個(gè)話題一直沒有定論。但毋庸置疑的是,翻譯之初就是兩種語言的轉(zhuǎn)換,以達(dá)到不同語言的人們之間的交流。隨著不同語言的種族之間交流的增多,人們對于翻譯的要求才隨之越來越高。從傳統(tǒng)上看,人們似乎將‘翻譯僅僅視為一種技藝,并沒有將它提到‘學(xué)科的高度。幫助我們認(rèn)識(shí)‘翻譯是一門經(jīng)驗(yàn)科學(xué)的是哲學(xué)家,特別是20世紀(jì)30年代以來發(fā)展起來的科學(xué)哲學(xué)家。科學(xué)哲學(xué)家使翻譯研究者獲得了充分的理據(jù),提出‘翻譯理論。
1 翻譯的科學(xué)性
翻譯出現(xiàn)之初,一定是經(jīng)驗(yàn)學(xué)。只是不同語種的人們出于交流的目的進(jìn)行的兩種語言上的轉(zhuǎn)換。但是在不斷的實(shí)踐當(dāng)中,人們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規(guī)律,制定翻譯規(guī)則,歸納翻譯方法。翻譯就逐漸上升到科學(xué)的高度,用于指導(dǎo)實(shí)踐。
但翻譯學(xué)又不同于其他科學(xué)學(xué)科,有具體可以量化,精確到數(shù)字的標(biāo)準(zhǔn)。翻譯學(xué)其實(shí)可以認(rèn)為是社會(huì)學(xué)與人文學(xué)科的綜合體,在這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翻譯現(xiàn)象不是一種簡單的兩種或者多種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行為,而是社會(huì)現(xiàn)象、文化現(xiàn)象、心智現(xiàn)象、精神現(xiàn)象與語言現(xiàn)象的結(jié)合。翻譯進(jìn)行時(shí)需要綜合考慮社會(huì)、宗教、政治、文化、教育背景等多個(gè)領(lǐng)域的問題,是多種因素作用下的文化產(chǎn)品。可以說, 翻譯學(xué)是一門獨(dú)立的、開放性的、綜合性的社會(huì)科學(xué)。
2 翻譯的藝術(shù)性
翻譯是文字的加工與再創(chuàng)作,很多情況下,翻譯并不是單詞的羅列與疊加,而是連貫的語言表達(dá)。而其中包含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等背景。例如:Autant de tête, autant davis. 如果按照字面翻譯,則為:一樣多的腦袋,一樣多的主意。但考慮到文化背景,中文則將其翻譯成“三個(gè)臭皮匠賽過一個(gè)諸葛亮”。原文中既沒有出現(xiàn)臭皮匠,也沒有看到諸葛亮。但通過這樣的藝術(shù)加工,卻使母語是漢語的人們瞬間就了解到上述文字的含義,達(dá)到了交流的目的。又比如“Quand le chat nest pas là, les souris dansent.”按單詞本意來翻譯,為“貓兒不在,老鼠跳舞”。但如果考慮到譯入語的語言習(xí)慣,則應(yīng)翻譯為“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成語、古詩,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翻譯界一直有一種說法,翻譯就是誤讀,詩歌是無法翻譯的。那是因?yàn)榭紤]到翻譯背后的文化、社會(huì)背景、生活習(xí)慣、政治背景等因素。不管翻譯是不是可以完全表達(dá)原文的意圖,翻譯本身不可能只是翻譯文字本身,單純的“科學(xué)加工”下的譯文,很可能導(dǎo)致翻譯出的文字根本不符合譯入語的語言習(xí)慣,根本無法讓人理解譯文含義。
然而翻譯本身又有自身的局限性和依附性, 只能算作一種特殊的準(zhǔn)藝術(shù)形式。因?yàn)樗荒軅€(gè)性鮮明地顯露自己的藝術(shù)特征,它必須在尊重原文的基礎(chǔ)上的再創(chuàng)作,而且受到譯者自身語言水平與文學(xué)素養(yǎng)等條件的限制,導(dǎo)致譯文水平參差不齊。而翻譯質(zhì)量不高, 平庸的譯作充斥書市, 也是社會(huì)誤解文學(xué)翻譯, 也是翻譯藝術(shù)不被人認(rèn)可的原因之一。
3 翻譯是科學(xué)還是藝術(shù)?
根據(jù)翻譯的內(nèi)容不同,翻譯的方法頁不同。針對科技翻譯,或者專業(yè)詞匯密布的專業(yè)性翻譯,翻譯主要依靠的是詞匯的轉(zhuǎn)換,重要的是知識(shí)上的對等,而無需過多的考慮翻譯內(nèi)容的情感因素,社會(huì)因素和文化背景。而針對文學(xué)翻譯則不同。文學(xué)翻譯與藝術(shù)有其共同點(diǎn),都需要有創(chuàng)造性。但兩者又不完全相同,藝術(shù)創(chuàng)作沒有范本,完全是藝術(shù)家本身的思想表達(dá),情感宣泄。而文學(xué)翻譯,既需要譯者的再加工、再創(chuàng)作,又需要尊重原文作者的本身所想要表達(dá)的觀點(diǎn)。嚴(yán)復(fù)先生在《天演論》中提出的“譯事三難:信、達(dá)、雅。” ,首先也是強(qiáng)調(diào)“信”字,翻譯必須忠實(shí)原文。而譯者本身并不只是文字的搬運(yùn)工,而是需要準(zhǔn)確的傳達(dá)原文作者的思想,并結(jié)合文章受眾的文化習(xí)慣、閱讀習(xí)慣、知識(shí)背景等元素。完全按照科學(xué)理論一板一眼翻譯,針對文學(xué)翻譯顯然并不適合。
張經(jīng)浩教授在《譯論》一書中指出: “翻譯不是科學(xué), 是技術(shù)或者藝術(shù)”,“翻譯是科學(xué)的說法不能成立, 而且翻譯既是一門技術(shù)或藝術(shù)又是一門科學(xué)的說法也不能成立。其實(shí),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既是技術(shù)或藝術(shù)又是科學(xué)的混合體”。還提到“正因?yàn)榉g不是遵從某些法規(guī)的機(jī)械性語言轉(zhuǎn)換, 而是需要?jiǎng)?chuàng)造力的語言再現(xiàn)藝術(shù), 人們原有的機(jī)器翻譯設(shè)想才始終未能取得成功”。但根據(jù)翻譯標(biāo)準(zhǔn)多元互補(bǔ)論,我們會(huì)得到與上述說法大相徑庭的結(jié)論:翻譯既是科學(xué)也是藝術(shù)。 說得更具體一點(diǎn),在一些場合,翻譯主要是科學(xué);在另一些場合,翻譯主要是藝術(shù)。針對科學(xué)性強(qiáng)的翻譯,在科學(xué)理論指導(dǎo)下的機(jī)器翻譯可以勝任,但針對文化色彩濃厚的翻譯,則需要譯員的翻譯技巧與藝術(shù)再加工。當(dāng)然,這種技巧與藝術(shù)加工也是在科學(xué)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現(xiàn)如今,譯員翻譯已不同于幾十年前,科技的介入,科學(xué)的指導(dǎo),譯員們有了許多的輔助工具與手段,都在幫助他們降低翻譯難度,提高翻譯效率,增加翻譯的準(zhǔn)確度。AI人工智能在一些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也緩解了人工翻譯的不足。在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的今天,世界就像一個(gè)地球村,各國之間的交往異常頻繁,不同語言之間的交流需求呈火箭式增長,很明顯,人工翻譯根本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人工翻譯就是遠(yuǎn)水救不了近火,人工智能或者軟件翻譯,雖然并不一定準(zhǔn)確,但卻可以解燃眉之急。
4 結(jié)語
關(guān)于翻譯到底是科學(xué),技術(shù),還是藝術(shù)的爭論可謂曠日持久,有人更加堅(jiān)定與自己的觀點(diǎn),如勞隴;有人改變了自己的觀點(diǎn),如奈達(dá)和譚載喜;更有人從哲學(xué)的角度調(diào)和了這對矛盾,即翻譯既是科學(xué)也是藝術(shù),相輔相成,辯證統(tǒng)一,如辜正坤;還有人認(rèn)為這樣的爭論實(shí)際上并無意義,如朱純深。
我認(rèn)為這是一個(gè)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們不必急于尋求一個(gè)令所有人都滿意的結(jié)果。在翻譯的實(shí)踐與翻譯學(xué)的逐漸建立的過程中,這個(gè)問題會(huì)迎刃而解,或者漸漸失去討論的意義。縱觀學(xué)術(shù)界深層的思維定勢和研究取向,我們往往會(huì)發(fā)現(xiàn)存在一種現(xiàn)象,那就是對微觀事件可以任其含糊,對宏觀的名分確立則耿耿于懷,名不正則言不順。其實(shí)我們更應(yīng)該重視的是微觀的翻譯事件,當(dāng)務(wù)之急不是討論翻譯到底是什么,而是如何發(fā)展切合自身特點(diǎn),與國際接軌、被國際認(rèn)可和接受的翻譯理論去指導(dǎo)實(shí)踐。
(作者單位:天津商業(yè)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