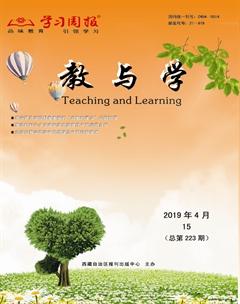論《貝姨》中的貨幣哲學觀
摘 要:馬克思的貨幣哲學理論認為貨幣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轉變為物與物關系的一種異化。本文試圖用馬克思的貨幣哲學理論來分析巴爾扎克在《貝姨》中對物欲橫流的巴黎社會的描寫。文章分為兩部分:一是闡述馬克思的貨幣哲學理論;二是用這種理論探討小說中所描寫的社會現象。
關鍵詞:貨幣哲學;異化;金錢觀;欲望
一、馬克思的貨幣哲學觀
馬克思以人類在現實生活中所從事的物質生產活動和經濟活動為出發點,獨辟蹊徑,從哲學角度對貨幣本質進行探討,認為其本質上是人類社會關系的一種呈現。
馬克思認為:貨幣的產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變成勞動產品與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即披著經濟統治外殼下的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當人們普遍以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進行交換時,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會被物的外殼所覆蓋。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改變為物作用于物的關系,即社會關系的物化。貨幣的出現使得人分配的東西由權力轉變為貨幣,人們萌生出強烈的拜物心理,人們對金錢、商品等物品產生崇拜與敬仰,進而將其視為人所追求的終極目標。
馬克思指出:“依靠貨幣而對我存在的東西,我能為之付錢的東西,即貨幣能夠買的東西,那是我—貨幣占有者本身。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1”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各個階級與階層之間的差距以貨幣多少來體現,階層之間所擁有的貨幣數量的不對等造成社會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馬克思揭示的是貨幣與人類社會以及人性之間的關系,進而上升到對人類社會進步及人類解放的思考。
馬克思立足于對人類現實社會的深刻批判,認為對貨幣的瘋狂癡迷只是人們在資本社會中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一種途徑和手段。人類對貨幣的盲目追逐使得社會逐漸被貨幣領導和統治,擁有貨幣的多少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有價值的根本依據和判定標準。貨幣是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的貨幣,是社會化的貨幣,這是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物化,但物化世界的產生卻又是由人的本質的異化所引起的,人的異化是貨幣異化的根源。
二、談《貝姨》中的貨幣哲學
在七月王朝時期的法國巴黎,舊式貴族已日趨沒落,新興資產階級逐漸占領統治地位。主人公貝姨卻只是富貴人家的窮親戚,是社會的底層人民,盡管她和堂姐于洛太太人出身相近,但于洛太太卻生得乖巧,攀上了一門好親事,貝姨目睹著堂姐一家奢侈豪華的生活,心中不免嫉妒。
貝姨一生都在追逐著金錢和地位,但與顯赫的社會地位相比,貝姨對金錢的渴望更為癡狂。貝姨的一生是一個小人物的奮斗史,她心氣高,立志要自己掙得一份家業,成為整個工廠技術最嫻熟的女工,但夢想眼看要實現時,帝國卻崩潰了。社會的變革使得資產階級新貴族和底層社會人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希望被革命扼殺,貴族們所擁有的權勢和地位在資產階級面前不值一提,擁有金錢才至關重要。貝姨解救了波蘭青年人,一開始,她便用一張借據控制了這個年輕人,他們雖然相互依賴,但關系卻不是依靠感情來維持,青年人只是屈服于貝姨母性的控制。
小說所展現的并非只是貝姨自己的個人命運,而是以貝姨為聯接點,通過講述貝姨及周圍人的人生際遇,來表現大的時代下被金錢所奴役的人類的命運。
巴爾扎克在描寫金錢時毫不避諱,反而直截了當。克勒韋爾從前他也只是個跑堂的,但卻深刻認識到了金錢的重要性,于是不計一切手段,擴充資產,甚至憑此當上上尉。獲得金錢的手段毫不重要,只有將金錢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最為踏實。根據社會地位,克勒韋爾的女兒是遠遠配不上于洛男爵的兒子。但“這個年月,像奧棠絲那樣漂亮的姑娘,沒有陪嫁就沒有人要。她那種美女,做丈夫的見了要害怕的;好比一匹名貴的馬,需要太多的錢照料,絕不會有多少買主。[2”愛情與婚姻在金錢面前不值一提,不再高貴。克勒韋爾是在變動的社會中獲得巨大利益的資產階級金融貴族的典型代表,他們靠著各種生意謀取大量利益,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社會地位也隨之提升。
作者不吝筆墨地描寫于洛男爵的人生際遇。于洛男爵家已經衰敗,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是其包養情人,男爵不顧一切,對情人們投入大筆金錢,這些情人是用金錢堆砌出來的,身上掛滿了黃燦燦的金子,她們大都揮金如土,貪得無厭,不斷從各個男人身上索取,將一個個男人刮得精光。包養情婦是男人間的攀比和炫耀,這些女人不是作為一個人而存在的。于洛男爵將大筆的錢揮霍在情婦身上,將近傾家蕩產,他表面雖毀于女人,實則上是毀于金錢和自己的虛榮心。。
從資產階級新貴族的代表于洛到資產階級金融貴族的代表克勒韋爾,到處于社會下層地位的貝姨以及巴黎男人的那些情婦們,無一不喜歡金錢,不視金錢為生命。整個巴黎是金融貴族的專制,自上而下都已被金錢腐化。“正是在資產階級的上層,不健康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無節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資產階級法律相抵觸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種形式下,投機得來的財富自然要尋求滿足,于是享樂變成淫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就匯為一流了。[1]”
巴克扎克也直接批判了這種金融勢力膨脹的社會現象,“這種病根在于缺乏宗教,也在于金融勢力的擴張,說穿了便是自私自利的結晶化。從前,金錢并不包括一切,大家還承認有高于金錢的東西。例如貴族、才具、貢獻于國家的勞跡;但是今天,法律把金錢定期衡量一切的尺度,把它作為政治能力的基礎……[2]”過去視神或上帝為最高統治者的觀念已被貨幣所取代,人們崇拜的已經由神靈轉變為衡量所有事物價值的物神——金錢。
馬克思也承認貨幣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但巴爾扎克筆下,基本只刻畫了貨幣的消極作用。貨幣與人類社會息息相關,貨幣的異化是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一種異化,也是人以及人類勞動的一種異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
[2]巴爾扎克.《貝姨》.上海三聯出版社,2015年.
[3]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人民出版社,1965年.
[4]王淼:《貨幣的倫理反思與社會批判——馬克思貨幣哲學思想解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7月.
作者簡介:
安茁(1996.03—),女,漢族,陜西渭南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研究生,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