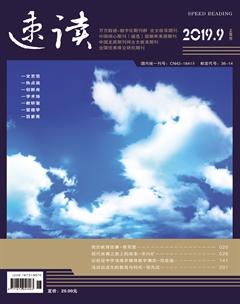勤學苦練不能停
張喜平
俗話說要想戲路通,全靠幼時功。從小在父母的熏陶下,我就對戲曲有了濃厚的興趣。父母都是秦腔演員,經常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演出。看完了回到家里,我就漫無目的的模仿,時間長了就有了這個習慣。可事情往往不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去發展,因為還喜歡武術,想當一名武術運動員,卻又苦于沒有專門的武術學校,思來想去,便去了業余體校學體操。沒想到這一練就是8年多,還在全國各地參加比賽,也取得一些的成績。高中畢業后,便鬼使神差的就考進了寧夏平羅縣秦劇團,那年我才16歲。
常言道,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在學藝這道路上,誰都知道非常的苦。每天清晨5點多就要起床練功,練功本來就練的腰酸腿疼,早飯過后還要拖著疲憊的身體跟著老師學戲,日子過得真叫個苦。但耳畔總有老師的教導在回蕩,有勁使在功上,有功用在戲上。自己也暗下決心,要想當好一個好演員,出人頭地,多苦都得咬牙堅持。
因為不是在專門的戲校學藝,像我這樣的就叫學員,用劇團的行話叫跟班生。既然是在劇團,跟老師們外出下鄉演出也是家常便飯。下鄉演出也很辛苦,吃飯住宿條件也很差。上午一般沒有演出的時候,老師就帶我們在舞臺上練功和學戲。記得當時有位何老師對我們很好,他每天起得很早,幫我們燒好水,然后幫我們一一檢查好練功服。夏天自然好說,可在冬天,叫我們起床練功踢腿、跑身架、拿大頂、輪桿花,唱念做打一樣都少不了。雖然下鄉演出這么辛苦,吃住的條件特別差,但單純的思想和單調的生活,每天的心情卻顯得很高興。
有道是要練驚人藝,須下苦功夫。由于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堅持,生物鐘對每天的作息時間都有了慣性。比如早上5點多起床先練一次功到8點,然后吃早飯,休息半小時也就到了上班時間,學員們就繼續練功練到中午十一點半。下班吃完飯中午休息到兩點上班,繼續練功到五點半。下班吃晚飯,七點半再練到十點半。下鄉演出主要練功時間是在上午,因為中午和晚上都有演出。十幾年如一日,除了練功就是演出。
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記得那時候下鄉演出的時候經常站在舞臺的側面觀看老師的演出,當時心里就想,自己什么時候能像老師這樣演出呢?不知不覺十幾年又過去了。1987年,我從寧夏平羅秦劇團調回到甘肅平涼秦劇團工作,也就是說調到家門口了。想想自己十幾年學藝,功夫練了不少,就是不會演戲,只會跑龍套、演雜角,翻跟頭、當馬童。父母對我說,要好好學戲,演員的成就是演戲,功夫再好沒有用。老師也說,一定要好好學幾本戲,這才是你吃飯的真正本事。于是,我就暗自下定決心,從頭做起,好好學戲。于是,我除了每天堅持起早練功,就和在寧夏一樣練習各種技能,準備學戲。
因為調回到了父母的身邊,父母對自己的培養也就有了特別的“待遇”。父親教我學《出五關》《金沙灘》《長坂坡》等劇目。在學《出五關》扮演關云長一角時,自己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也吃了很多的苦。《出五關》這本戲一學就是好幾年,父親先是給我講關云長是個什么樣的人物性格,他在曹操這里的心理活動。后又讓我看《三國演義》小說,理解關云長的人物生活經歷和內心活動。跟著父親練習《挑袍》一折上橋的這一段戲,練架子功和唱腔一樣都不能少。每天早晨堅持練功練唱,架子功必須三個多小時,大刀的一招一式,上馬下馬的動作,還有人物的表情。由于經常聽父母講怎么演好這個角色,所以關云長這個角色就深深的印在了自己的心里。
有道是十個指頭不一樣長,人對事物的理解肯定也不一樣。雖然父母經常教導我說在藝術的道路上沒有捷徑可行,自己也知道只有踏踏實實的刻苦學習,刻苦刻苦再刻苦,所以只有不斷琢磨,反復練習。我就照父母和老師說的去練,反復地練,每天堅持練功練大刀,練架子功練唱,練“上橋”動作,練“挑袍”動作,練“灑酒”的動作。也記不清練了多少次,終于有了登臺演出的機會。演出后得到了父母的肯定,也受到了老師的認可。功夫沒白費,觀眾的贊揚、鼓勵和熱情的掌聲就是最好的肯定。
戲曲行內話說道,千斤話白四兩唱,三分唱念七分作。我雖然在扮演角色下了不少功夫,也有觀眾對我出演好評。但外行看的是熱鬧,內行才能看出門道。父母和老師除了對我好的方面進行了肯定外,主要是指出了我許多的不足,目的是讓我更進一步。當時我想趁著自己還年輕,繼續努力,好好奮斗。不久機會就來了,是全區舉行秦腔大獎賽。我征求了父母和老師的意見后,就報名參加了,準備的劇目就是《出五關》中的折子戲《挑袍》。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這次比賽中竟然獲得了二等獎。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趁著這股熱情,又拜岳老師學習《長坂坡》。行家都清楚,《長坂坡》中趙云這一角色,是個武生行當。當時岳峰老師就給我講,要想演好這一角色,離不開腿功、架子功和桿花,還要從2米8高度空翻而下。這個時候練了十幾年的基本功給我壯了膽。我便給老師說:好的老師,這個功夫我沒問題。老師說那就好,還要好好學唱腔和白口,同時表演也都要跟上。老師的話我記在心,我就按照這個新計劃,安排練習腿功,兩個小時的長槍,兩個小時的架子功身段,每天都一樣,苦練苦練再苦練。
老師在舞臺上演,我就在臺下學。我們跑龍套的閑暇時間多,老師抽空就給我指點,教我學“趙子云”。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老師說你可以登臺了。就這樣,我塑造的第二個角色也在舞臺上亮相和觀眾見面了。演出結束后,我非常的激動,就好像拿到了大學畢業證一樣高興。
這次演出后,同樣受到了父老鄉親的認可和鼓勵,好評和掌聲讓自己也很開心。第二天早上起來,老師卻給了我一頓批評,說教我的動作走了樣,亮相沒有做好,就知道練功不會演戲,表情,身段,架子功都沒有到位。以后還要繼續努力下更大的苦功去學習。老師的這盆涼水,讓我醍醐灌頂,清醒地知道了自己還有許多的不足,還離真正的“趙子云”差距很大。從此以后,每當老師演出,我就在一旁認真地學習。
光陰似箭,不知不覺中,老師的年齡也大了。老師把演出的機會給了我,把主要角色讓給我演,我在感動之余,也慢慢感覺到了自己肩上的責任。藝術不正是這樣嗎?一代傳承一代,戲曲才不會消亡。老師年齡大了也變得火氣小了,在以后的許多次演出結束后,常常會聽到老師的表揚,嗯,有進步,演的好,你努力了就會有收獲。有了像模像樣的演出,也就有了和同行同臺交流切磋技藝的機會。記得有一次在和西安的李愛琴老師同臺演出《長坂坡》中的趙云角色,演出過程中,就受到了觀眾十幾次的熱烈的掌聲和熱情的鼓勵。
之后,我又跟我父親學了《金沙灘》中的楊繼業這一角色。父親說,你把這三大本戲學好以后,你演其他戲,就不會那么難了。因為這三大本戲,《出五關》《長坂坡》《金沙灘》不好學,你學會了,就進步了。我讓我的父親當老師教我從頭學起。每天除了練功,就是聽父親教戲和訓練動作。在和父親學戲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吵架的現象。這讓父親很生氣。雖然偶爾會不聽父親的話,但轉天你還得練,這就是父子關系不同于師生關系的奧妙之處。因為我從小注重練形體功,唱腔是我的短板。父親一再對我強調,這出戲要在唱腔上下大功夫,功底再好,唱腔不行,等于白搭。懂戲的人都知道,楊繼業這一角色的唱腔不但很多,而且還要有架子功身段,大刀功夫,唱念做打,樣樣俱全,一個都少不了,是很難的飾演一個角色,一定要下大功夫。
我又練了好長時間,每天練得很煩悶很難受。但還得咬牙堅持,因為父親會做出一些老師不敢做的事情。我覺得自己掌握了臺詞和唱腔,學會了動作和調度,我對父親說要不讓我上臺演一演。可父親卻說,你還不能演,因為你現在掌握的只是毛皮,那里的東西還差得遠呢。于是,我開始反反復復地再練習。一個手勢,一個動作嚴格地練,尤其是在唱腔上,琢磨心境,玩味吐字。父親雖然是嚴師,但也是慈父,看著我每天刻苦的訓練,“心軟”了。有一天他說,我覺得你一次演完夠嗆,要不先分了三段演出吧。于是,楊繼業“點將”先演了。我自己覺著沒問題,可父親卻說,在往好里練。后來我又演了楊繼業在“五臺山”,演出后父親又說,沒演好再繼續好好練。又練了好長時間,才把全本戲演完了。因為這是和父親學的第一本大戲,父親也許在心里頭已經有了很多的贊揚,但嘴上表達出來的一直是不行再好好練,好好學習。這可能就是一個父親對孩子的獨特的關懷吧。
在我的藝術生涯中,最大的感悟就是勤學苦練不能停。你自己覺得差不多了,可在老師的眼里還差得很遠。老師覺得差不多了,觀眾還總會有說三道四。因此,藝無止境,刻苦刻苦再刻苦。從藝這么些年來,這三本大戲都是半文半武的英雄形象戲,自己一路堅持下來,總算沒有改行。近些年演大戲是演不了了,但又不想離開自己熱愛的舞臺,于是就學唱歌,當主持人,閑暇時練習毛體書法,嘗試著做一名毛澤東的特型演員扮演者。
我很榮幸,直到今天,還在不斷努力,奮斗學習,努力工作。我們都是追夢人,文藝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一直在心,不斷用行動實現著自己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本刊訊.甘肅省檔案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參加甘肅代表團審議時重要講話精神[J].檔案,2019(03):3.
[2]田野.“問道崆峒·走進平涼”——聚焦扶貧攻堅,探尋平涼產業轉型升級[J].甘肅農業,2015(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