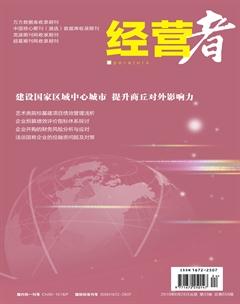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逃稅罪
申莉萍 楊娟
摘 要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在認定主體、確定金額、危害后果上與逃稅罪均不相同,同是危害稅收征管的犯罪,逃稅罪可以通過補繳稅款免于刑事追責,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則無此優惠。在服務和保障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大背景下,給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減輕處罰的空間,是兼顧經濟發展與經濟秩序的合理選擇。
關鍵詞 民營經濟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逃稅罪
一、問題的提出
近期“兩高”相繼發布了首批保護民營企業典型案例,為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服務和保障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提供參考和指引。從公布的指導案例可以看出,發票犯罪的刑事政策與程序都是寬字當頭,以寬為主,重視企業的挽救教育。
1996年的《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的決定》規定了,“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或騙取出口退稅的,應當依照第一條的規定處罰;以其他手段騙取國家稅款的,仍應當依照《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有關規定處罰”。《刑法修正案(七)》針對逃稅罪增加了補繳稅款不追責的規定。同是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犯罪,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方式騙取國家稅款的,達到追訴金額就直接構罪,而以其他方式偷逃稅款的,還有“初犯補稅免責”的補救機會。那么,為什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不能通過補繳稅款的方式免除刑事處罰?該罪與逃稅罪的區別在哪里?應該如何妥善處理好打擊偷騙稅款犯罪與保護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
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逃稅罪辨析
(一)認定主體不同
逃稅罪的認定主體為稅務機關。任何逃稅案件,首先必須經過稅務機關處理,稅務機關沒有處理或者不處理的,司法機關不得直接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原因有三:第一,公安部的批復中,“應納稅額”是指某一法定納稅期限或者稅務機關依法核定的納稅期間內應納稅額的總和;第二,逃稅罪需要行政催收程序前置;第三,逃稅罪中逃稅稅款占應納稅款比值涉及不同稅種的計算,分子和分母的確定均需具備專業的稅務稽查經驗,才能得出準確的數值。
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認定主體為司法機關。該罪將虛開的稅款數額或造成的稅款損失數額作為定罪量刑依據,認定的重點與難點在于判斷哪些發票屬于虛開,需判斷貨物流、應稅勞務流、現金流、發票流是否一致。稅務機關可以通過稅負(銷售收入和納稅額的比值)的異常情況初步判斷企業是否有虛開行為,但要進一步認定準確金額則手段有限,需公安機關刑事偵查后才能對貨物流、現金流、發票流的具體情況固定證據,進而梳理出虛開的發票,最后由鑒定機構累加虛開發票稅額和認證抵扣金額。
(二)金額確定不同
增值稅抵扣一般在網上完成:行為人先選擇、認定進項發票,認證后勾選要抵扣的發票,確定提交,即完成了抵扣騙稅行為。其他逃稅行為,例如偽造、變造賬簿只是逃稅的準備,不申報或不實申報應納稅額才是著手,當稅務機關發現且經催繳后仍無法收回稅款時犯罪才成立。所以,普通逃稅的逃稅金額確定有賴于稅務機關行政行為,而增值稅專用發票騙稅金額由行為人獨立確定。
(三)危害后果不同
逃稅罪中,扣繳義務人既侵犯了國家的稅收征收制度,又侵犯了國家財產權,所以不能適用“初犯補稅免責”的規定。增值稅納稅人也處于和扣繳義務人相似的地位,增值稅實行抵扣制,逐環節扣稅,各環節中納稅人只是把從買方收取的稅款轉繳給政府,而經營者本身并未承擔增值稅稅款,不是真正的負擔者,隨著增值環節向前推進,消費者才是全部稅款的負擔者。因此,增值稅納稅人繳納增值稅,本質上是將“代收的稅款”交付給國家的行為,增值稅納稅人虛開發票騙稅的實質是侵占消費者繳納的稅款,最終損害的是國家財產權,所以后果更嚴重,可罰程度更高。
(四)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適用補繳免責規則
與逃稅罪相比,虛開增值稅發票罪金額認定更依靠司法機關,稅款抵扣也更隱蔽便捷,不易被稅務機關及時察覺,因此無稅款催收前置的現實條件。實際上,逃稅行為的從寬處理是考慮到盡可能保障國家稅收和刑事手段的局限性(而非逃稅本身不值得刑罰),在綜合權衡之下做出的選擇。再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以抵扣騙稅的方式逃稅本就是犯罪,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侵犯了國家財產權,是手段與目的均需要處罰的犯罪,從罪刑相適應的角度看,不應有補繳稅款免責的優惠。
三、賦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減輕處罰的空間
缺乏良性運作的經濟環境與條件,加上嚴格規制,將使經濟主體感到進退維谷,步履艱難,禍福存于旦夕之間。生存不保,何談發展。經濟類犯罪更加注重社會秩序的恢復、損失的彌補,刑法的過度介入會使經濟發展喪失活力與彈性。
(一)以騙取國家稅款的金額為量刑數額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中“虛開稅款數額”和“騙取國家稅款數額”作為選擇性量刑情節,在兩個數額均存在且查實的情況下,因為虛開的數額始終大于實際抵扣的數額,所以將抵扣數額作為認定標準更有利于對民營企業的合理保護。同時,抵扣稅款才是將虛開增值稅的危險現實化,以此為標準也與刑法重實害犯的打擊精神相一致。
(二)延伸損失計算節點
將損失認定時間延長到二審法院判決之前,允許通過補繳稅款的方式減輕處罰。企業逃騙稅高發也有經濟轉型等社會原因,如果絲毫不給企業補過的機會,其結果只能是導致企業被拖垮,國家失去一個稅源。保證社會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是國家總的目的,規制經濟的法律手段也必須服從于這一目的。延長損失計算時間雖會導致金額的認定處于不確定狀態,影響法院判決的嚴肅性,但在服務和保障經濟發展的時代,無論是從功利還是法理的角度,這樣做都是理性的選擇。
(申莉萍單位為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楊娟單位為成都市青羊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