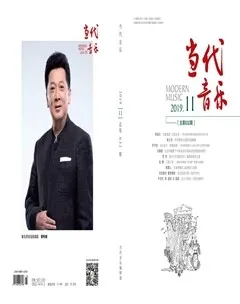維吾爾族打擊樂器在管弦樂中的運用



摘要
多民族地區的管弦樂創作是中國當代音樂創作發展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肖克來提·克力木作為維吾爾作曲家、國家一級作曲家和民族音樂傳播者,他的作品中表達著民族風格、個性特征和對新疆維吾爾族管弦樂創作發展的思考。他的音樂創作涉及領域廣泛,在不同領域均有較為突出的代表作品,如交響音詩《胡楊頌》;歌舞劇《愛的脊梁》;舞蹈音樂《春天來了》;管弦樂《節日序曲》《絲路序曲》《為九件打擊樂而作》等等。
[關鍵詞]管弦樂;打擊樂;音樂分析
[中圖分類號]J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233(2019)11-0122-04
收稿日期2019-08-06
作者簡介(趙曉華(1988—),女,新疆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烏魯木齊830049)
《為九件打擊樂而作》創作于2003年,是肖克來提·克力木有意識地將維吾爾族傳統打擊樂器和西方打擊樂器進行融合而作。在繼承維吾爾族傳統打擊樂技術的同時,也借鑒并糅合了一些西方現代的作曲理念與技術,實現個性化的創新。這樣的創作理念正如他本人所說:“在以往的創作中,我們的作品要么是西洋的,要么是維吾爾族的,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分開的音樂風格,我想要將它們糅合在一起。這個打擊樂就是純新疆風格,但樂器是將兩者相結合,中間的節奏也是典型的維吾爾族5/8節奏,從音響上很容易辨別。”
這部作品,節奏熱情奔放,又對樂器音色進行擴展,這是對維吾爾族傳統打擊樂演奏與技術的更新,豐富了維吾爾族傳統打擊樂的音響,使之對藝術效果有著全新的呈現。作品中所用的打擊樂器除了阿蘭鼓和西洋打擊樂器(鈴鼓、軍鼓、吊镲、定音鼓、大鼓)以外,加入了三件維吾爾族傳統樂器,分別是:薩巴依(Sapayi)、手鼓(Dap)、納格拉鼓(Naera)。
薩巴依(Sapayi),維吾爾族打擊樂器。傳統的薩巴依是在一對羊角上穿若干鐵環而成,現代的薩巴依是在兩根并排的硬木棍中部裝兩個大鐵環,每個大鐵環上又套有若干個小鐵環。演奏時,右手執木棍低端,前后左右搖震或時而上端有節奏地碰擊手肩部發聲,時而高舉一對薩巴依對碰,大鐵環敲擊在木棒的鐵皮上時,發出的是“咔”的聲音,而套在大鐵環上的小鐵環,互相撞擊,發出的卻是“沙沙”的聲響。薩巴依常作為伴奏樂器用于木卡姆和舞蹈中,這個看似簡單的樂器,是當年游蕩在南疆的阿希克(注:阿希克是游吟者、流浪藝人。他們四處流浪,以荒野和麻扎為家,薩巴依是他們唯一的,也是最信賴的伙伴。他們常常搖著薩巴依,邊走邊唱,無所顧忌,不在乎別人的眼光。若是人們覺得他們唱的歌打動了自己,給他們一個馕、一碗水或者一碗抓飯,他們會欣然接受。然后,再走向漫長的下一程2)獨有的樂器。薩巴依的聲音格外響,沉悶的鐵器碰撞中,一種輕靈之聲流露著冷漠隱約傳來,像是表達著某種渴望,在吶喊,在呼喚。詩人沈葦在《新疆詞典》中寫道:“手持薩巴依歌唱的通常是苦修者,他們盡情宣泄內心的孤苦,通過身體、手臂傳向薩巴依的木柄和鐵環,不停地抖動。薩巴依的音樂沙啞而單調,仿佛能將各種痛苦收集和綜合起來,簡化為一種單純的表達。”
手鼓(Dap),維吾爾族打擊樂器,維吾爾語稱之為“達甫”,意為敲打時發出“達”“甫”的聲音,音色清脆鏗鏘,聲音力度變化較大,演奏技巧靈活多變。手鼓早在1400年前的南北朝時就已出現,隋、唐時期隨西域歌舞傳入內地,到了清朝之后,手鼓被清朝政府列入宮廷樂隊的必用樂器,放在“回部樂”中。在《西域聞見錄》卷七寫道:“回樂以鼓為主”,“聲音抑揚高下,隨鼓而起落,而歌舞節奏之盤旋,亦以鼓為則”。長期發展以來,手鼓成為新疆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和錫伯族慶祝豐收和歡慶節日的常用民間樂器,特別是在維吾爾族的音樂中,手鼓更是不可或缺,比如在維吾爾族原始民歌的演奏中,在木卡姆奇演唱的木卡姆套曲中,在“麥西來甫”的打賣場上都離不開手鼓。除此之外,手鼓也是在維吾爾族音樂中起指揮作用的打擊樂器。
納格拉(Naera),別名那噶喇、奴古拉,漢語叫“鐵鼓”,維吾爾族打擊樂器,常與嗩吶、冬巴(大鐵鼓)一起用于婚慶迎親的鼓吹樂中。維吾爾族的納格拉與西洋的定音鼓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同源于西亞和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的罐鼓,14世紀以前,隨絲綢之路傳入,后在維吾爾族民間廣為流傳并沿用至今。清代文獻《欽定大清會典圖》中曾記載:“哪噶喇,鐵匡冒革,上大下小,形如行鼓,兩鼓相聯,左右手各以杖擊之。”納格拉鼓多為兩個一對,配置可分為四度納格拉鼓(a—d1)和五度納格拉鼓(a—e1)兩種,是維吾爾族樂舞音樂的主奏和伴奏樂器。
一、引子
《為九件打擊樂而作》4小節的引子由軍鼓和大鼓的長音引出,此段落為4/4拍,吊镲做了一個兩小節的點綴,從力度上進行反差呼應。力度ppp—ff—ppp的轉換帶著柔緩引出全曲。
譜例1(截取自總譜第1~4小節):
二、第一部分
在大鼓微弱的襯托下,鈴鼓的進入與引子完美對接,并逐漸加強力度,隨之而來的是定音鼓和薩巴依。鈴鼓、定音鼓和薩巴依都采用了固定節奏音型持續,節奏律動非常穩定。軍鼓、吊镲、大鼓則與之對比,以靈動的、不斷變換節奏來突顯出即興風格。從樂曲第17小節開始,手鼓打著傳統節奏帶著濃郁的維吾爾族音樂風格將第一部分帶入了打擊樂歡快的氛圍中,定音鼓的每一個重拍也都與手鼓的每一個重音拍進行呼應。此處手鼓的節奏重音引用了音樂劇《冰山上的來客》的序曲中節奏重音的寫法,將重音不斷地移位,目的是打破傳統,使其無規律可尋,卻又在音響效果上和諧統一。
突然,所有樂器都停止了,只剩下納格拉簡短的五小節華彩樂段,以前八后十六、前十六后八與十六分音符相結合的節奏型迅速敲擊鼓邊,像是在靜謐的空間里獨自酣暢地狂歡,這獨自的陶醉正意猶未盡時,鈴鼓、薩巴依、阿蘭鼓、軍鼓、大鼓用ff的力度同時出現,打斷了納格拉的獨處時光,并與納格拉形成“對話”模式,結束了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