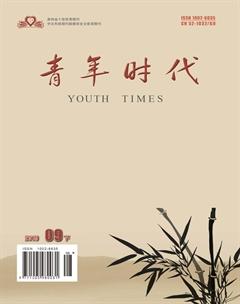新媒體傳播中個人信息保護模式探析
方皓
摘 要:新媒體傳播的數字化、互動性、網絡化在便捷信息傳播的同時也對個人信息保護帶來沖擊,本文以2014年谷歌西班牙案件中涉及的“被遺忘權”為出發點,結合新媒體傳播特點分析當前個人信息保護面臨的新挑戰,并在對“被遺忘權”的法理淵源及其國外經驗進行分析后提出我國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可有限制引入“被遺忘權”。
關鍵詞:新媒體;個人信息保護;被遺忘權
一、引言
個人信息是與個人密切相關的能獨立或通過與其他信息組合分析對信息主體進行識別的信息,其所強調的是信息的私人屬性,因而不能隨意公開、使用。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信息的傳播媒介也經歷了由傳統媒體到現如今的新媒體。信息通過新媒體傳遞的同時滋生出一系列隱患:網絡痕跡“未經許可”被記錄、個人信息“未經許可”被使用等情況時常見諸報端、網絡。為了應對這些挑戰,“被遺忘權”在歐美、日本等地區被有限制地應用于司法實踐。本文擬對這些地區“被遺忘權”的司法實踐進行簡要回溯,以期能夠從中提煉出適合我國實踐的應用啟示。
二、新媒體傳播中個人信息保護新挑戰
(一)新媒體概念及特征
新媒體的概念最早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P·戈爾德馬克的一份關于開發電子錄像商品的計劃書中[1],其相較于傳統媒體而言出現時間晚,功能特征上與既有媒體也存在差別,是基于數字化且以先進的信息傳播技術為核心所支撐的媒介或內容載體,其最大的特征是交互性,包括人與新媒體之間的人機交互、新媒體之間的的機機交互以及立足于新媒體基礎之上的人人交互。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受眾與媒體之間的相處模式以及受眾間的相處模式,增進了相互間的交流及互動,尤其是因特網的出現更是進一步拉近了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其形式的豐富性、渠道及輻射的廣泛性、傳送的精確性以及高性價比等優勢特點,使得其相較于傳統媒體具有更強的優勢,對傳統媒體也構成了顛覆,從而在現代傳統產業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但是新媒體具有的數字化、融合性、互動性及網絡化等特征也導致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即在民眾的更高參與、信息追求更大透明度的同時導致信息的過度處理及泄漏。
(二)個人信息保護面臨的新挑戰
新媒體傳播中個人信息保護面臨的挑戰主要集中在公眾知情權、公共安全保障、“知情同意”及信息使用的情景界定等方面與個人信息保護之間的沖突。
1.公眾知情權與個人信息保護沖突
現如今,人們需要從各種信息中獲取與自身相關信息或對自己存在潛在價值的信息,對信息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從而導致從信息資源中獲得知情權變得十分必要。公眾知情權包含知政權、社會知情權以及個人信息了解權。在信息時代,個人將不再是孤立原子,自身獲取信息的同時也在輸出信息。這就導致在信息流通傳遞過程中不可避免涉及到對他人信息的“窺探”,如何權衡信息的“公開”與“保護”是一大難點。
2.公共安全保障與個人信息保護沖突
在新媒體傳播中信息的流通有著更加便捷、迅速的傳播特點,也導致了傳播過程中公與私的界限劃分問題。傳統意義上的個人信息保護已不僅局限在私法領域,尤其是隱私權的保護范圍,已經開始向公法以及社會治理等領域進行擴展和延伸。出于對公共安全的保障,個人信息被廣泛收集與利用,也導致公共安全保障與個人信息保護之間產生沖突。
3.“知情同意”與個人信息保護沖突
作為對數據及信息處理行為的事前引導規則,知情同意原則被數據服務商廣泛使用,在用戶個人信息收集使用協議中頻頻出現。該原則設立的初衷,一方面明確數據活動應當獲得用戶清晰及明確的同意,即使是個人一般信息也應當符合一般人可期待性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為數據的合理利用提供法律保障,知情同意應該在更大程度上從保護信息與公眾利益出發進行權衡考量。
4.信息使用的情景界定與個人信息保護沖突
不同情景下對信息的收集、處理在涉及個人信息的敏感度方面有所差別,因此有效界定信息使用情景并進行風險評估是對個人信息保護的一個可選之策。但如何進行具體界定則是這中間的難點,況且對于信息經多次傳遞、使用后進行風險評估是難以進行的,這也將導致對使用情景分檔管控停留于紙面之上。
三、“被遺忘權”的概念界定與法理淵源
(一)“被遺忘權”的概念界定
“被遺忘權”(數字遺忘權)的概念最早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其著作《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中提出,其最初目的是為了解決數字化記憶給人們帶來的對個人信息控制權削弱的問題,通過在一定范圍內信息主體有權要求數據控制者對過期的、與現實情況不相符的信息進行刪除,以達到保護個人隱私、名譽、財產等權利的目的。“被遺忘權”重回公眾視野起源于西班牙谷歌案。在本案中,歐盟法院從個人數據定義、數據控制者界定及職責出發認定谷歌公司作為“數據控制者”必須保證個人數據以恰當、相關以及和他們被處理和(或)進一步處理的目的相關且必須進行必要、及時的更新。實際上,歐盟法院在本案中在法律效力上第一次確立了信息主體享有“被遺忘權”[2]。
(二)“被遺忘權”的法理淵源及其爭議
“被遺忘權”的設定是為了解決數字時代信息主體與信息控制者之間的矛盾,其源頭可以從西方部分文獻中得以窺探。法理淵源至少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隱私法中的控制個人信息權利,著重在于保護信息主體的人格。個人信息與隱私所包含的私人空間、私人信息及私人活動三個方面均存在交叉重疊部分,因此“被遺忘權”作為隱私權的一種延伸,對個人信息所有者所賦予的刪除權在一定意義上是對隱私權的保護。另一個是財產法中的毀損個人財產的權利,著重在于保護信息主體的財產所有權。因個人信息作為一種私人財產所具有的財產屬性導致信息所有者對信息所具有的支配控制權上附屬財產所有權,“被遺忘權”對信息所有者所賦予的刪除權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信息所有者財產權的保護。
盡管“被遺忘權”的淵源能夠從法理源頭獲得支持,但圍繞“被遺忘權”的存廢爭議卻從未停止。支持者認為,“被遺忘權”是一種公民的個體賦權,合理的遺忘機制可以為社會個體提供重新開始機會,從而對抗由信息數字技術給個人帶來的數字標簽,緩解信息技術對人類記憶機制帶來的沖擊,況且從歷史經驗來看“被遺忘權”在實踐中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保護言論自由與隱私權之間起到了合理的平衡作用。持反對意見者認為,“被遺忘權”所賦予的信息主體“刪除權”不僅使得歷史將被更改重寫,還導致了言論自由受到不可接受的沖擊,信息主體對“被遺忘權”的使用將導致私人信息與公共信息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從而使得個體在維護自己權利的同時侵害公共空間的信息流通。這是不合理也是不正當的。
四、新媒體傳播中“被遺忘權”的國外經驗
(一)美國經驗
美國針對個人信息保護存在兩種模式,即針對政府機關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的公法領域立法模式與利用行業規范來保護信息主體的私法領域自律模式,且美國以部門法為主立法較為分散[3]。在信息使用方面,美國更加強調自由、民主,也一直強調言論自由應當優先于個人隱私的保護,因此美國公法領域對個人信息主體的“被遺忘權”是持否定態度,但在美國各州的立法中則又有類似于“被遺忘權”的存在,但由于美國國體所限其也僅限于在所在州施行。
(二)歐盟經驗
歐盟針對個人信息保護有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機構,其對個人信息保護一般采取司法途徑解決或者是參加行業機構的調解。而在立法方面,則更加傾向于“保護”,因西班牙谷歌案而成為焦點的“被遺忘權”即出自《1995年歐盟數據保護指令》,且信息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應當事先征得信息主體的同意,同意原則是個人信息收集合法性的前提[4]。歐盟針對信息主體的“被遺忘權”是持有積極態度的。對于歐盟來說,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遺留的歷史問題,導致歐洲許多國家對于個人信息保護十分重視,因此其政府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也是積極作為,“被遺忘權”的設立即是源自于加強對個人信息的保護。
五、新媒體傳播中“被遺忘權”的國內嘗試與啟示
近年來,個人信息遭遇泄漏、非法收集及過度使用等情況日益嚴重,加之我國針對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全面性不足,導致個人信息保護面臨諸多挑戰。在2010年頒布的《侵權責任法》中,第36條規定了對于網絡侵權行為的處理及歸責原則。其第二款規定,第三人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害,被侵權人有權要求網絡服務者提供刪除、屏蔽、斷開網絡連接,這或可算作是“被遺忘權”的中國嘗試。
充分結合國外經驗,我國在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中可選擇有限制地引入“被遺忘權”,也即在《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將“被遺忘權”視作個人信息權的一部分,對信息主體賦予有限的自決、查詢、更正及封鎖等權限。同時,可充分借鑒美國行業自律的規范模式作為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試行經驗進行推廣。
參考文獻:
[1]彭蘭."新媒體"概念界定的三條線索[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3).
[2]孫曉煥.被遺忘權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6.
[3]鄭文明.新媒體時代個人信息保護的里程碑——"谷歌訴西班牙數據保護局"案解讀[J].新聞界,2014(23).
[4]吳曉平.新媒體語境下國外個人信息失控與保護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