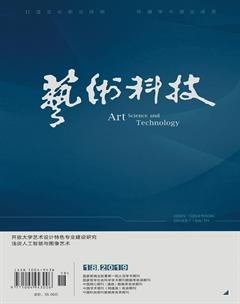智能時代的全覺互聯文本表征結構解析
李華峰
摘 要:智能時代的全覺體驗是多維度的、沉浸式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文本的互聯迭代提供了良好的傳播通路。全覺式的文本修辭方式也會成為智能技術社會應用的主要范式語法,互聯文本的6個特質構成會促使文本呈現出交叉融合的新語義生態。
關鍵詞:智能時代;全覺互聯文本;大數據;定量傳播模型
智能時代的全球互聯化以科學技術為驅動力,全覺圖像文本的多樣性從三維空間向多維空間質性轉化,藝術體驗方式與聲光電技術全面結合,跡象場域將增強現實技術,成為一種可快速迭代的虛構視像展示空間,形成了一種原生的全覺互聯文本。
全覺互聯文本結構包含視覺、圖像、文本、原生、話語、智能6個部分。
視覺信息的社會架構與語義屬性所傳達的象征指向多停留在群體觀念的視覺化,情境關聯的儀軌系統形成指義群組,在每個相應場景都可以傳達秩序意象。已知的受眾群體結構均有主題設定,主題也就容易被視覺觀念閱讀。
視覺的語義能指的話語具有共時性,觀念是線性歷時的。智能時代的媒介語言通過多向渠道分發,會形成特有的語義通路,逐漸演變成互聯互通的信息傳遞價值鏈。同時,在視覺信息語義重生過程中,會形成語義的次化語態矩陣。例如國際著名當代藝術家徐冰先生的作品《地書》,藝術家用世界范圍內收集來的標識符號,撰寫成了一本“天下同文”的視覺觀念藝術作品。這是一本超越了現有語言、族群以及國界的作品,不需要翻譯就可以讀懂,講述了一位標準白領一天的生活。這部藝術作品對群體觀念的線性思維邏輯塑造是通過諸多標識生成的,標識的表意屬性已經在此時轉換成了語義的次元化圖符,作品中的各種標識表情都成了作品中的釋義詞匯。
圖像的符號化已經迭代了符號學家眼里,圖像是一種圖像符號。在互聯技術的驅動下,符號本身的自我解構已經愈發自然而然,從能指的角度或從所指的角度去互為探討,都已經失去了意義。因為語境本身時刻在以幾何倍的方式被賦予新的存在價值,而符號的構成元素的基礎表達主體,也從人類群體意志向大數據信息主體轉化。
大數據信息主體的參照物已經在自毀標本,所有的圖像信息迭代都會以目標受眾的信息采集方式重新生成,如同淘寶網首頁的產品平面廣告,都是后臺數據庫根據大量用戶使用痕跡及習慣,進行產品銷售海報設計。在智能時代的圖像生成與傳達,目標受眾的互聯場域在逐層地類數據化。
智能互聯語境中,圖像言語句法也從傳統的閱讀理解成為體驗表達,言語已經不再是間斷的、離散的,而是升級成了“象形”與“意象”的融合語態。例如Orz這個圖像詞匯,是失意體前屈的縮寫,是一種源自日本的網絡象形文字。這個詞匯的形狀像是一個人被事情擊垮,跪在地上,是用來形容被打敗很郁悶,一種失意或沮喪的心情,同時這個圖像詞匯還表示佩服及膜拜的意思。“Orz6”表示“我(O)認(R)栽(Z)咯(6)”,“Orz”在此時儼然成了一個詞根,然而這個詞根被賦予意義,正是不同群體的共識與異議中激蕩自發形成的語義詞根。這種識別方式既是象形的,又是表意的,還是可拼讀的,而且,通過互聯網傳播超越民族文化意識,形成互聯語態共識。
文本語態從傳統的表達與內容層面演變成了組構式的修辭語法,造型本身已經被字符化,文本自身在表達層面和內容層面呈現了互生狀態。文本的一致性導向功能也在逐漸自我削弱,協議化原則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例如,智能手機的屏幕即是一個可以隨時迭代的協議化場域,視覺界面在概念、主題、主題、網絡4個層面引發的共生效應會在信息傳播中演化為“物理源型”與“心理場域”之間矗立的共軛界面,是物理世界與心理世界轉換的關鍵觸發界面。
藝術家葛宇路因為一條“葛宇路”,把自己及自己的姓名變成了一件可以自說自話的藝術作品,藝術家在北京百子灣附近一條長約452米的小路上,他給這條路命名為“葛宇路”,“葛宇路”也被收入地圖。作品帶有限速、禁止停車等交通標識,使用“葛宇路”也可以準確導航、訂餐及收發快遞。當《葛宇路》作為畢業作品,在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展展出,一篇《如何在北京擁有一條以自己命名的路》的帖子開始在網上熱傳,隨之而來的是“葛宇路”路牌被拆除。這個“葛宇路”的協議化場域生成,即是互聯文本語態的即時共生,通過大數據的無定向分發,“葛宇路”被賦能成立了。但是由于“物理源型”藝術家的自白,又被“心理場域”的制造者——社會受眾,迅速瓦解掉,僅僅存留了一個思維文本痕跡。
原生對照世界的“觀實”存在,如同賦予文本的意義就是人類制造文本的目的。而文本的原生屬性具有“意識的模糊性”,在原生主體與原生元素之間,原本是無邊際的場域。原生信息的認知軸線分為運動、形狀、場深、幻向。
原生文化流變的核心是信息迭代定量傳播模型,是一種二元對立的贗相性結構,創造了一種“互聯網圖景”。原生的聚合性具有“零釋義”的圖景態度,然而,原生圖景的跡象針對類比性、模仿性、一致性。原生將一種“相似性”透視結構應用于所表現的互聯空間維度。例如,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小說里的設定用語有“三體人”“智子工程”“宇宙社會學”“低光速黑洞”“黑暗森林”等,以及紀念對照,如危機紀元、威懾紀元。整部小說都是圍繞人類終結的原生命題展開的,所有的設定也都具有時間與空間的尺度重合。
話語映照互聯世界的方式,在可感的場景范圍內,話語成為互聯的唯一在場方式,在人類已知的文明歷史、可感場域內,話語景觀媒介合成狀態在大眾的目光之下,承載著巨大的話語信息量。
每部智能設備都如同一臺全新的話語裝置,作為設備的持有者,是一個新世界的觀者,話語互聯的經驗持續處于極端抽象和迭代重建中。互聯話語的修辭手法始于“迷思”,止于“重復”,每個決定性瞬間都充滿了信息的矛盾,受眾讀取信息的方式與話語的意義、空間、時間形成特有的時空觀。
話語發展的典型瞬間分為起、承、轉、合、離5個階段。受眾得到的話語結構是受眾本身在意識環境中形成的語境分層,簡單化范式的生活環境內,人類以分離的、還原的、抽象的、彌散的精神狀態生活,在控制論的語境中遇到了話語更新構想的可能,這種構想呈現了互聯文本的機體論基礎。例如,由藝術團隊Teamlab打造的“Teamlab Borderless”是一個無邊界的藝術作品,所謂的“沒有邊界的藝術”,即藝術作品不受展示空間的限制,與其他藝術作品相互交流、相互影響,打破作品與作品之間的界限,進而相互融合。諸多作品相互交織疊加所產生的無邊界話語,讓觀眾可以置身在藝術作品中體驗虛構話語的魅力,置身于作品中,觀眾已經成為藝術作品的一部分。
智能互聯會超越傳統經典的藝術語境,人類在科學發展的路上,會看到經典與科技的不共存屬性及共體雙生,彼此矛盾存在。在科技發展過程中,人類看到的更多是統一性與差異性、偶然性與必然性。互斥關系的“整體論”讓智能互聯在不斷尋求最基本的覺知單元,把智能系統分解為思維邏輯的范式節點。
例如,“漫步在雨中而不會被淋濕”的互動裝置藝術作品《雨屋》曾經在倫敦和紐約引起轟動。該作品的獨特之處在于:當觀展者置身于其中時,可以在大雨中自由穿梭,卻絲毫不會被淋濕。《雨屋》將“雨”這一自然現象變成了人造景觀,利用智能交互技術,在參觀者走入“雨”中,作品中安裝的攝影機會根據參與者的各個身體部位制作3D影像,由圖像信號轉換成控制信號,進而控制“雨”的分布;除了視聽效果體驗外,吸引參與者能夠自己控制“雨”,同時也被“雨”控制。
智能時代的互聯文本是全覺認知的,文本一旦生成,就處于持續的更新迭代升級中,每一種文化形式都是互聯的“程序”與“通道”。程序是應用在秩序的環境中,由固定的行為感知序列構成;策略是用在有序性與無序性共同支配的創造環境中的行為方法。
智能文本已經為人類的信息交流提供了科學技術基礎,然而文本的意義不在于已經存在,而在于傳播前后的效果。互聯文本是人類認知社會定量信息的手段,核心問題是信息的自我媒介化程度,信息的媒介化程度越高,說明信息傳播網絡越高效。
參考文獻:
[1] 韓叢耀.圖像:一種后符號學的再發現[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 埃德加·莫蘭(法).復雜性思想導論[M].陳一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