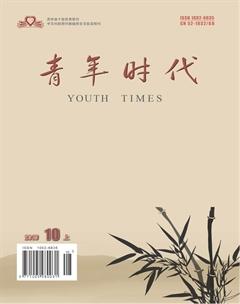黃老學派的古代戰爭辯證法思想
李飛
摘 要:黃老學派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對戰爭問題作出了深刻的探討。這些戰爭思想里面包含著一系列辯證法的思想因素。主要包括興兵時機問題中的辯證法思想,戰爭性質與軍事實力的辯證關系,軍人素質中所包含的矛盾因素,將領與士兵之間的辯證關系,軍隊素質與軍人數量的辯證關系,戰術中的諸多矛盾因素,戰術中的內因與外因關系等問題。
關鍵詞:黃老學派;戰爭;辯證法
一、引言
黃老學派是形成于戰國時期,鼎盛于漢初的道家學派的一個分支,《黃帝四經》《鹖冠子》是它的代表作。另外《呂氏春秋》就其主體而言,也是黃老學派的著作,它的思想體系和基本觀點與《黃帝四經》《鹖冠子》是一致的,漢初的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也包含了許多黃老學派的思想資料。
二、黃老之學與戰爭思想
黃老之學講求治道,即所謂“君人南面之術”,主要是一種政治哲學。它的政治理想是對內實現國家強盛,對外實現王霸政治。所謂王霸政治就是維護舊的分封制的政治,國家之間的攻伐不是為了兼并他國,而是為了恢復理想的政治社會秩序,而這個秩序是以西周的分封制為藍本的。實現王霸政治,離不開戰爭手段。黃老學派對戰爭的討論,沒有僅僅停留在把它作為國家對外活動的一種手段,而是進一步把戰爭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進行自覺的研究。黃老學派可以說具有自己獨立的成體系的戰爭思想,這些戰爭思想里包含著一些辯證法的思想因素。
戰爭的直接目的是取得勝利。黃老學派認為要取得勝利,必須注意興兵的時機。《黃帝四經》說:“圣人之功,時為之庸,因時秉宜,兵必有成功。”又說:“天固有奪有予,有祥福至者也而弗受,反隨以殃。”抓住了時機,戰爭就會成功,貽誤了時機,反而要遭受禍亂。可見,時機是決定戰爭勝敗轉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把握興兵的時機要做到兩方面,一個是時機沒有到來時,要安心等待。《黃帝四經》云:“不曠其眾,不為兵邾,不為亂首,不為怨媒,不陰謀,不擅斷疑,不謀削人之野,不謀劫人之宇。慎案其眾,以隨天地之從,不擅作事,以待逆節所窮。”這是說在面對敵國因為不行正義發生混亂時,不要急于做戰爭的發動者,不要做禍亂的肇始人,不要主動算計敵國的領土宮室,而要穩定自己的臣民,遵從客觀規律,等待敵國因為不義而走向窮途末路。另一個方面是時機到來時,要果斷地抓住它,不能猶豫不決,所謂“因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這兩個相反的方面要互相配合,才能把握時機,從而獲得戰爭的勝利。這種主張是辯證的。
戰爭要取得勝利,除了時機問題,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戰爭的性質問題,一個是軍事實力問題,這兩個問題也是一對辯證的矛盾。黃老學派的戰爭主張是為王霸政治的理想服務的,王霸政治的實質就是維護傳統的社會與人倫秩序,合乎這個秩序,黃老學派稱之為“義”,所以黃老學派所主張的戰爭就叫“義兵”,而那些只為爭奪名聲與利益的戰爭是黃老學派所反對的。黃老學派認為義兵是必然會勝利的,戰爭是否合乎義是它勝利與否的根本,也就是說戰爭的性質對戰爭的勝敗具有決定作用。
雖然如此,卻不能因此否定軍事實力的作用。《呂氏春秋·簡選》篇說:“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斗因用惡劍則不可。”片面的戰爭理論認為只要符合義的要求,哪怕是沒有經過訓練的老弱罷民,拿著十分落后的武器,也可以戰勝訓練有素、武器精良的敵人,《呂氏春秋》認為這是不懂兵法的人的論調,這些人大約是看到許多國家軍事實力雖強,但卻最終失敗,才形成這種觀點。但是這些國家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軍事實力不重要,而是因為沒有把軍力用在正義的地方。因此,否定軍人素質與武器裝備的重要性是不對的。這就好比用鋒利的劍去擊刺,如果沒有用好這把劍,那么是刺不中的。這把劍從效果上來說與質量低劣的劍沒什么區別,但因此在戰斗時特意選擇惡劍則是不可取的。
軍事實力與義兵的關系是幫助的關系,《簡選》說:“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不)為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軍事實力對義兵具有輔助的作用,不能完全倚靠軍事實力,但也不可以忽略軍事實力。
三、黃老之學與軍事實力
黃老學派對戰爭性質與軍事實力關系的理解是辯證的,但是它對戰爭性質的區分仍然受到王霸政治的局限,決定戰爭勝利與否的戰爭性質應該根據它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來作區分,而按照王霸政治理想所作的義與不義的區分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
由于黃老學派對軍事實力的作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進而對軍事實力的構成要素作了一些討論。軍事實力有許多構成要素,其中軍人素質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軍人包括兩類,一類是將領,一類是士兵,對這兩類人的軍事素質,黃老學派有不同的要求。
對于將領,《淮南子》說:“故鼓不與于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于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于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這有點類似于黃老學派所主張的“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認為將軍的地位與下屬軍官不同,只有不同才能成為他們的統率,而只有成為他們的統率,才能把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作用綜合起來,滿足“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的要求。這些不同的能力與不同的作用有時候是完全相反的,就像春天與秋天,夏天與冬天一樣,但是軍隊的統率要把它們都統一起來,才能應付復雜多變的戰爭情況。也就是說,在將軍的軍事素質里面包含著諸多對立統一的矛盾,這是辯證法的思想。
《淮南子》所說的“五行”也是這樣的矛盾:“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之所以柔而不可卷,是因為不是一味的柔,需要的時候也會剛,之所以剛而不可折也,也是因為有柔配合。仁與柔比較接近,仁也與它的反面相配合,這樣才能做到仁而不可犯。這些思想都是富有辯證意味的。
士卒的軍事素質有賴于將領對士卒的管理。在管理士卒方面,黃老學派主張威義并行,賞信罰明。《淮南子·兵略》:“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當作“義”)并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這段話所說的威義、文武、賞罰都是矛盾的兩方面。士卒是從民眾中產生的,也是由民眾供養的。軍力的強大與否取決于民心與軍心所向。所以說“兵之所以強者,民也”,而要凝聚軍心民心,就要讓軍民受到“義”的感召。“義”是一種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中各個階級可以按照不同標準保證其利益。與此相反,在不義的社會情況下,各個階級的利益都會受到侵犯,處在底層的民眾尤其得不到生命財產的保障。因此,民眾愿意為“義”去反對“不義”,甚至不惜身死。所以說“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但“義”是一種沒有強制力的東西,在遇到困難危險的時候不能保證每個軍民都能不屈不撓。因此,還需要在“義”之外,加上“威”,“威”就是統治者加在被統治者身上的一種強制力,有了這種強制力才能保證軍民去實現“義”,所以說“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可見,“威”和“義”是一種辯證的矛盾。“義”是一種政治、倫理的感召力,這在古代叫作“文”,“威”是一種暴力的強制手段,這在古代叫作“武”,文武是不同的,但是兩方面要配合起來,才能使軍力強大,進而戰勝敵人。所以說“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并取”“威義并行,是謂至強”。這種把對立的兩方面配合起來使用的作法,是符合辯證法的。
將領與士卒的關系也是一種辯證的矛盾關系。對此,黃老學派也頗為注意。《淮南子·兵略》篇說:“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這段話把將與卒比作是心與體的關系,可見兩者是既區別又互相聯系的一個整體。他們的區別在于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將起的是心的作用,負責全局,出謀劃策,統率士兵;卒起的是體的作用,負責具體的、實際的作戰任務,聽從命令,實現將領的意圖。兩者也是有聯系的,體現在兩者是互相依賴的。將要依賴于卒,否則其意圖將無從實現,所以說“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也要依賴于將,否則將無法與敵人作戰,所以說“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在這個矛盾體之中,將似乎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從“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來。《淮南子》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將與卒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又能看到二者地位的不同,這些都是具有辯證眼光的。但是它對將領的作用有所夸大,帶有一定的唯心主義色彩。
除了軍隊素質外,軍人數量也是構成軍事實力的重要因素,軍隊素質與軍人數量構成一對辯證矛盾,黃老學派對此有較全面的認識。黃老學派反對單純強調軍人數量的做法,認為只重視數量,而不重視素質,不但不能保證作戰勝利,還會產生禍患。《呂氏春秋·決勝》云:“軍雖大,卒雖多,無益于勝。軍大卒多而不能斗,眾不若其寡也。夫眾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它所說的“不能斗”,就是軍人素質問題。
黃老學派雖然反對單純強調數量,但也反對完全否定軍人數量的作用,如果軍人能齊心諧力,那么數量眾多的一方必然戰勝人數較少的一方。《淮南子·兵略》:“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眾,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眾。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眾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眾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眾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單個的人與人之間的戰斗力是十分接近的,并不能像水澆在火上一樣,輕而易舉地將對方消滅。因此,想要用人數少的軍隊去對抗人數多的軍隊,顯然是不能成功的。兵家所說的人數少的軍隊可以對抗人數多的軍隊,是就將領方面而言的,不是就兵卒方面而言的。有的將領帶的兵多但是收到效果卻和帶的兵少一樣,這是因為人員作用發揮得不齊;有的將領帶的兵少而收到的效果卻和帶的兵多一樣,這是因為人員能夠較好地協作。如果每個人都能發揮他的全部作用,那么以少勝眾是不可能的。
在軍人數量與軍隊素質的關系中,黃老學派顯然認為軍隊素質是更為根本的。《呂氏春秋》所說的“軍大卒多而不能斗,眾不若其寡也”就是強調軍隊素質比單純的數量更為重要。
黃老學派的這些思想看到了軍隊素質與軍人數量這對矛盾的對立統一,也看到矛盾兩方面的主次分別,并且對它們主次地位的認識也是準確的,是比較深刻的辯證法的思想。
在具體的戰術上,黃老學派強調要注意處理一系列的矛盾,注意矛盾的轉化。《黃帝四經》云:“毋藉賊兵,毋裹盜糧。藉賊兵,裹盜糧,短者長,弱者強;贏絀變化,后將反施。”《鹖冠子·世兵》篇說:“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參之天地。出實觸虛,禽將破軍,發如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搗虛,殷若壞墻。執急節短,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與道翱翔,翱翔授取。錮據堅守,呼吸鎮移,與時更為。一先一后,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摶?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縣。兵以勢勝,時不常使。蚤晚絀嬴,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
這些論述中所說的短長、強弱、嬴絀、明微、天地、進退、虛實、死生、鎮移、先后、左右、陰陽、得失、蚤晚、遲速、合散、消息等都是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體,黃老學派強調要注意矛盾雙方的不同作用,根據不同的時機、場合綜合利用,注意它們之間的轉化,促進有利于自己的轉化,而避免不利于自己的轉化。雖然黃老學派沒有逐一解釋如何利用這些矛盾以及如何對待它們的轉化,但這些主張無疑都是深具辯證眼光的。當然,這里面也混入了一些形而上學的、神秘主義的因素。
《黃帝四經》所說的“一朵一禾”也屬于這樣的矛盾。《黃帝四經》說:“我將觀其往事之卒而朵焉,待其來事之遂而私焉。一朵一禾,此天地之奇也。”“朵”就是“動”,“禾”就是“和”,從總體來說,動與和都是在敵人采取行動以后我方再采取行動的意思,以后制先,這是黃老學派一貫的一個戰術主張。《淮南子·兵略》說:“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鱉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圣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后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也是以后制先,以靜制動的意思。這個戰術主張雖然有忽略先機的一面,但它強調從表面的被動中發掘出有利因素,也具有辯證意味。
雖然總體來說,動與和都是后以制先的意思,但動與和還有些不同,動是根據敵方已經做出的行動而采取對策,和是等待敵方做出行動再采取對策,二者在時間上有已發生與未發生的區別。在主動性方面,動的方面比和的方面相對主動一些,因為動的根據已經發生,動即將付諸實踐,而和的根據尚未發生,還無從付諸實踐。所以動與和是相反的兩方面,把這兩個相反的方面結合起來,運用到實戰中,是具有辯證意義的。
黃老學派在戰術方面,注意到了內因與外因的矛盾。《呂氏春秋·決勝》篇說:“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己與彼的區別就是內因與外因的區別,“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就是注意到內因與外因都是影響勝敗的因素。然而在兩者中,“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就是說內因比外因更為根本。最后,把兩者結合起來,“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就能避免失利而取得勝利了。這也是值得肯定的辯證法思想。
參考文獻:
[1]黃樸民.戰國黃老學派及其軍事思想[J].管子學刊,1994(4):55-60.
[2]嚴武.黃老學派的興起及其法律思想[J].法商研究,1989(1):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