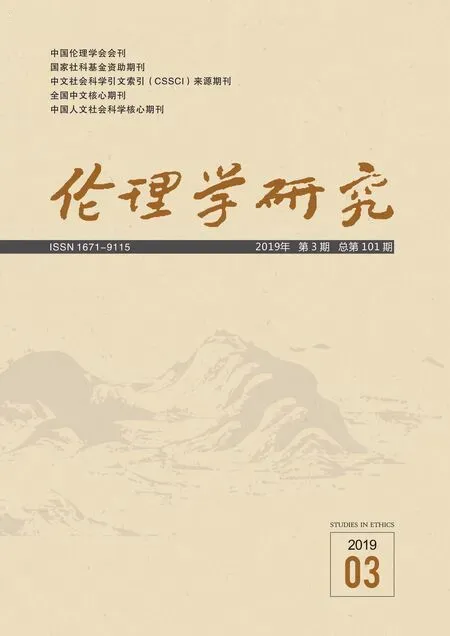康德實踐哲學的義理構建及其邏輯跳躍
詹世友,由 田
康德的實踐哲學具有一個完整的義理系統,從先天的道德法則、善良意志、道德義務、本體自由,到人性(humanity)的目的性地位、德性的本質;從自然的目的理念、歷史實踐、人性發展,到人的總體道德化,每個環節都具有共享的純粹理性的先天法則前提(對其進行表象即為道德法則),并在道德法則的指導下,落實到人的實際生存活動、人性發展及其人類的歷史發展,表現為一個具有宏大理論視野和實踐場域的系統。這個系統以厘定道德價值的純粹先天的基礎為出發點,又落實到人們的日常道德實踐之中,考察人們怎樣才能彰顯出自己作為一個有理性者的尊嚴,拯救人類本有的自由,充分賦予人性在實踐哲學中的關鍵地位,把它的發展或文明化看作人類向道德發展的階梯,并從自然目的論出發,以人性的豐富性及其內涵著的沖突因素作為基礎,來考察人類的歷史實踐,以及人類邁向總體道德化的無限進展的愿景。在他的實踐哲學中,貫穿著本體與現象的劃分、自然與歷史的交聯、文明化對道德的促進。可以說,康德的實踐哲學系統義理嚴整,漸次展開,首尾一貫。如果我們不能梳理其其義理的整體系統,而只是片段式地考察其某個學說,就必然會誤解其實踐哲學的核心關切。只有通過對其整個義理系統進行考察,我們才能深入、落實地理解到康德實踐哲學的本真旨趣,并廓清對其實踐哲學的某些誤解,同時也能揭示其某些邏輯上的不當跳躍。
一、一個總前提:物自體與現象的劃分
1.物自體與現象的劃分,對康德整個哲學來說意義重大,用叔本華的話來說:“康德的最大功績是劃清現象和自在之物[兩者之]間的區別”[1](P569),從道德哲學上說,其功績就在于他“論述了人類引為不可否認的道德意義是完全不同于、不依賴于現象的那些法則的,也不是按這些法則可以說明的,而是一種直接觸及自在之物的東西”[1](P575),這關涉到我們把本體界作為道德價值的來源,所確定的是對所有有理性者都具有普遍約束力的道德原則,還是一些依人們的感性偏好變化而變化的權宜之計。如果說,在認識領域中,物自體的假設只是說明我們所能認識到的并非物本身而是經驗現象,并可以說明我們既具有先天的感性形式和先天的知性形式作為知識的來源,同時感性經驗也是我們知識的來源,從某種意義上說,物自體的假設的作用是限制知識,防止我們追求對物自體進行認識的僭妄,從而喚醒我們在知識論上的獨斷論迷夢,那么,在實踐領域,物自體的作用卻是肯定的、積極的,它要產生一個能夠對所有有理性者的意志都具有約束力的先天的純粹理性的普遍法則。這是康德實踐哲學的總前提,它指引著康德實踐哲學系統的義理展開和演進。
在實踐哲學中,自在之物或物自體就是理性世界,也就是本體界。純粹的理性世界與現象世界的性質正相反,現象世界的特點是多樣性的、特殊的、變動不居的、相對的、受自然必然性支配的,理性世界的特點則是同一性的、普遍的、超時空的、絕對的、受自由規律支配的。理性世界和現象世界是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兩種角度,并不是說真的存在這樣兩個世界。如果我們只從現象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則我們就無法拯救自由,因為一切都被自然必然性所決定,我們的行為也都是出自一個自然原因的結果,我們對此就沒有責任,于是人與其他動物就沒有本質區別;同時我們也就無法得到對所有有理性者都有約束力的普遍道德原則。理性世界是我們的自主性、自發性的根源,我們作為一個有理性存在者,具有不受到來自經驗性的感性偏好的決定的自主意志,我們自作主宰,我們在現象上受到自然因果性的決定的同時,可以在本體界中服從自己的理性法則或者自由法則。不這樣看待我們的人類的特性,我們就無法彰顯自己作為一個有理性者的尊嚴。
2.普遍的道德法則來自先天的純粹理性。所謂純粹,就是不摻雜任何經驗因素。關于為什么純粹理性會有普遍的法則,我們可以從知性法則中得到說明。在說明我們為什么能夠形成對經驗世界的知識時,康德認為,我們具有先天的知性法則,在它們沒有范圍經驗雜多時,它們就是一種純粹的形式性法則。知性是理性在經驗中應用做成知識時的名稱,在超越經驗現象界而有所作為時,其名稱就是理性,或者說,理性就是知性的超越經驗使用時的名字。在這時,它仍然只有先天法則。但由于這種先天法則指向對意志的約束并訴諸行動,所以,其作用是實踐的,而不是認識的。在這里,理性的先天法則仍然只能沿用知性形式的邏輯概念,如質、量、關系、模態。在質上,它的法則就是個體性,在量上就是普遍性,在關系上就是自由的因果性,在模態上就是必然性(必要性),它們不應用于任何經驗性質料之中,而是使這種經驗性質料以應然的秩序而出現。
3.理性法則只對意志具有決定作用。在康德的實踐哲學中,由于道德價值出自于主觀準則的性質,而準則又是意志的規定根據,但這種準則只能到本體界尋找,而不可能在現象界如感性偏好中去尋找,所以,這種準則就必須是客觀的道德法則,只有它可以直接作為規定意志的根據。意志就直接關乎實踐,即行動,所以,意志是實踐的能力。因為它受到理性法則規定而不是感性偏好規定而行動,所以它就擺脫了自然必然性的制約,體現了其自由。顯然,這種自由只有從把人作為具有理性本性的存在者來看才是可能的,而從人作為感性經驗的存在者來看,人是不可能有自由的。這種自由可名之為本體自由。如果我們說,本體界的性質是同一的,無差別的,那么,純粹理性與具有自由性質的意志是同一的東西,所以,就純粹理性自身就有實踐能力而言,意志就是實踐理性。所謂純粹理性就有實踐能力,是指純粹理性自身的法則能夠直接決定意志,從而訴諸行動。
理性法則出自于先天,但它并不范圍感性雜多而做成關于事物的知識,而是針對一種理性的理念(即在經驗中沒有對象物),從而表現為讓感性經驗事物按照應然秩序出現的理性命令,這種秩序是自然世界中按照自然必然性所不會出現的事物的秩序,所以,有理性者是這類道德事物秩序的肇始者,一而無對,是自作主宰,而不受任何其他的存在者的支配與決定。然而,本體界或者理性世界是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即中國古人所說“不聞不睹”“無聲無臭”的領域,所以,對那些只相信經驗的事實的人而言,理性世界就是純粹的虛構,他們不會相信理性法則對人的意志的決定作用,而必然認為只有情感、功利的計算等等才能決定我們的意志的趨向。而實際上,對道德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得見的,而正好是這種看不見的、先天的、對所有有理性者都有約束力的普遍法則。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學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人們對這種看不見的普遍法則獲得一種領悟,并且信得及。對只相信感性經驗事實的人,康德認為,只要提醒他們,為什么有人會感到有良知的拷問,對某種崇高的、純粹的普遍法則有敬重之感,就會使之從專注于感性偏好、功利計算等中回轉,而思入本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拯救人的自由和道德。
4.在康德的實踐哲學中,劃分出了許多領域的本體與現象,這表明他對這一點十分看重,也是理解他的思想的關鍵。比如,在法權學說中,他區分了“作為現象的占有”和“作為本體的占有”:在現實中對不屬于任何人的對象進行占領,“這種占領就是空間和時間中對任性的對象的占有,因而是我把自己置于其中的占有(possessio phaenomenon[作為現象的占有]”[2](P267);而一種占有如果是純然法權上的,即是出自實踐理性的,“故而在什么是正當的這一問題上可以排除占有的經驗性條件”[2](P267),則這種占有就是possessio noumenon[作為本體的占有]。顯然,只有符合“作為本體的占有”的條件,“作為現象的占有”才能具有正當性;在國家學說中,康德也提出了“作為本體的國家”和“作為現象的國家”,認為那種與人的自然法權相吻合的憲法的理念,“亦即服從法律的人們聯合起來,同時也應當是立法者”的那種共同體,就是“respublica noumenon[作為本體的國家]”,而按照這個理念組織起來的一個公民社會,就是這個理念按照自由法則,通過經驗中的一個事例的展現,這就是“respublica phaenomenon[作為現象的國家]”[3](P88)。這種國家在現實中,是經過了多少爭斗和斗爭之后才能艱難地獲得的;在德性學說中,他也認為要區分“作為本體的德性”和“作為現象的德性”。他說:“在同一個德性作為義務地(依照其合法性)行動的熟練技巧被稱做virtus phaenomenon[作為現象的德性],而作為對出自義務(由于其道德性)的這些行動的堅定意念被稱做virtus noumenon[作為本體的德性]。”[2](P15)即是說,“作為現象的德性”是在外在行為中所表現出的合乎義務的行為特征,而“作為本體的德性”則是履行義務的內在意念,其主觀準則就是要履行客觀義務,等等。在康德的思維視野中,現象世界的行為是本體界的顯象,是本體界在現象世界中的個別表現。這種個別表現顯然可以被看作是體現了本體界的某種性質,或者說我們通過現象界的這種個別表現可以獲得領悟本體界的某種指引線索。現象中的行為表現可能只會符合外在的法則(即康德所說的合乎義務的行為),其主觀準則可能并不完全就是客觀的法則。從道德上說,本體界的事物就是人格,就是一種沒有任何限制、出自先天的純粹理性法則的品質。而現象界的人性表現則是人格的經驗現象及其發展,它們會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甚至就表現在追求經驗幸福的行為之中,但是表現于現象界的行為品質只有能夠體現出對理性法則的遵循,才能說是有道德意義的,所以這樣的行為就必須被約束在普遍道德法則之下。當然,這類行為所體現的只是外在道德,然而,如果我們不斷地這樣去做,也有望變成內在的道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法權的形而上學學說,即人們在普遍法則的約束下使大家的外在自由能夠并存的條件,就是道德形而上學的一部分。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總是覺得康德混淆了法權學說、德性學說、政治哲學、歷史哲學、人類學和道德哲學。實際上,對康德而言,法權學說就是道德形而上學的針對外在行為的形式部分,德性學說就是道德形而上學的針對人的內在品質的形式部分,而實用人類學、歷史哲學、政治哲學就是道德哲學的經驗部分。
二、形而上學層面的道德原則推演
1.在本體界,我們首先考慮我們的意志怎樣才是善良的。他說:“在世界之內,一般而言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一個善的意志之外,不可能設想任何東西能夠被無限制地視為善的。”[4](P400)。它與意志所能運用和利用的各種好的自然稟賦、性格或幸運的賜予相比,是無條件的善。也就是說,良好的自然稟賦如那些可稱為精神的才能的東西,如知性、機智、判斷力,好的性格如下決心時的勇氣、果斷、堅韌,以及在情緒和激情方面的節制、自制、冷靜的思慮等等,或者由幸運所致的權力、財富、榮譽,甚至健康和各種組成幸福的事項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意志在訴諸行為時所能運用的(如自然稟賦和性格),或者能夠有助于這種本身善的意志的(如幸運所致的好處境),它們都只有相對的善,而不是本身就善或者絕對的善,因為如果沒有善的意志來糾正它們對心靈的影響,它們就有可能變成惡的。這充分說明了,我們的行為的道德價值都是來自善的意志的,而不是來自這種自然稟賦、性格或者幸運的結果。所以,善的意志是這些相對的“善”的前提條件。善的意志超出塵表,只能被設想是處于本體界的,也就是處于理性世界的,所以,“理性的真正使命必須是產生一個并非在其他意圖中作為手段,而是就自身而言就是善的意志”[4](P403)。
2.這種善的意志實際上就是要讓先天的、純粹理性的普遍法則成為直接決定它的根據,而不受到任何其他東西的決定。這樣的意志是一種理念。而人的意志卻是一種并不純粹善的意志,因為它會受到感性偏好的刺激,甚至因為我們無法確知的原因而被感性偏好所決定。但是,任何一個人因為有理性,都會對道德法則表示一種敬重,即使我們并不能做到在任何情況下都遵守它。所以,我們可以從義務出發,來思考我們的道德原則。在這里,人的意志的實際情況成為一種參照,那就是我們會有對普遍的道德法則的敬重,出自這種敬重,我們會了解到我們必須做什么,這就是我們的義務。所以,康德說:“義務就是出自對法則的敬重的一個行為的必然性。”[4](P404)“這個概念包含著一個善的意志的概念,盡管有某些主觀的限制和障礙。”[4](P403)我們做符合義務的事情,卻可能有兩種動機,即“出于義務”和“合乎義務”。完全出于義務而行動的意志就是善的意志,我們研究道德哲學,就是為了產生善的意志,或者弄明白善的意志的性質是什么。在解釋出于義務和合乎義務的行動時,康德借助于人們的普通理性,他認為,普通理性就足以分辨出這二者來。
3.參照人的意志的實際情況即它并不是一種純粹善的意志,我們還可以順利地進入到絕對命令式。假言命令和絕對命令的區別,與合乎義務和出于義務一脈相承。其核心是,因為我們的意志不是純粹善良的,所以,絕對命令對我們而言,就是一種應當。因為我們不能自然而然地遵守道德法則,故絕對命令對我們的意志是一種強制。
4.康德提出了三大道德律令,并認為這三大道德律令實際上是等值的,它們只是分別從形式、質料、質料與形式統一這三個方面加以不同的表述。這個說法到底是否合理?
所謂形式,就是僅僅關涉到道德法則的純粹形式,核心是說,要能夠把客觀的道德法則作為自己的主觀準則,即“要只按照你同時能夠愿意它成為一個普遍法則的那個準則去行動”[4](P428)。這個命令是直接針對意志的,要求用道德法則的純粹形式來作為意志的規定根據。實際上,道德法則本身也只有形式,它本身沒有涉及任何質料或對象。用道德法則的形式規定意志,就是要使其主觀準則擺脫任何感性偏好等質料性的內容,而形成意志的動機。但是,這只是消極性的,只保證意志的意向或意愿是善良的,為意志作出行動奠定一種善良價值的意動傾向。康德在說明此律令時所舉的4個例子,只是說明我們遵循什么樣的準則是不具有道德價值的,從而反證遵循其相反的準則即普遍的道德法則才是有道德價值的,并且只能給出一些形式性的規定,如自己的主觀準則普遍化之后不能自相矛盾等等。
同時,由于在現象界,預先只有自然規律在起作用,所以,道德規律并不能規定行為和結果按照一種本來沒有的自然規律而出現,而是要使“作為事件的活動的聯系是遵從道德規律的,就像自然規律純粹遵從其普遍性一樣”[5](P184)。比如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行動,這種種行動在現象界都是遵從自然規律的,但是,這種種行動之間的聯系卻可以服從道德規律,如我們在行動中要把保持誠信作為自己的義務,而且這種義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普遍必然的要求,這種普遍性就像自然規律的普遍性似的。因為行為及其結果都是落到現象界的,所以,要說明具體的有道德價值的行動,還需要參照自然法則來進行。其形式性就在于使按照道德法則而行動的后果可以得到持存,可以按照自然法則而存在,而不是自我取消或走向相互矛盾和沖突。比如我想通過許假諾而度過目前的難關,那么,我們就可以看一看,如果每個人都這樣行事,那么,這件事能按照自然規律而普遍存在嗎?當然不能,因為大家都這樣做,則許諾這件事在現實中就不會存在了。所以,康德認為這第一個律令還可這樣表述:“要這樣行動,就好像你的行為的準則應當通過你的意志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似的。”[4](P429)這個公式并不是單獨的一個命令式,而是第一律令的變式。
為什么需要“人是目的”作為第二個道德律令?這是因為,道德律令的最重要作用是要用在人身上。人的任何行為都是有目的的,道德行為自然也不例外。因為目的就是意志的對象或客體,所以是質料性的。這就牽涉到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中是如何看待目的的問題。按照康德的想法,行為的絕對的道德價值只體現在道德法則對意志的決定之中,人因為意愿而善,至于行為的結果是否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則與行為的道德價值無關。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去實現某些特定的目的如獲得某種快樂量的增加或內心寧靜等等,并以此作為規定我們意志的根據,則我們的行為就與道德價值無涉(當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但是,目的是人設定的,所以,人是設定所有目的的主體,以道德法則來直接決定自己的意志而作出的行為也要追求某種目的。于是,我們現在就應該考察純粹的道德行為與目的的關系。
第一,就我們一定要作出道德行為的意愿而言,作出這種行為本身就是目的,而能作出這種行為的有理性者就體現出了一種人格(即不從感性偏好吸取動機而用道德法則來直接決定自己的意志的品格),從而可以說,彰顯出人格尊嚴,就是我們的純粹的道德意愿的目的本身。但這一點是同義反復,沒有說出更多的東西,無非是說:我們要做出道德行為,就應該把道德行為做出來。但這讓我們看到了我們的道德行為的意向的自身目的性。
第二,并不是只有人格是目的自身,實際上,就人作為一種有理性者來說,我們的本性或者自然稟賦是我們成為人的基礎本質,其存在和發展就是我們的目的本身,它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目的。所以,康德說:“有理性的本性作為目的本身而實存。”[4](P436)也就是說,人的自然稟賦是我們作為有理性者的本性,我們有義務促進它們的發展,把它們提升到人性的狀態,這就是我們的目的本身。
所以,人是目的的公式關乎人的完善。它是這樣表述的:“你要如此行動,即無論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還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時候都同時當做目的,絕不僅僅當做手段。”[4](P437)①它也要能夠被普遍化,即任何違背這個律令的行為動機都是不具有道德價值的。因為“人格”是在本體界的,有尊嚴的,超乎一切其他價格之上,所以如果說把人格作為目的本身,實際上沒有說出任何新的東西,只是同義反復。康德認為,“人是目的”的律令一定要把作為人格在經驗現象界的顯象作為目的,即“人格中的人性”,這才是質料性的。“人格中的人性”就是指我們每個人身上的人性,而不是指任何其他有理性者身上的人性。但為什么“人格中的人性”應該成為目的呢?從具體的質料性目的來說,人格中的人性就是指我們的自然稟賦得到理性的指導而發展出來,并在行動中表現出來,它們在日常行為中都應該受到出自道德法則的行為的尊崇,即作為目的,而不能僅僅把它們作為手段。奧諾拉·奧尼爾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他說:“把他人當作人來對待,這其中積極的方面要求行為遵循共享他人目的的原則”,也就是僅僅做到不侵犯他人,不把他人純粹用作手段還夠,還有必要采取“‘努力促進他人的目的’的準則”[6](P146)。人性作為設定目的的能力,把他人作為人來看待,積極的方面就是要把他人的目的納入到自己的目的之中,從而為他人發展自己的人性創造條件或提供幫助。這一點只有在這樣的理論視野中才能得到彰顯:那就是人性的表現一定是體現自由的,而不是體現一種機械性的特點;同時,人性的發展一定指向人類的文明化,并成為人類道德化的一個必要條件,或必經階段。所以,在現實生活行為中,人身中的人性是必須被尊重的對象。當然,在現實世界中,人們的人格中的人性也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作為手段,但是前提是不能辱沒人性的尊嚴。比如,在生產勞動中,我們的勞動能力作為一種人性能力,肯定要被作為一種手段,才能生產出社會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在生產過程中,人的勞動能力不能被當作奴隸的能力來使用(這就是僅僅被當作手段),而是應該以能夠促進我們的人性能力發展的方式被使用,其前提就是必須尊崇人的基本自由和平等權利,尊重人的人格。
第三條律令為什么是必要的?康德說,這體現了形式和質料的統一。這條律令是作為意志與普遍的實踐理性相一致的最高條件,即“每一個理性存在者都是一個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4](P439)。這一律令有兩層意思,即,(1)服從道德法則者是立法者,這是形式性的,但又比第一條律令更進了一步,因為它特別提出有理性者同時就是具體的立法者,在這方面我們不聽命于他人,也不聽命于神圣存在者,當然,作為受動者,我們也應該遵循我們自己所立之法。這是意志自律的徹底形式;(2)一個能成為立法者的人,必定會尊重人格中的人性,把它作為目的,如果大家都能這樣做,那么就組成了一個目的王國,即人們都尊重對方包括自己的人格中的人性,而不僅僅把它當作手段,這樣每一個人作為受動者,就能夠發揮自己的行動能力了。這顯然要“抽掉理性存在者的個人差異,此外抽掉它們的私人目的的一切內容”[4](P441)才是可能的。所以,目的王國是一種思想實驗,“在此實驗中我們把自己視為行動者(即假設的普遍立法者)和受動者(即這些法則的假設的承受者,如果某條法則使他人淪為單純的工具或未能把他當作自在目的來對待,那么這些承受者的行動能力就會被這條法則所破壞)。”[6](P181)也就是說,普遍法則公式與自在目的公式要能夠得到實現,必須讓所有人作為受動者都能夠執行。所以,目的王國是一種理念,在現實生活中,僅僅把他人的人性(甚至自己的人性)作為手段的情況所在多有,所以,這種理念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方向,并對把人格中的人性僅僅當作手段的行為提出了道德上的終極約束。比如,目的王國的理念排斥了戰爭,因為戰爭中的各方的目的是正相反對的。正如Allen Wood所說,“在實際的戰爭中,各方的目的通常都會落在可以想見的目的王國之外”[7](P170)。所以,康德把國與國之間的永久和平看作是一種理想。Allen Wood也認為,現實生活中社會競爭性的運作方式,也有許多是違背目的王國的理念的:“目的王國將威脅到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文明舉止,它們把所有人的競爭者視作為必然的理性的異議的對象。”[7](P170)這樣說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康德的意思是,在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運作中,雖然也會有把人們人格中的人性視作手段,但是我們要讓這種方式在尊重人們人格中的人性的前提下來進行,比如不能把人視作完全工具性的奴隸,要保障人們的法權等等,這就是為什么康德把人是目的公式也提到了“絕不僅僅當作手段”,也就是說,人格中的人性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會成為手段的,但是必須在把它的整體發展作為目的這一前提下來進行。
所以,康德的三大道德律令是等值的,只是在不同的方面來進行展示。這一義理的展開,就是說明我們在道德行為中,要把自己也把他人當作一個有理性者來對待。這使得康德的道德學說獲得了一個穩固的形而上學基礎。
同時,我們看到,先天的純粹理性的法則,也是人類政治活動的指導原則。先天的純粹理性的法則是前提,它在人們的政治活動中就是普遍的法律,在其約束下,人們的外在行為自由能夠并存的條件就是法權;政治還有一個任務,就是要以符合理性理念的國家制度,即有自由,又有法律的強制的公民法治狀態來促進人們的自然稟賦得到安全的發展,要求人們在生活中能夠獲得人是大自然的目的的觀念,平等尊重對方的人格和人性發展,并能夠把所有人都視作目的而不僅僅當作手段的思維方式,這就是《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一部分“法權的形而上學的初始根據”所關注的焦點;先天的純粹理性的法則,也是我們塑造道德美德的前提,那就是我們首先要能夠把尊重人們的平等法權作為自己的主觀準則,并能夠培養直接用普遍的道德法則來作為決定自己意志的根據,而抗拒把來自感性偏好的原則作為決定自己意志的根據的意志的力量,這就是美德;能夠履行德性義務,即促進自己的完善(包括自然完善和道德完善),并促進他人的幸福,這些都是在理性法則的指導下而形成的理性目的,它們是德性義務的質料內容。這就是《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二部分“德性的形而上學的初始根據”所關注的關鍵之點。
道德形而上學的建立,就是為了拯救本體自由,為了在道德原則問題上走出那種只憑權宜之計行為的狀態,同時為人類政治奠定了一種真純普遍的原則,為人類的自然稟賦的發展提供了理性原則的指導,并為人類歷史發展指出了一個總體道德化的最高目標。
三、純粹道德原則對人類道德經驗的指導
純粹道德原則的確定,其目的是對日常道德行為進行指導。在這方面,康德關注的是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通過反省,從人們的道德經驗中可以朗現出道德法則的純粹性和崇高性,也就是說,普通的實踐理性其實也能認識到道德法則,因為我們能夠體驗到我們的行為有可能出于不同的動機,比如是出于自愛還是出于義務,而且我們會對出于自愛的行為并不抱有高的評價,而對出于義務的行為即使對自己產生不利后果,也會感到驕傲。這種反省在普通人類理性中就能做到:“普通人類理性盡管當然不如此在一個普遍的形式中抽象地思維這一原則,但畢竟在任何時候都現實地記得它,并把它用做自己的判斷的圭臬。”[4](P411)康德在分析我們的知識時,發現知識必須由后天的感性雜多與先天的知性形式來構成;同樣,他也認為,如果我們的行為要具有道德價值,從對道德經驗的分析中,必定能發現,在來自感性偏好的動機之上另有來自先天的理性法則的約束。
第二,康德說:“與道德形而上學相對的部分,作為一般實踐哲學的劃分的另一個分支,將會是道德的人類學,但是,道德人類學將會只包含人的本性中貫徹道德形而上學法則的主觀條件,既包含阻礙性的也包含促進性的條件,即道德原理的產生、傳播、增強(在教育中,在學校教導和民眾教導中)以及其他這類基于經驗的學說和規定,而且道德人類學可能是不可缺少的,但絕對不必被置于道德形而上學之前或者與之混淆。”[2](P224)也就是說,道德人類學是道德哲學的經驗部分,它顯然要受到道德形而上學的指導。道德人類學就是考察人的本性中的素質如何得到經驗性的提升。這就是在為人們獲得一種純粹理性的道德思維方式而努力,并在某種決定性的時刻,實現向純粹理性的思維方式的躍升。同時,在歷史哲學領域,康德也是在考察人類在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借助“非社會的社會性”,而促進人的自然稟賦的發展,并在社會交往中造成人的文明化,實現某種道德的進步,另一方面也告訴大家,在人類歷史經驗性進化中,我們其實已經發展出了某些有利于道德化的理性素質,比如認識到人類是大自然的目的,人只能支配動物,把它們純粹當做手段和工具,但對任何人卻必須“視為大自然的賞賜的平等分享者”,并認為,“對于建立社會來說,這種準備遠比好感和愛更為必要”[8](P117)。還有,在社會交往中培養的優雅舉止、親切風度、良好鑒賞等能力,都是文明化的,它們可以看作是“外在的道德”,“包含著一種有從外部促進道德的趨勢”[3](P238)。
第三,我們人的自然稟賦是一個整體,有多種因素,它們都應該道德合乎理性目的的發展。康德早在1778年4月初致馬斯庫赫茨的信中就說過:“我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善良的、建立在基本原則上的意向,把這種意向鞏固在善良的心靈中,并由此為發展稟賦指出唯一合目的的方向。”[5](P59)在人們的經驗生活中,我們不要把這些因素對立起來,它們應該能夠整合統一起來,但必須有一種發展目標的引導。(1)在作為決定意志的根據這一點上,理性與感性偏好是直接對立的,因為這事關我們能夠獲得一種具有絕對的道德價值的原則,所以,在我們的主觀準則中不能雜有任何一絲感性偏好的成分,在什么樣的程度雜有感性偏好的成分,就在什么程度中損害了道德原則的真純性、道德價值的崇高性。(2)在人的生活中,人的自然稟賦都要起到作用,只是需要說明,我們的自然稟賦的發展要受到理性的思維方式的引導,而且要在生活行為中特別是追求幸福的過程中,人性的各成分的發展要與理性的道德原則相互協調,所以,并不是像有人所認為的那樣,康德主張理性與人的其他自然稟賦是對立的。(3)康德指出:“在交往中把舒適生活與德性結合起來的思維方式就是人道。”康德并不是告誡人們不要追求舒適和幸福,而是主張人們要懂得“應該如何用德性的法則去限制過舒適生活的偏好”[3](P272)。他認為,文明化的有趣的交談、交往都是經驗生活中的有意義的東西,可以被認真地推薦給德性。康德并不主張那種沒有任何生活享受的苦修主義,他說,“沒有社交舒適的犬儒派的純粹主義和隱修士的殘害肉體,都是德性的扭曲形象,對于德性來說是沒有誘惑力的”[3](P277)。(4)自由在任性自由中得到落實。他在最后的著作《道德形而上學》中,認為意志無所謂自由和不自由,只有任性才有自由,這樣才能把自由落實在經驗性的道德人類學、歷史哲學之中,即不斷地把人的自然稟賦提升到與理性相適應的狀態,這是自由的發展的經驗過程。其引導性的理念都是理性的自由運用,即我們的感覺、知性、想象力、判斷力、欲求能力等都朝著普遍性(一般性)的方向發展,并與先天的純粹理性的法則即普遍的道德法則相互適應,與理性的自主運用相互適應,并期望在某個特定時刻而躍升到一種純粹的道德思維方式之中。他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目標,就是人類作為一個總體而整體地邁向道德化。
四、康德實踐哲學義理系統中的邏輯跳躍
康德窮其畢生精力來構造其實踐哲學的義理系統,其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他劃分了本體與現象,從而使絕對的、先天的、普遍的道德原則能夠得以確立,使我們獲得一種對道德的絕對的、至高善的價值的理解,獲得對理性人格的尊崇,確證人作為一個有理性者的尊嚴,并拯救了道德領域中的本體自由,并能夠說明人的自然稟賦如何在理性理念的引導下逐漸得到提升和發展。然而,既然把本體與現象絕然二分,則這兩者如何溝通就成為了康德實踐哲學的重要問題。
康德在實踐哲學中溝通本體與現象時,必然會產生以下邏輯跳躍。
第一,在處理我們的道德律令如何能夠在經驗世界中實現時,他只能提出一個概念即“應該”。對于應該,如果我們人們根本就達不到,那么,這種理念最多就只能是引導性的。因為設定道德法則的純粹先天的、普遍的性質,而在現實生活中的人的經驗行為又必然是個別性的、具體的、相對的,而且其動機也必然會受到個人的感性偏好的刺激和影響,從而在現實生活中也許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完全道德的人。這一點,他自己也是承認的。但是,他對道德法則直接決定我們的意志的絕對道德價值深信不疑。他認為,即使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道德的人,也不能否認普遍的理性的道德原則的崇高性。它只能作為一個范導性的理念而起作用。然而,既然人性的發展、優雅的生活是我們生活的必需,那么,我們也很難設想如果我們采取完全的理性的道德思維方式后我們會怎樣生活。如果說純粹的道德就是排除了任何感性偏好的因素而只以道德法則來決定我們的意志,那么這樣的意志在現實中能夠存在嗎?他只能說,道德律令只是一種對我們這類其意志并不純粹是善良的理性存在者來說的“應該”,是一種道德強制性,是始終懸在我們面前的一條命令。
康德把本體與現象絕然二分,所以,在道德哲學中,道德的“應該”與行為的“實然”之間始終存在一種無法消除的張力。他提出的溝通之法,就是我們通過促進自然稟賦的發展而使之一般化,并期望它們在某個決定性的時候達到完全的普遍性,從而形成一種純粹理性的道德思維方式,這樣“應然”才能變成“實然”。但這純然是概念上的假設和期望,并不能找到一條現實的道路。馬克思主義認為,關鍵在于要揭示推動社會發展的真正的、可實證的動力,而不是憑借假設。馬克思主義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這兩個“對子”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所以共產主義是一種科學的信仰,而不是一種純粹的理性理念,科學地揭示了現實的物質生產力的變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內在的、客觀的推動力量。所謂應然,實際上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揭示,是必定可以實現的,現在的實踐是邁向這一理想狀態的階梯,為它的實現積累條件。所以,所謂本體的彼岸與經驗的此岸之間的關系問題,歸根到底是個現實的實踐問題。
第二,康德在處理自由法則與自然法則之間的關系時,同樣存在著邏輯上的跳躍。我們認為,康德在這個問題上也費盡了心血。由于道德法則是處于本體界的,沒有摻雜任何經驗現象的因素,但是,道德法則又是要體現行為之中的,而現實行為必然要落在現象界。如果按照康德的理論立場,他只需要說真正的道德行為就是用道德法則作為直接決定意志的根據而作出的行為,至于這種行為是什么樣的,結果如何,已經屬于經驗的范圍了,不能作道德價值的考察,因為“人們是因為意愿而善”,而不是因為結果而善。但是,完全遵循道德法則的意志一定會產生行為,所以需要說明這樣的行為在現象界的狀況。對康德而言,在這方面,只有自然法則可以拿來同道德法則相類比。所以,自然法則的律令可以表述為:“要這樣行動,就好像你的行為的準則應當通過你的意志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似的。”[4](P429)即是說,我們要抱有這樣一種意愿,即要讓他的行為所遵循的準則在經驗世界中似乎是遵循著自然規律似的。它必須借用道德哲學之外的原理,即目的論原則。就是說,自然的目的對人而言,就是要使有道德價值的行為能夠在自然界按照自然規律而持存,或者發展到它所可能達到的完善程度。比如說,自殺之所以不具有道德價值,是因為自然生人,就是要其按照自然賦予其生命長度的可能性而生存著,而不是自我毀滅;不促進自己的稟賦才能的發展之所以不具有道德價值,是因為自然賦予我們以稟賦,就是要我們憑自己的努力促進其發展,而不能因為喜好閑散而讓自然才能在那里白白生銹等等。但這些都是以揣測大自然的意旨而進行的,故而其表述式是“好像……似的”。顯然,要貫通本體與現象,對康德而言,必須進行邏輯上的跳躍,而不太容易做到邏輯上的嚴整一致。但是,在康德整個實踐哲學的義理結構中,這又是必然的選擇。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也必須回到人類物質生產實踐對人類的自然稟賦發展的作用以及道德進步的作用,人類的物質生產實踐就是對自然界和對人的內在自然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發展的過程。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想象中的東西通過生產實踐制造出來,則康德所謂自在之物就得到了真正的認識。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理想狀態,就是通過生產實踐而實現了從必然到自由、從經驗的此案到理想的彼岸的過渡,自然的人化與人化的自然得到了高度統一。所以,馬克思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與本質、對象化與自我確認,自由和必然、個人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9](P120)馬克思這段話,就是在回應康德的難題。
第三,康德把大自然的最高目的設定為人類作為一個總體而整體地道德化。但它不是建立在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揭示上,而是建立在目的論上。在康德看來,一方面,我們被賦予自然稟賦,有自然本能,有各種人性能力,有道德本性。康德認為,我們被賦予自然本能,其目的可以被合理地理解成是為了追求幸福。而被賦予理性,其目的只能被理解成是為了追求道德,大自然的最高目的我們只能設想為:人類作為一個總體而在人類的無盡長河中達到整體的道德化;另一方面,他認為,在歷史的舞臺上,我們看到的都是為了物質利益的爭奪、沖突、無用的虛榮,甚至殘酷的戰爭。面對這些歷史景象,我們會充滿一種憂傷:如果人類歷史只是這樣,那么,我們就會懷疑我們人類為什么要存在?所以,我們必須為人類的歷史活動賦予意義。這就需要訴諸我們的理性理念,這是我們作為一個理性存在者所能設定的、超越感性經驗的理性的最高目的,我們就為了實現這一最高目的而存在于世界上的,這就是我們的生存意義之所在。
康德認為,人類是大自然的創造物,所以,大自然在地位上比我們更高。他認為,人們能認識到我們大家都是大自然的目的,是平等的,人們都應該把對方視為目的,而不能僅僅把對方視為達到自己的利益的工具,這一點是人類道德進步的顯著標志。但同時,追問大自然的目的也只有人能做到,這是我們理性的功能。他在追問大自然的最高目的時,遵循以下理路:
(1)我們和地球上其他東西一樣,都是大自然的造物,但自然不做無用功,他把我們人類造成既有本能又有理性,一定有其目的,即本能追求幸福,理性追求道德。
(2)但人們因為既有本能又有理性,他們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多樣,沒有邊界,并且能夠想到的獲得利益的辦法會越來越多,但是地球又是圓的,不能沿地面無限地散開,所以,人們必須“在一起”,從而會因占有而互相沖突,甚至會有激烈的戰爭,我們總是不和。這就是我們在歷史的經驗舞臺上看到的景象。
(3)我們生活的意義必須被表象為:我們有“非社會的社會性”,一方面我們只有在社會中才能更好地發展人性,另一方面我們又經常沖突,這一點看上去是壞事,但卻是我們發展自己的才能,使之不致昏睡的必經途徑。這就是說,我們的生活意義就表現在我們能夠生活于一個普遍的法治狀態下,既有自由,又有普遍的法律和政治權力的正規強制,這樣我們的自然稟賦才能得到安全的發展,我們在這樣的政治狀態中生活,才能進行有效的社會交往、啟蒙,獲得共享的價值觀和判斷、共通感等一般性的觀念,走出純粹的個人主義狀態,而獲得一種擴展了自我,這就是良好的政治所能為我們獲得的生活意義之所在。
(4)所有這些人的生活意義的獲得,都是人們的認識、審美和欲求能力從個人主義狀態向普遍性的狀態提升的過程,也是人類作為一個總體而整體地道德化的一個必經階段。
(5)這一切都只能被理解為是在大自然的操縱下的一個過程,因為這個進程不是人類能夠自覺地計劃的。這就是康德關于歷史發展如何邁向其最終目標的觀點。這種觀點非常鮮明地表明,康德只是從理論上解釋世界,而對如何改變世界則不能提出任何切實的見解。他關于人類歷史發展最終會實現人類總體的道德化的看法,是一種典型的理論想象,從其思路來說,就是一種邏輯的跳躍。
所有這些邏輯跳躍,從理論上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康德對本體與現象的劃分,從他對這二者的界定來看,二者之間是有著不可通約的本質差別的,但是在具體的道德行為中,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他又致力于把這二者連通起來,由于他缺少能夠真正溝通本體和現象的物質實踐的觀點,所以就只能通過邏輯的跳躍來達到。
[注 釋]
①李秋零先生把這個公式的“人身中的人性”譯為“人格中的人性”,似不妥。人格是本體界的,人性并不能處于本體界中,而只能存在于經驗性的人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