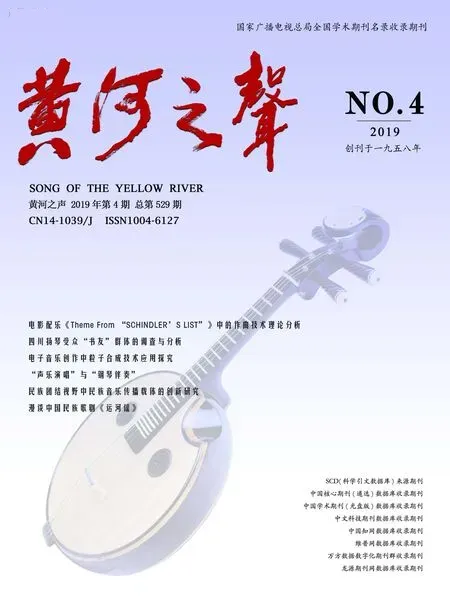漫談中國民族歌劇《運河謠》
吳 曉
(天津師范大學音樂與影視學院,天津 300387)
歌劇(opera)是一門起源于西方的綜合舞臺藝術形式,相較于戲劇而言表達故事的方式多依托于歌唱和音樂,其演唱方式為美聲,最早出現(xiàn)在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民族歌劇是以本國的語言演唱、采用民族素材,為本國人民寫作的歌劇。而中國民族歌劇則是依托于中國語言底蘊、文化背景、音樂素材下創(chuàng)作的,采用民族唱法的歌劇形式。
一、《運河謠》之時代召喚出新穎
(一)《運河謠》的創(chuàng)作背景
《運河謠》是2012年由國家大劇院推出的首部原創(chuàng)民族歌劇,該劇在當時就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部作品的作曲家印青老師本著“藝術只是承認一流,時間才能打造精品”的原則,從構思到創(chuàng)作。《運河謠》這部歌劇的作曲花費了他整整兩年的時間,從廣闊的中華民族文化中吸取精華,力求展現(xiàn)出中國民族歌劇的魅力,同樣也是飽含廣大藝術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晶。
“這部歌劇作品是印青創(chuàng)作生涯的又一里程碑之作。時代呼喚的是真誠與平等,所以不能矯揉造作地表現(xiàn)假崇高,而應運用傾訴的語言,表達‘平民化’的情感。”當然在保持中國民族歌劇原有特色的基礎上,整部作品給人呈現(xiàn)出一種嶄新的面貌,而其新穎主要體現(xiàn)在幾個方面。
(二)《運河謠》的獨到新穎
其一是在劇本的采用上,沒有依托舊體裁現(xiàn)有的傳奇故事、民族戰(zhàn)爭、歷史人物、民間故事等進行改編,而是完全構造一個新的故事。其二在人物設置上,沒有采用英雄性的人物,而是以小人物以小見大進行展開,并且在小人物的選擇上沒有采用本身就給人浩然正氣既定印象的角色概念,而采用了唱曲女藝人的底層甚至于當時社會有些貶義傾向的角色設定。其三在其音樂唱法上,采用純民族唱法,音樂基本要素中沒有刻意的強求民族特色,而是整體流露出一種自然的狀態(tài),不生硬,整體音樂多樣統(tǒng)一,不硬搬硬套西方歌劇宣敘調寫法,并抓住漢語特色的音調進而融入譜曲之中,這也是整體民族性體現(xiàn)的同時沒有過往民族歌劇的生硬的原因之一。其四在舞臺舞美設計上,實景搭建,一比一比例的船,細節(jié)之處考究到位,并且隨著劇情的發(fā)展不斷變幻,兼具意境色彩,給人以視覺震撼與美并存的雙重享受。其五在音樂內容上,民族化的風格特征不僅僅通過主題旋律來展現(xiàn),在整部劇中貫穿了多個民間音樂元素和民族樂器,并且由于是在運河上的故事,在民間音樂素材的選擇上由于故事地域的流動性,素材也融合了南北不同的元素,使音樂內容更為豐富也更貼合實際。這些不同的新編創(chuàng)的融入,造就了這部優(yōu)美的歌劇《運河謠》。
二、《運河謠》之珠聯(lián)璧合美如畫
(一)《運河謠》的故事背景
《運河謠》這部作品以明朝萬歷年為時代背景,大運河為主要故事地點,講的是男主人公秦嘯生因上書揭發(fā)知府貪污漕糧遭遇追捕,與反抗作妾的女主人公水紅蓮同逃亡與運河河畔巧遇,進而發(fā)生的一系列故事。
(二)《運河謠》的和諧之美
《運河謠》之美首當其沖的是音樂美。序曲以輕柔舒緩的音樂起,首先在音樂內容上就給作品奠定了一種悠揚優(yōu)美的基本情緒,并且由大提奏出的主題引出,音色不尖銳給人以舒適之感,其后再依次承接小提琴,單簧管,在樂隊的配合下,圓號進入全曲基調提升變得緊張,在不斷進行中整體音符也變得緊湊密集,情緒越發(fā)激昂向上,持續(xù)進行在全曲達到高潮的情緒下戛然而止,重新回到序曲開始時的優(yōu)美基調由管樂組奏出,四個小節(jié)后樂隊齊上陣仍傳遞出優(yōu)美抒情的情緒。這種樂隊的表現(xiàn)形式在后面整個劇目的演出中也多有采用。其后在氣氛較為濃烈的情緒下漸漸下降,漸弱引出作品的主題曲《我們的運河的流水》,這也是《運河謠》中流傳最為廣泛的曲目之一,音樂旋律優(yōu)美,音色上較為暗淡表現(xiàn)出一種平靜松弛的狀態(tài)。
開場戲是以龍王歌舞會為場景,《彩龍船》一曲一出旋律加上民間打擊樂與樂隊,熱鬧非凡。女主演唱的主題曲《運河謠》旋律抒情之外,詞的優(yōu)美婉轉也是畫龍點睛之筆。在后面幾幕中多用重唱的形式,多段采用了一曲多詞的形式,且在詞的構造上多優(yōu)美詩意,運用上多為反復強調,氣勢上更為壯闊。在作品最后一幕關硯硯與秦嘯生在北京的臺階上與眾人采用京味兒的叫賣腔調,賦予濃厚的文化特色且在用詞上也十分通俗,給人以大眾化的審美感,貼近生活還有點曲苑雜壇的味道,很有意思。
在樂隊的伴奏上作曲家也做了一些小心思,在宣敘調時多次使用模進,強化旋律,在詠嘆調時多用色彩性的伴奏,增強情緒。穿插在曲子中的各種民族樂器使作品更增添了一股民族的味道,達到旋律與伴奏的雙重契合,聽覺與表演呈現(xiàn)的雙重契合。其次是整部作品的舞臺設置美,從一彎河水一艘木船一襲襲擬人化的白衣運河水到龍王舞會的服飾美再到拉纖時夕陽西下的背景美,視覺審美給人以舒適感。使整體作品的民族性風格體系凸顯,形式美與內容性和諧統(tǒng)一。
三、《運河謠》之畫龍點睛巧心工
(一)民族化語言與表達
《運河謠》從作品序曲開始就民族性濃郁,無論是不是音樂工作者,只要聽到這樣的曲調立馬就帶入中國特色民族氛圍之中。其巧妙還體現(xiàn)在作品的繪畫性內容上,首先在舞美的設置上,這也是全劇中非常值得一提的地方,一排穿著素衣的女子隨著歌聲飄出,導演在此處采用擬人化的手段用一排素衣女子來象征著大運河,大運河也正是整個故事發(fā)生進行的地點,它伴隨并承載著整部歌劇的進行,這就為《我們是運河的流水》這一曲目為何頻繁出現(xiàn)的原因提供了現(xiàn)實依托。并且這一曲目雖然多次出現(xiàn)但是在詞上有多次變動,還承擔了陳述劇情的任務,既有承接又有對比。
(二)貼切的角色設定
在角色設定上,每個人的性格設定都很貼切,女主身份雖為藝人,但是整體人生觀是剛正不阿的,具有故事女主英雄性特征。秦嘯生書生形象決定了其對有情有義的水紅蓮滋生愛意,也使對關硯硯產生同情之心,做下保護關硯硯的決定并盡職盡責顯得自然不生硬。關硯硯角色也是導演比較巧妙的設計,一個盲女的引入讓劇情發(fā)展更為合理,人物形象也更為悲慘,戲劇中的轉折處就此發(fā)生,同時也讓主角的英雄氣質更為凸顯。第一幕中李小管角色短暫出現(xiàn)展示出風流放蕩的性格為后文埋下伏筆。第二幕中水紅蓮與秦嘯生關于水手如何說話劇情表述的對話也比較巧妙,相對粗俗化詞語的運用恐怕更是編劇的小心思,讓整部劇更貼近實際也讓大眾感到更有戲。因此《運河謠》的整部作品從音樂、舞美、角色、戲劇內容等眾多細節(jié)上都呈現(xiàn)出作者考究巧妙的心思。
四、《運河謠》之細節(jié)深慮顯不同
(一)《運河謠》的題材選定
《運河謠》的民族性體現(xiàn)在旋律、伴奏樂器、場景設置,給人以聽覺視覺同步觀感,相較以往有些歌劇只強調民族性卻缺乏真正民族性特色內容體現(xiàn)的劇目,在體現(xiàn)上更為細節(jié)。由于中外交流的不斷深入,由以往多借鑒戲曲手法的創(chuàng)作表演模式逐漸加入了西方歌劇形式。由此也在題材、演唱技術、選段編排及各種藝術形式上有所變化。
“近幾年,中國歌劇的創(chuàng)作中,劇本創(chuàng)作立足于民族傳統(tǒng)審美心理,注重加強了文學性和戲劇性,強調了情節(jié)的推進和復雜性,音樂創(chuàng)作也更加符合劇情,貼近生活。其中比較優(yōu)秀的劇目包括《傷逝》、《原野》、《蒼原》等。這些歌劇作品雖然題材不同,但都有著強烈的戲劇沖突和鮮明的人物性格以及經典的唱段。這也與作者及表演者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
(二)同類型民族歌劇之比較
在同類音樂內容性都比較成熟的歌劇作品中,《運河謠》與他們有什么區(qū)別呢。拿幾部較廣為人知的作品來說,跟《白毛女》《江姐》相比,整體社會意義不如《白毛女》《江姐》深遠,可能與時代不同感知不一樣有關,《白毛女》《江姐》雖然比《運河謠》誕生早,但其故事背景選用的比《運河謠》更為貼近現(xiàn)代人,故事題材也更加深刻,因此更能激發(fā)群眾的熱血。《運河謠》則對于愛情的描述更多,雖有一定社會意義的闡述但是以明朝萬歷年間的故事背景,很多人可能無法更多感同身受,只當個故事來看待,因此不如《白毛女》《江姐》來的深刻,但這卻并不妨礙《運河謠》是新時期歌劇中的上乘之作。與《木蘭詩篇》相比,愛情的表達更為顯露直觀,且更貼近生活化的表現(xiàn),相比下更接地氣,也更易帶動觀眾的情緒走,觀眾看的懂看的熱鬧就容易拉動市場需求,從而產生一系列IP效應。與《趙氏孤兒》相比,由于《運河謠》完全是原創(chuàng)劇本,沒有《趙氏孤兒》的原有群眾基礎,是一張白紙上作畫,一方面群眾基礎需要重新聚攏,也自然產生另一方面大眾對于《運河謠》的期待就沒有自主意識,在呈現(xiàn)難度上《運河謠》便少了忠于原著的壓力,《趙氏孤兒》整體作品的再度創(chuàng)作就有著多種局限,因此在劇本創(chuàng)作上《運河謠》也有著不必過多思想負擔,在作品呈現(xiàn)上好像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驚喜。
五、深化民族自信再輝煌
縱觀中國民族歌劇的發(fā)展,現(xiàn)階段我們還處于探索前進的階段,我們渴求更為民族化的作品時也同時會造成不同層面的欠缺。但現(xiàn)在隨著廣大人民群眾審美觀念的提升,民族歌劇的受眾面更加廣闊了。尤其在文化自信提出后,依托我國傳統(tǒng)民族文化而發(fā)展的各種藝術形式進一步提到臺面上,當然造就了百花齊放局面的同時也造就了質量的參差不齊。《運河謠》作為百花齊放下的果實可謂是豐盛且?guī)в袪I養(yǎng)的。在最基礎的大眾欣賞上當時是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的,無論大眾采用了何種的欣賞方式,大眾擁有的多樣化的群體特征,由于劇目本身的特性,如作品音樂內容的民族化、戲劇內容的通俗易懂化、表演方式的合理性和連接上的得當都讓作品投身于市場時得到了大部分觀眾的認可。
那么一部優(yōu)秀歌劇的產生除了帶來審美體驗的直觀感受外,還應多方面考慮,發(fā)揮一部作品最大程度上的影響力。如在民族精神的傳播上,打造中國民族歌劇的道路是漫長的,每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都是成功路上的墊腳石,民族精神就是在一部部優(yōu)秀作品的傳播上慢慢建立的。而優(yōu)秀的標準又是如何定義的呢?西方歌劇現(xiàn)在擁有著成熟的模式和界定,我們也應樹立我們的東方審美,產生一種普世價值,最基本的內容民族性一定不能偏離。此外在作品內容完備之下也應順應時代發(fā)展,利用時代技術,才能更好的發(fā)揚發(fā)展讓它在群眾中生根。把握作品、掌握宣傳、擺正態(tài)度、不驕不躁、不氣不餒,那么中國民族歌劇發(fā)展定會開出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