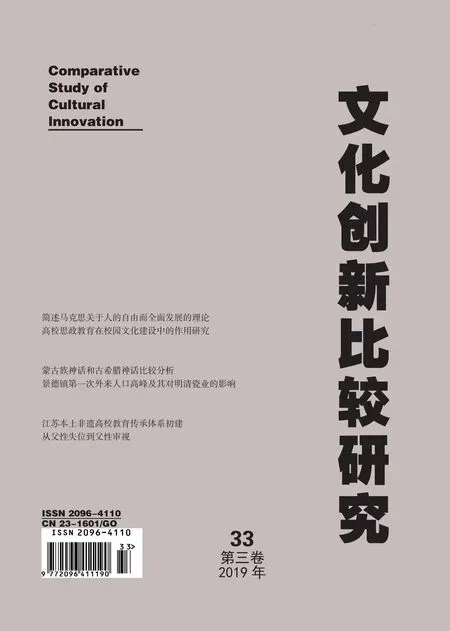自由的誕生及其可能
——基于弗洛姆《逃避自由》的思考
李 越
(中央民族大學(xué),北京 100089)
1 弗洛姆的自由觀
自曼德維爾、霍布斯之流開創(chuàng)“人是理性的”、“人天生具有狼的屬性”、“人性的惡造成了社會的善”之說以后,西方思想界便把其當(dāng)做無須驗(yàn)證和質(zhì)疑的真理性前提。雖然后來的盧梭是重視人類情感和感性的,但啟蒙運(yùn)動(dòng)已經(jīng)把主流引向了“理性”的殿堂。因此,大多數(shù)思想家只看見了自由“善”的一面,是基于這個(gè)隱形的前提:即人是理性人,人的理性把利益作為價(jià)值選擇的主要甚至是唯一依據(jù),以實(shí)現(xiàn)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不考慮人的情感與心理層面。人已經(jīng)成了現(xiàn)代社會的中心和一切活動(dòng)的目的,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出自于自私自利的動(dòng)機(jī),而不是感性的支配,似乎人類活動(dòng)的全部強(qiáng)大動(dòng)力就是自利與自我中心主義。而弗洛姆看到了另一面,并作出了很好的解釋:“近四百年來,人為自己做了許多,都在為自己的目的而努力。但是如果我們這里所說的他不是指工人、生產(chǎn)者,而是指有感情、智力及感性潛能的具體的人,那么許多看似是他的目的的東西,其實(shí)并不是他的。”人并非是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而奮斗,而是為了時(shí)代和社會賦予他的價(jià)值而奮斗,即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他敏銳地感知到了不被眾多思想家發(fā)掘的、大眾心理的另一面,尤其是中下階層人民的行為動(dòng)機(jī)和角色認(rèn)知,抓住了他們在個(gè)體面對強(qiáng)大的非人為力量時(shí),產(chǎn)生的相對剝奪感和不安、孤立感以及產(chǎn)生的結(jié)果。
作為心理學(xué)家,弗洛姆對自由的定義更多地關(guān)注到了自由狀態(tài)的心理層次解讀:“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義會隨人把自身作為一個(gè)獨(dú)立和分離的存在物加以認(rèn)識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變化。”可見,弗洛姆的邏輯起點(diǎn)是以人和社會的獨(dú)立與分離為前提,自由是人作為獨(dú)立個(gè)體存在的一種自我意識和狀態(tài)。自由的確能帶來市場經(jīng)濟(jì)機(jī)遇和個(gè)人財(cái)富積累,但當(dāng)自由的代價(jià)是獨(dú)立和孤獨(dú)時(shí),人們往往會選擇逃避自由,除掉自由的負(fù)擔(dān),轉(zhuǎn)移為個(gè)人行為承擔(dān)風(fēng)險(xiǎn)和責(zé)任的同時(shí),也“除掉了個(gè)人自我”。他們會臣服新式權(quán)威,或者強(qiáng)迫接受公認(rèn)的某種社會模式。
2 中世紀(jì):現(xiàn)代意義自由的誕生與夭折
卡倫·霍尼在《我們時(shí)代的神經(jīng)癥人格》一書中,假定了一種“基本焦慮”的存在,它是由于資本主義文化中的市場競爭、人與人之間的金錢利害關(guān)系而導(dǎo)致的。基本焦慮并不會導(dǎo)致神經(jīng)癥焦慮,但如果家庭和社會環(huán)境給人造成了不利的影響,那么基本焦慮就可能演變?yōu)樯窠?jīng)癥焦慮,成為精神疾患。弗洛姆的理論雖與卡倫·霍尼相似,卻不盡相同。由于接受了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哲學(xué)理論與成熟時(shí)期馬克思的社會學(xué)理論,弗洛姆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人本主義理論相結(jié)合,弗洛姆發(fā)現(xiàn)了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在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
他指出,不同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需要不同的人格結(jié)構(gòu)來作為生產(chǎn)力。一方面社會的強(qiáng)大力量塑造了人的行為模式,另一方面人的這種適應(yīng)又會使人產(chǎn)生新的行為動(dòng)機(jī),進(jìn)而對整個(gè)社會產(chǎn)生反作用。這較好地解釋了為什么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中世紀(jì)的人們生活在穩(wěn)定的政治經(jīng)濟(jì)體制內(nèi),社會流動(dòng)性差,社會等級就是一種自然等級,但同時(shí)也是給予人以安全感和歸屬感最為明確的部分。在這個(gè)時(shí)期,社會競爭相對較少,人的經(jīng)濟(jì)地位是生而決定的,雖然具有相當(dāng)?shù)奈鋽嘈裕彩歉麟A層人民的生活保障,生活受制于傳統(tǒng)。個(gè)人的自我意識、他人意識和世界意識尚未得到充分發(fā)展,也沒有意識到三者是獨(dú)立的實(shí)體。
弗洛姆更進(jìn)一步,將孤獨(dú)提升為了人類的哲學(xué)本體論問題,因?yàn)橹惺兰o(jì)的終結(jié)和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人的個(gè)體化水平進(jìn)一步提高,這直接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孤獨(dú)。始發(fā)紐帶被打破,而人類還沒有形成足以抵御孤獨(dú)的繼發(fā)紐帶。如果用卡倫·霍尼的術(shù)語習(xí)慣,即“基本孤獨(dú)”。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則進(jìn)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之間深深的孤獨(dú)感與無能為力感,因?yàn)閭€(gè)人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jīng)濟(jì)中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如果不適當(dāng)處理,就會導(dǎo)致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世紀(jì)轉(zhuǎn)型期的人們在打敗舊式權(quán)威的最后一只攔路虎——教會之后,轉(zhuǎn)而投向了另一種更具有壓迫性的秩序——內(nèi)在的束縛、強(qiáng)迫和恐懼。因恐懼和妥協(xié)產(chǎn)生的內(nèi)心秩序比基于強(qiáng)制武力和知識壟斷為基礎(chǔ)的外界秩序更為長久,也更為虔誠。我們對擺脫外界控制和秩序而欣喜若狂,卻對內(nèi)在的束縛和秩序置若罔聞,它們會削弱自由戰(zhàn)勝傳統(tǒng)敵人并獲得勝利的意義。
3 “善”的秩序:自由最后的避難所
自由是一個(gè)相對概念,這意味著只有通過他人和社會的表達(dá)途徑才能實(shí)現(xiàn)其價(jià)值。盧梭主張個(gè)體和社會共同體是互益的“共生關(guān)系”,從“社會契約論”來看,個(gè)人要維護(hù)共同體甚至為之犧牲是為了保障個(gè)體自由的實(shí)現(xiàn),并非弗洛姆所提及的個(gè)人喪失自我融入群體,而是維護(hù)好的共同體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個(gè)體實(shí)現(xiàn)自由的途徑,個(gè)體和共同體是積極的、主動(dòng)的、互益的有機(jī)聯(lián)系,這也為康德等人無法解釋的“個(gè)人自愿為集體犧牲”提供了答案。個(gè)人因其力量的弱小而無力保障和實(shí)現(xiàn)自身的自由,因此需要團(tuán)結(jié)同階級的力量進(jìn)行抗?fàn)帲瑺幦?shí)現(xiàn)自身的自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剝削壓迫的奴隸制、等級森嚴(yán)的封建制等“惡”的秩序,亦或是法國大革命中雅格賓派的獨(dú)裁和“暴民政治”的狂熱等根本無秩序的狀態(tài),個(gè)人基本生命權(quán)都難以保障,自由更是無從談起。如果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集權(quán)主義將戕害個(gè)人自由,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善”的秩序是個(gè)人自由的最終歸屬和避難所。
而縱觀中國古今,中國的自由與秩序、自我意識和群體意識的區(qū)別也經(jīng)歷了古代孔孟儒學(xué)的“無我”,近代思想啟蒙的“唯我”,現(xiàn)代的價(jià)值“自我擴(kuò)展”階段。儒家學(xué)派不談自由和自我意識,將自我價(jià)值依托于群體價(jià)值,是為“無我”;近代思想啟蒙家如胡適和早期的陳獨(dú)秀,宣揚(yáng)個(gè)人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標(biāo)榜個(gè)人自由,即“唯我”;現(xiàn)代在中西方思想的共同沖擊下,產(chǎn)生了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充斥的思想混亂時(shí)期,宗教和封建同時(shí)被沖擊導(dǎo)致價(jià)值出現(xiàn)真空,個(gè)人生命的有限性消解了生命的價(jià)值和意義,自我價(jià)值無處依附,因此陳獨(dú)秀重社群的傾向一步步凸顯出來,并在此時(shí)提出“自我擴(kuò)展”,虛幻的個(gè)人于實(shí)在的整體構(gòu)成人生的矛盾,個(gè)人通過“自我擴(kuò)展”而認(rèn)同并融化于整體,達(dá)到人我合一,獲得實(shí)在性和永恒性。
可見,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考慮到了自我價(jià)值依附的問題,正如盧梭所說,人無法擺脫“自然和社會的雙重枷鎖”,所以人類必須選擇如何“戴著腳鐐跳舞”。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自我價(jià)值的歸路總結(jié)為三條,一是超自然的宗教依附,宗教是由一些特定的行為、實(shí)踐、世界觀、文本、圣地、預(yù)言、倫理、組織組成的文化系統(tǒng),其特點(diǎn)是將人類與超自然的、先驗(yàn)的或精神的元素相聯(lián)系,如基督教和佛教。這一途徑發(fā)展到極端是神秘主義者或是宗教狂熱信徒;二是價(jià)值的自我擴(kuò)展,即建立人和群體或組織的聯(lián)系,通過群體實(shí)現(xiàn)自身價(jià)值的無限延伸,這一途徑的極端則是種族主義或者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三是價(jià)值的自我消解,即完全從世界上隱退,以便讓世界的威脅徹底消失。針對于本章討論的命題,筆者認(rèn)為,“善”的秩序真正要保障的、有價(jià)值的自由是,人能夠在社會中自主選擇自我價(jià)值的依附取向,即能自主地選擇何種途徑為自我價(jià)值的歸屬并有相應(yīng)行動(dòng)的能力。而借助弗洛姆的概念,即要保障人的全面完整人格的自發(fā)活動(dòng)。
4 總結(jié)
弗洛姆給出的答案是愛與勞動(dòng),這顯然是一個(gè)極具偶然性、對個(gè)人素質(zhì)要求極高,因此從個(gè)人層面難以落實(shí)的方案。自由的可能性最終要回歸到“善”的社會秩序,要從社會的層面加以解決。自由的意義與價(jià)值需要通過他人和社會的途徑才能加以表達(dá),并且自由的實(shí)現(xiàn)需要建立在較高的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上,否則純邏輯的自由概念是毫無意義的。筆者認(rèn)為,在社會層面里人的自由表現(xiàn)在能自主選擇價(jià)值取向和進(jìn)行自發(fā)活動(dòng),即“善”的社會秩序能保障共同體中個(gè)人選擇自我價(jià)值的歸屬并能作出相應(yīng)的行為:超自然的宗教、群體的“自我擴(kuò)展”亦或是自我消解。自由和秩序之間,應(yīng)當(dāng)是互益的共生關(guān)系。“善”的秩序應(yīng)做的,便是保障追求自由的意愿的積極生長,而不是使自由“異化”,成為一種需要逃避的負(fù)擔(d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