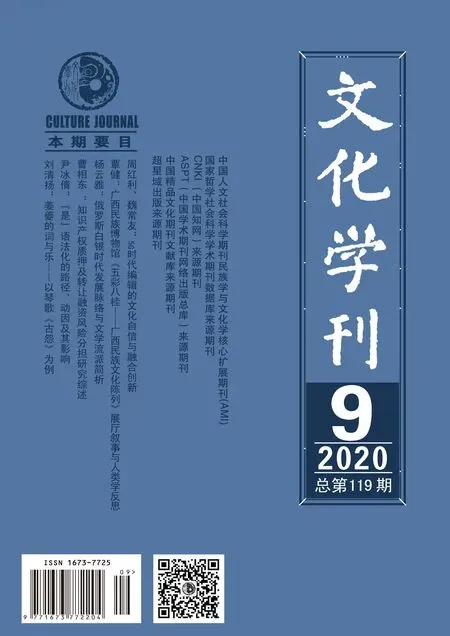中國傳統文化對來華傳教士的影響
——從《漢語札記》看馬若瑟的中國化
趙 蓉
一、馬若瑟其人與《漢語札記》
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生于法國,是一名耶穌會傳教士。在他之前,已有一批法國傳教士在清廷為康熙皇帝服務。康熙皇帝對西學興趣濃厚,遂又派遣傳教士白晉回國招募新人來華。1698年,白晉帶領新招募的十名傳教士來華,馬若瑟便是之一。來華以后,馬若瑟大部分時間居住在江西南昌、九江等地,1733年遷居澳門特別行政區,1736年左右在澳門去世。
在華近四十年的時間里,馬若瑟對漢語和中國文化顯示出了極度熱愛。他并不認為學習漢語是一件苦差事,而是非常美好的、能帶來心靈慰藉的事情。他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于漢語和中國文化研究,在天命之年寫出了這部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代表作《漢語札記》。
這本書的直譯書名是《關于中國語言的知識》。馬若瑟寫作的初衷是幫助漢語學習者更快掌握這門復雜的語言。以往的漢語學習讀物要么是解釋字詞含義的詞典,要么是以拉丁語法結構框架為主的語法書,明顯不適合獨立于印歐語系的這一東方語言。《漢語札記》獨辟蹊徑,不以拉丁語法結構套用分析漢語,而是關注漢語本質特征。其寫作指導思想是,中國文化、文學與語言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只有在對中國文化有了深入了解,對中國各類文學作品所構建的學術思想、精神內核有了深刻領悟之后,才能熟練掌握和運用漢語。因此,要漢語學習,先要熟讀中國典籍,了解中國文化。
《漢語札記》全書共分三個部分,基于上述指導思想,馬若瑟在緒論部分即將中國文學加以分類,并進行了全景式的介紹。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從白話(通俗漢語)和書面語(文言)兩方面,闡述了漢語的語法、句法、虛詞以及修辭和文體等,同時加入了中國禮儀的介紹,在最后部分將精心挑選的400多條短語進行了匯編。從內容上看,《漢語札記》遠遠超出了一本語法書的范疇,也不能定義為一本語言教材,而應說是一部關于中國語言文學知識的百科全書。
二、馬若瑟在《漢語札記》中對中國典籍如數家珍
與其他漢語教材不同,《漢語札記》的開篇并沒有直接介紹詞匯語法等內容,而是將40多種中文典籍根據時間、寫作風格等進行分類歸納,分為九大類,不僅包括四書五經,還有諸子百家、唐宋名家及史家作品,試圖給歐洲的讀者展現出一個中國文學的全貌。
由此可以看出,馬若瑟對中國古代典籍涉獵相當廣泛,實在是令人驚嘆。大部分中國傳統儒生學習上述典籍都是為了考取功名,而馬若瑟完全是憑著自己的興趣愛好來研讀這些經典文集。他曾在《春秋論》的自序中寫道:“是故瑟于《十三經》、《廿一史》、先儒傳集、百家雜書,無所不購,廢食忘寢,誦讀不輟,已十余年矣。”[1]馬若瑟并不是只關注學術論著,“百家雜書”都有所涉獵。他對元雜劇話本和明清通俗小說也非常熟悉。《漢語札記》第一編白話文部分的例句大都選自其中,如《元人百種》《玉嬌梨》《水滸傳》等。《漢語札記》從中國各類文獻中引用的例句有13 000余條[2],可以說《漢語札記》就是建立在對中國各類文獻的梳理總結之上。只有對各類文獻典籍了如指掌,加上用心用時的記錄分類,才能完成這樣一部全方位概括中國文學、分析中國語言文字規律的巨著。從這方面看,馬若瑟的學識可以比肩任何一個中國本土儒生。
三、馬若瑟在《漢語札記》中表現出對中國禮儀了如指掌
馬若瑟自33歲來華至70歲左右在澳門逝世,后半生全部是在中國度過的,其生活方式也有很多被同化之處,如穿華服坐轎子、使用毛筆書寫、把文房四寶作為禮物贈與友人等。在近四十年與中國人的日常交往中,他早已適應各種中華禮儀,在各種場合都游刃有余,經驗豐富。為了幫助新來的傳教士在交際中更準確地使用漢語,迅速了解中國文化,他在《漢語札記》中專門辟出一章,論述中國禮儀。
在這一章中,馬若瑟列舉了稱呼、拜賀、送禮、宴請等禮儀,每一種都有詳細的說明和例句。他發現中國人非常重視對他人使用敬語,對自己使用謙語,如用“貴邦”“尊府”“大老爺”等表示尊敬,而用“卑職”“賤恙”“愚見”等表示謙卑。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儒家的一整套禮儀制度為支撐的,儒家提倡“禮者,自卑而尊人”。馬若瑟僅僅介紹人際交往中的稱謂便能抓住儒家精神的內涵,可見他對儒家文化細密深刻的理解和領悟。其他如拜賀時如何拱手、作揖,送禮的種類、方法,宴請時的座次、飲酒的程序等,書中都有非常詳盡的說明。除非是親身經歷,否則很難將如此繁復瑣碎的禮儀介紹得如此清晰,由此可見,馬若瑟在人際交往方面已經非常中國化了。
四、馬若瑟在《漢語札記》中表現了對漢語的深刻理解和崇拜
如前所述,馬若瑟對中國語言有極大的興趣,自來華之初便全身心投入漢語學習之中,三四年后便可閱讀中國書籍,開始中文寫作。此后在華的三十多年時間里,中文既是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又是他進行閱讀和研究的對象,一個是客觀環境的要求,一個是他的志趣所在。在長期的浸染之下,漢語已經取代了馬若瑟的母語成為他的第一語言。后代學者在評論《漢語札記》時提到:“他已經成了一個中國學者。……你很難感覺是在閱讀一位歐洲人所寫的文章。”[3]
《漢語札記》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將漢語口語(白話)與書面語(文言)分成兩編加以論述,口語部分稱之為“現代漢語”,文言部分稱之為“古代文學中的語言”。馬若瑟在生活中發現,雖然中國人使用的漢字是一樣的,但是在口語和書面語中,它們的用法卻不大相同。他這樣編排是希望傳教士能從聽說和讀寫兩個層面盡快掌握漢語,這是極其具有開創性的一種編寫架構。以往的傳教士也許也發現了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的不同,卻沒有人對此加以論述,直到馬若瑟將白話從文言中分離出來進行分析。自白話文運動開始,近代漢語發展經歷了白話與文言不斷糾纏、白話文地位逐漸上升、文言逐漸衰退的過程。馬若瑟對漢語白話文的關注和研究,較白話文運動提早近200年,從這個意義上說,其可以算是開白話研究先河之人。而能開此先河之人,必然具有扎實的中文功底和對漢語的敏感性。由此可見,馬若瑟雖身為金發碧眼的西洋傳教士,但在語言方面的中國化程度已經很深了。
馬若瑟對中文的深刻領悟體現在各個方面。他認識到,漢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表音屬性,是音、義、形三者的統一。對于漢語語音,他不僅準確地介紹了平聲(包括陰平、陽平)、仄聲(包括上聲、去聲和入聲),而且對音韻格律進行了詳盡分析。他將中文詩歌和古代希臘語、拉丁語詩歌相比較,發現中國人更加強調韻律,而且經常會換韻,很少一韻到底。在第二編的第三章中,他摘錄了先秦諸子和唐宋名家的作品段落,展示了平仄的變化、韻腳的豐富統一、句式節奏的完美轉換,指出它們是優美文章不可或缺的形式。詩歌文章的韻律節奏能反映出一種語言的精髓,非母語者往往較難體會其精妙之處。馬若瑟卻不然。他不僅能將這些韻腳系統地歸納總結,還能領悟到文章的優美便來源于此,能夠像中國人一樣欣賞這些經典之美,實屬難得。
在考察中文詞匯方面,他將漢語詞匯與其他歐洲語言的說法相比較,而后得出“中國語言是一種豐富、優美并具有表現力的語言”的結論。講解“也”這個詞時,他是這樣說的:
“書也無心去讀”意思是“他不喜歡讀書”。我們也許會說“沒有心讀書”,請注意中國人在說這個句子時,措辭多么優美。他們把賓語“書”放在開頭,然后是虛詞“也”,使人注意后面的部分,而不是“書”這個詞。[4]
在進行語言比較研究時,研究者通常會帶有主觀色彩,認為母語優于其他語言。馬若瑟則為一特例,其在《漢語札記》中對于漢語的褒揚比比皆是,足見他對這種語言的由衷熱愛,甚至可以說,他認為至少在語言文字方面,中國文化優于歐洲。
五、結語
通過以上幾個角度的考察不難看出,馬若瑟對中國古代典籍了如指掌,對中國交際禮儀游刃有余,對中國語言文字理解精準,這些中國元素已經滲透到了他的生活、寫作和思想中。除馬若瑟,還有一批傳教士均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如艾儒略、白晉以及清后期的馬理遜、裨治文等。中國文化以獨特性、多元性和融合性影響了異質文化的外來者,這對于今天如何開展文化交流、將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出去,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