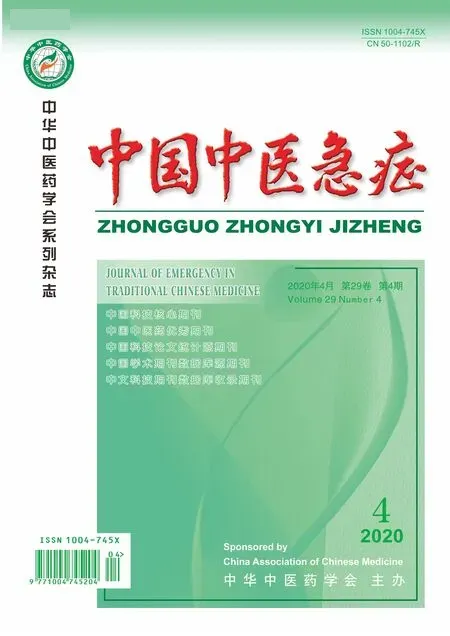從陽明經證探討白虎加人參湯治療甲狀腺毒癥?
譚張奎 向 楠
(湖北中醫藥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5)
甲狀腺毒癥是由于血循環中甲狀腺激素水平過高,引起以神經、循環、消化等系統興奮性增高和代謝亢進為主要表現的一組臨床綜合征[1]。據報道[2],甲狀腺病毒癥具有高發病率和死亡率,且易出現甲狀腺危象。及時準確的診斷和治療至關重要。中醫治療可分為治未病與治已病,尚未發展成甲狀腺危象之時,采取有效方法治療甲狀腺毒癥成為關鍵一步。本文將從陽明經證入手探討分析白虎加人參湯治療甲狀腺毒癥的理論依據,為臨床應用奠定基礎。現報告如下。
1 中醫對甲狀腺毒癥的認識
甲狀腺毒癥屬中醫“癭”病范疇[3]。甲狀腺疾病由內因外因作用而成,如《呂氏春秋·季春紀》云“輕水所,多禿與癭人”,說明環境因素致使該病發生。又如《諸病源候論·癭候》[4]謂“癭者,憂患氣結所生”。《濟生方·癭瘤論治》[5]曰“癭病者,多由喜怒不節,憂思過度,而成斯焉”。這些記載闡述了情志內傷為重要發病因素。《雜病源流犀燭·頸項病源流》[6]云“西北方依山聚澗之民,食溪谷之水,受冷毒之氣,其間婦女,往往生結囊如癭”。明確了水土飲食對疾病的影響,且對女性影響更大。本病基本病機屬于氣滯、痰凝、血瘀壅結頸前,但是隨著疾病的發展,長期郁、瘀可化熱化火,火熱內盛,進而累及心肝脾胃。心經受邪,則心悸怔忡,夜不能寐;累及肝經則肝火熾盛,出現急躁易怒;累及脾胃,則胃火熾盛,出現消谷善饑、大渴欲飲等。火熱之邪內迫津液外出,汗出則胃中干燥,勢必耗傷津液,氣隨津脫,出現疲乏無力、體質量下降等。病情逐漸發展可形成屬熱盛津傷的甲狀腺毒癥。
2 熱盛津傷證是陽明經熱病發展之候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并治》[7]云“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直接提出了陽明證的外在熱象證候。又認為“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此處“實”字,余無言《傷寒論新義·陽明上篇》[8]認為是“熱入而實”。喻嘉言首倡陽明當分經證與腑證,經證尚在陽明之表未成腑實之證,以大熱、大渴、汗出、脈洪大為主證,總之熱字貫穿始終。陽明經證燥熱偏盛本屬實證,但隨著津液不斷耗傷,則由實轉虛。
3 陽明燥熱傷津與甲狀腺毒癥發生機理相符合
3.1 陽明經多氣多血,易燥易熱 《素問·血氣形志篇》“陽明常多氣多血”。朱丹溪謂“氣有余便是火”,《古今醫鑒·火證》[9]云“火熱之病……其實一氣而已”。氣循行于周身,是人體必不可少之元素,但氣過多則會產生壅滯,即為氣實,實則化燥化火,《景岳全書·陽不足再辨》[10]云“夫氣本屬陽,陽實者故能熱”,繼而煎灼精氣血液,燥熱傷津,出現煩熱口渴;熱迫津液外泄則汗出;長期熱氣蒸騰,津液外泄,氣隨津泄,導致疲乏無力等。《得心集醫案·內傷門》“由是身中之氣,有升無降,所謂氣有余便是火。其頭眩難支者,氣升火亦生也……火既無出,只得奔走空竅……下利奔迫,辛庚移熱可知,時欲得食,消中之累又萌”。
3.2 太陽寒邪入于陽明,寒為燥化 太陽為寒水之經,外感邪氣犯于太陽,其邪不解,傳入陽明,出現“不惡寒反惡熱”,說明表邪已解,已入陽明本經。如《醫理真傳·陽明經證解》[11]云“太陽之寒邪未盡,勢必傳于陽明……當知寒邪走入燥地,即從燥而化為燥邪,乃氣機勢時之使然也”,這里很好地闡釋了寒邪入里化熱的病機過程。“若本經經癥,而傳入本經之里,則現口燥心煩,汗出惡熱,渴欲飲冷”,其癥狀一目了然。
以上兩點充分說明了陽明經燥熱傷津的病因病機,它表現出的一系列癥狀與甲狀腺毒癥高代謝綜合征相符合。
3.3 陽明經屬胃,熱盛則氣機逆亂 胃處中焦,胃主受納腐熟,胃為燥土屬陽,熱邪入于胃,二陽相爭,燥熱偏盛,則消谷善饑。與脾互為表里,胃失和降,則脾無所依附,升清之職則怠。脾胃為“中央土以灌四傍”,主運化水谷精微于全身,升清降濁功能失常,上不能濡養頭面,出現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外不能濡養四肢則手震顫。甚則“胃不和則臥不安”,出現失眠。脾不升清反降則出現大便溏泄。《素問·太陰陽明論篇》“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臟則瞋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這一些癥狀與甲狀腺毒癥表現的精神神經系統和消化系統癥狀相符合。
3.4 陽明經邪熱盛,子盜母氣 胃五行屬土為子,心五行屬火為母。胃經熱盛,子病犯母,子行亢盛,引起母行虛弱,則出現心悸、氣短、汗出、失眠等。如《古今醫案按·血證》[12]云“夜不寐者,由子盜母氣,心虛而神不安”,《重訂通俗傷寒論·傷寒總論》[13]云“脾陰將涸,勢必子盜母氣,陰竭陽越,故心煩不寐,汗出津津,最為虛脫危候”。此與甲狀腺毒癥心血管系統癥狀相符合。
4 治法大義
綜上所述甲狀腺毒癥屬熱盛津傷,治則以熱者寒之、虛者補之。《素問·經脈別論》云“陽明臟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瀉陽補陰”,故采用清泄陽明之熱,補氣以生陰津之法。
5 白虎加人參湯之理法
白虎加人參湯是治療陽明證熱盛傷津常用方劑之一。《溫病正宗·附方》[14]“名之曰白虎者,取西方金水之義,謂其能止熱邪之陽亢也”。其主治脈大而虛,《素問·經脈別論》“陽明脈至,浮大而短”。《醫學心悟·陽明經證》“脈長者,邪在陽明……用白虎者,治陽明經病,初傳于腑,邪未結實也”[15]。
5.1 汗、吐、下三法誤治邪熱傷津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26條“服桂枝湯,大汗出后,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7],本為熱病更用桂枝辛溫之劑發汗,津液損傷,如《重慶堂筆記·卷上》“夫病本熱也,加以桂枝之辛熱,故液為熱迫而汗大出,液去則熱愈灼,故大煩渴而脈洪大”。168條“傷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熱結在里,表里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干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7],采用吐下兩法,均為損傷津液之舉,胃中津液枯竭,加之邪熱滯留,故有燥渴。
5.2 燥熱傷津重癥 169條“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7],170條“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7],222條“若渴欲飲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7]。從以上3條可看出,其一,燥渴一癥是其必備,且飲水不能止其渴,本質為津傷嚴重。《圓運動的古中醫學·榮衛病罷里燥方》提出“雖能飲水而口仍燥,此燥熱傷津之所致。非補氣不能生津,于白虎湯內,加參以補氣,由氣生津也”。其二,當無表證,即已無太陽表證,已入陽明之里。其三,體感溫度不高,但仍惡熱。白虎加人參湯組成為石膏(碎,綿裹)、知母、粳米、人參、甘草(炙)。石膏辛甘大寒,解肌退熱、生津止渴清陽明之實熱。臣以苦寒質潤之知母,助石膏以清熱且滋陰液。君臣相須,退熱生津。粳米、甘草益胃護津,防止大寒傷中之弊,為佐使藥。人參一味是此方中關鍵藥味,白虎湯只能除燥熱,氣虛傷津之癥非加人參不足以補其功。《寓意草·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曰“若元氣素弱之人,藥雖外行,氣從中餒。輕者半出不出,留連為困,重者隨元氣縮入,發熱無休,去生遠矣。所以虛弱之體,必用人參三五七分”,意在扶正氣以祛邪,全非補養衰弱之意。《傷寒說意·太陽風寒白虎湯證》“若氣虛者,宜白虎加人參湯,保其中氣,恐其寒中而陽敗也”。然人參之功用不全在補益,尚有生津止渴之效,如《本草綱目》用“人參為末,雞子清調服一錢,日三、四服”治療消渴引飲。全方攻補兼備,以治療燥熱傷津之陽明證。由此也可看出,白虎加人參湯也能治療甲狀腺毒癥。張博明[16]運用白虎加人參湯治療陽明熱盛,氣津兩傷之甲狀腺危象2例,療效明顯。李賽美[17]善用經方治療甲狀腺功能亢進癥,認為甲亢初期屬胃火熾盛,主張運用白虎加人參湯加減治療。
6 驗案舉隅
患某,女性,38歲,行政職員。初診時間:2019年7月15日。主訴:怕熱伴汗出1周,乏力2 d。病史:自訴平時脾氣急躁易怒,1周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汗出且活動時加重,以為感冒,口服感冒藥無明顯改善。現自覺發熱、汗出、多食易饑,大便次數增多,乏力,伴有口干,手顫抖,小便尚可。舌苔白膩,脈洪無力。實驗室檢查:FT3 46.08 nmol/L,FT4 52.72 pmol/L,sTSH 0.0017 ulU/mL,TRAb 12.98 IU/L血常規及肝功能正常。西醫診斷:Graves病。中醫診斷:癭病,證型屬胃熱熾盛傷津。中醫處方:生石膏30 g,知母15 g,粳米15 g,黨參15 g,炙甘草10 g,蘆根15 g,柴胡15 g,枳殼15 g,白芍12 g。7劑,每日1劑,溫服,囑靜養,勿劇烈運動。二診:2019年7月22日。自訴發熱汗出癥狀緩解,仍容易饑餓,手顫抖略緩解,舌苔白膩,脈洪無力。鑒于藥已對癥,不更方,加石斛10 g,14劑,服法如上,囑定期復查。隨訪癥狀消失。
按:該患者平常急躁,肝氣郁滯明顯,郁而化火。肝木過盛,橫逆犯脾胃,肝移熱于胃,胃火熾盛,腐熟功能亢進出現多食善饑,進一步導致脾胃運化失司,出現大便量多。邪熱內迫,津液外泄,且營衛出于脾胃,故見惡熱、自汗,氣隨津脫,故乏力。脾胃受熱煎灼,傷津耗液,故口干。脾胃主四肢,失于濡養,故見震顫。脈洪無力,亦是人生傷津的表現。綜合考慮應為胃熱傷津耗氣,治以清熱瀉火,養陰生津,用白虎加人參湯加減,該方清胃熱生津液,顧護正氣。加蘆根以輔助清熱生津,柴胡、枳殼、白芍乃四逆散組成,合用以疏肝,木疏則肝氣不逆,胃土不受克。病證方藥相符,故療效顯著。二診患者仍覺饑餓、口干,乃胃火尚未完全去除,且津液已傷,故加石斛以養胃陰。
7 結語
甲狀腺毒癥治療的主要療法有抗甲狀腺藥物應用、放射性碘和手術治療[18],最直接的副作用包括肝損害、粒細胞減少,術后易成甲減等。中醫從病證結合的角度,有是證用是藥,根據其高代謝的癥狀與陽明經的燥熱傷津相吻合的情況,選用白虎加人參湯治療,既清其熱,又補其虛。但臨床運用報道尚不多,可能對中藥治療重癥略有顧慮,本文通過梳理陽明經證及白虎加人參湯的理論機制,以希望能對臨床診治提供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