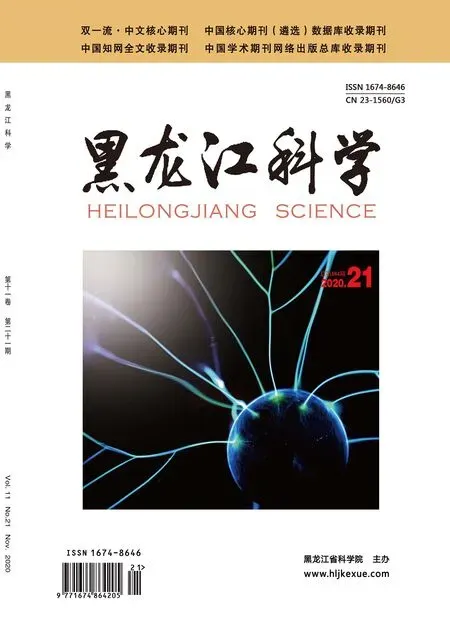民辦高校貧困大學(xué)生心理資助體系構(gòu)建研究
王孝雪
(山東華宇工學(xué)院,山東 德州 253034)
1 民辦高校貧困大學(xué)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問(wèn)題
1.1 自卑心理:約定俗成的觀念加劇
從高考的錄取分?jǐn)?shù)線來(lái)說(shuō),民辦高校學(xué)生的分?jǐn)?shù)要低于公辦高校學(xué)生的分?jǐn)?shù)。有些學(xué)生的家庭條件較好[1],但對(duì)于民辦高校中那些家庭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較為薄弱的學(xué)生而言,他們往往會(huì)因?yàn)榕c周圍同學(xué)存在較大差距而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家庭與學(xué)業(yè)都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在其他方面更是表現(xiàn)的極其不自信,會(huì)陷入失落、焦慮、郁郁寡歡、自我懷疑的心理狀態(tài)。同時(shí),他們也無(wú)心經(jīng)營(yíng)同學(xué)間的人際關(guān)系,主要表現(xiàn)為逃避社團(tuán)活動(dòng),甚至?xí)M(jìn)行自我否定、自我封閉。
1.2 嫉妒心理:貧富差距泛化
在生活費(fèi)供給充分的情況下,民辦高校中很大一部分學(xué)生的享受型消費(fèi)變多且追求名牌。在這種巨大的消費(fèi)差異下,民辦高校的貧困生往往會(huì)敏感多疑,尤其是在家庭、經(jīng)濟(jì)、成績(jī)等多種落差下,不免會(huì)產(chǎn)生嫉妒心理。
1.3 迷茫心理:個(gè)人規(guī)劃不充分
民辦高校一些貧困生沒(méi)有清晰的人生發(fā)展規(guī)劃,順利畢業(yè)是他們的短期目標(biāo)。他們經(jīng)常一時(shí)興起,盲目游走于各類社團(tuán)活動(dòng)中,但他們的綜合能力既沒(méi)有得到應(yīng)有的鍛煉,正常的學(xué)業(yè)也大受影響,無(wú)形的競(jìng)爭(zhēng)壓力使他們深感迷茫。
1.4 虛弱心理:自我調(diào)節(jié)不足,外部干預(yù)不到位
家庭現(xiàn)狀和經(jīng)濟(jì)壓力往往是貧困生無(wú)法正視的兩個(gè)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而來(lái)自家庭、學(xué)校及社會(huì)的心理干預(yù)救助工作不到位,致使一些學(xué)生在強(qiáng)烈自尊心的驅(qū)使下滋生了愛(ài)慕虛榮的攀比心理,具體表現(xiàn)為對(duì)貧困生這一標(biāo)簽的抗拒,甚至在貧困申請(qǐng)資料上弄虛作假。這些情況都對(duì)貧困生的身心健康極為不利,學(xué)校必須加以引導(dǎo)[2]。
2 民辦高校貧困生心理資助體系構(gòu)建現(xiàn)狀
其一,心理脫貧并未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引起重視,而是在經(jīng)濟(jì)脫貧方面取得了巨大進(jìn)展,使家庭困難的學(xué)生暫時(shí)解決了上學(xué)難的問(wèn)題。民辦高校對(duì)于貧困生的心理資助不能簡(jiǎn)單停留在談心談話環(huán)節(jié),還應(yīng)積極開(kāi)展大學(xué)生勵(lì)志教育、感恩教育及榜樣談話等活動(dòng),同時(shí)借助新媒體和網(wǎng)絡(luò)輿論的導(dǎo)向功能來(lái)使更多的人關(guān)注貧困生的心理問(wèn)題并有效解決。
其二,民辦高校在優(yōu)惠政策、資金支持方面較為匱乏,對(duì)貧困生的資助力度十分有限,覆蓋的貧困生人數(shù)也相對(duì)較少。據(jù)教育部信息管理中心的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助學(xué)貸款申請(qǐng)條件苛刻、流程復(fù)雜,其他資助方式也迫于民辦學(xué)校資助經(jīng)費(fèi)有限而使得資助效果并不理想。此外,資助渠道受限、資助范圍小、資助力度小、資助短期單一,致使未受資助的貧困生難以緩解心理的焦慮感,甚至?xí)X(jué)得是自己讓家庭經(jīng)濟(jì)變得更加困難,會(huì)產(chǎn)生愧疚感。
其三,輔導(dǎo)員作為開(kāi)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行為主體,對(duì)于貧困生心理資助認(rèn)知方面的知識(shí)嚴(yán)重不足。民辦高校輔導(dǎo)員是教育學(xué)、心理學(xué)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學(xué)生管理相關(guān)專業(yè)畢業(yè)的較少,固然參加過(guò)各種培訓(xùn),但還遠(yuǎn)遠(yuǎn)不能滿足學(xué)生的需求。
3 民辦高校構(gòu)建貧困大學(xué)生心理資助體系的策略
3.1 調(diào)動(dòng)家庭、學(xué)校、社會(huì)的參與積極性,形成三方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
構(gòu)建貧困生心理資助體系必須以學(xué)生為中心,從家庭、學(xué)校(教師、同學(xué))及社會(huì)三方入手,對(duì)貧困生給予包括物質(zhì)、精神在內(nèi)的強(qiáng)有力支持。例如,加大政府助學(xué)貸款的資助力度,鼓勵(lì)企業(yè)、名人或成功人士參與到貧困生資助體系建設(shè)中來(lái),并在民辦高校中增加高額的獎(jiǎng)學(xué)金、助學(xué)金制度[3]。高校可為學(xué)生提供更多的勤工儉學(xué)崗位,以解決貧困生的生活難題。同時(shí),相關(guān)責(zé)任主體應(yīng)與貧困生的家庭建立聯(lián)系,及時(shí)了解學(xué)生的思想動(dòng)態(tài)。
3.2 引入制度化的資助評(píng)估體系,創(chuàng)立貧困生心理資助檔案
需將心理健康指導(dǎo)在院系輔導(dǎo)員及班干部間進(jìn)行有效傳播,不斷增加傳遞信息的通道,以便對(duì)貧困生暴露出的心理問(wèn)題進(jìn)行毫無(wú)保留地反饋。反饋形式可以談心談話、調(diào)查問(wèn)卷、專家會(huì)診為主,并對(duì)反饋結(jié)果進(jìn)行整理,創(chuàng)立貧困生心理資助檔案[4]。
3.3 豐富貧困生心理教育手段,加強(qiáng)對(duì)心理教育平臺(tái)的運(yùn)用
民辦高校要打造出特色互聯(lián)網(wǎng)心理教育平臺(tái),精心設(shè)置與心理健康相關(guān)的課程,如非暴力溝通、慢生活體驗(yàn),等等。同時(shí),應(yīng)整合與心理學(xué)相關(guān)的影像資源,及時(shí)呈現(xiàn)貧困生感興趣的心理內(nèi)容,如心理問(wèn)題測(cè)試、答疑類小游戲,鼓勵(lì)貧困生進(jìn)行自主體驗(yàn),并向其提供在線咨詢服務(wù)。只有心理知識(shí)普及和渠道拓新雙管齊下才能實(shí)現(xiàn)心理健康教育制度的創(chuàng)新。
3.4 軟硬兼施,有效提升民辦學(xué)校對(duì)貧困生心理的資助水平
能夠提供心理教育的方式有很多,但高校教師往往不具備心理咨詢資格證,相關(guān)工作人員也不能各司其職地對(duì)貧困生所出現(xiàn)的不同問(wèn)題進(jìn)行授課或解惑。只有豐富心理資助手段和完善流程管理,才能讓資助人員因人而異地變換手段來(lái)對(duì)貧困生進(jìn)行有針對(duì)性的教育。例如,采取認(rèn)知療法對(duì)迷茫焦慮的貧困生進(jìn)行治療,對(duì)深陷家庭經(jīng)濟(jì)貧困及過(guò)往成績(jī)不理想這一狀態(tài)的貧困生進(jìn)行精神分析,可合理運(yùn)用積極療法幫助不自信的貧困生擺脫自卑心理[5]。
3.5 增加資助評(píng)價(jià)與反饋環(huán)節(jié),實(shí)現(xiàn)發(fā)展型資助育人
發(fā)展型資助的意義在于幫助貧困生樹(sh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jià)值觀。心理資助構(gòu)建體系中,應(yīng)增加資助評(píng)價(jià)與反饋環(huán)節(jié),從而對(duì)一系列心理資助工作進(jìn)行客觀評(píng)價(jià),并通過(guò)學(xué)生受資助之后的誠(chéng)信表現(xiàn)、勤儉事跡、學(xué)習(xí)成績(jī)來(lái)決定是否繼續(xù)對(duì)該生進(jìn)行資助。此外,還應(yīng)關(guān)注學(xué)生走上工作崗位后的表現(xiàn),并對(duì)受資助學(xué)生進(jìn)行跟蹤回訪,最大限度提高學(xué)生資助工作的價(jià)值,以達(dá)到鞏固強(qiáng)化育人成果的目的[4]。
- 黑龍江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中職學(xué)生職業(yè)素養(yǎng)培養(yǎng)問(wèn)題與對(duì)策研究
- 營(yíng)地教育獨(dú)立營(yíng)營(yíng)會(huì)執(zhí)行風(fēng)險(xiǎn)分析
——以A營(yíng)地獨(dú)立營(yíng)營(yíng)會(huì)為例 - 許昌市初中生體育參與影響因素分析
——以襄城縣東城區(qū)中學(xué)為例 - “職教云課堂SPOC課程+即時(shí)通訊工具”教學(xué)模式在外科護(hù)理學(xué)項(xiàng)目化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分析
- 基于任務(wù)導(dǎo)向與問(wèn)題驅(qū)動(dòng)的電工電子學(xué)實(shí)驗(yàn)教學(xué)改革探索
- 民族院校國(guó)際金融課程教學(xué)改革的研究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