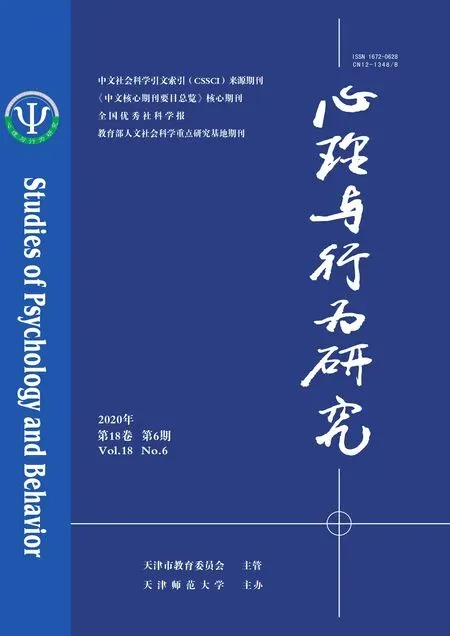不良生活經歷對大學生冷酷無情特質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 *
王小鳳 燕良軾
(1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長沙 410081) (2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生工作部,長沙 410004)
1 問題提出
近年來大學校園中惡性事件偶有發生,其中有的犯罪者表現出來的麻木、冷酷讓人不寒而栗,他們為何會如此冷酷無情?
冷酷無情特質(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CU)是指對他人冷漠、缺乏罪惡感、低共情的一種人格傾向(Frick, 2004),主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SM-Task Force Arlington VA US, 2013):缺乏懊悔或內疚感、缺乏同情心、不在乎表現、情感膚淺或情感缺乏。CU 特質往往與個體自我報告的親社會行為負相關(Roose, Bijttebier, Decoene, Claes, & Frick,2010),是品行障礙重要的早期標記變量(王孟成, 鄧俏文, 張積標, 羅興偉, 吳艷, 2014)。與低CU特質個體相比,高CU 特質個體在兒童和青少年階段均表現出更嚴重、更穩定和更具攻擊性的反社會行為,在成年期易演變為暴力罪犯(Scheepers,Buitelaar, & Matthys, 2011)。CU 特質水平較高的暴力犯,其暴力行為往往更加嚴重和殘忍,而且再犯率也更高(Mu?oz & Frick, 2012)。
盡管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CU 特質具有很強的遺傳基礎(Viding, Jones, Paul, Moffitt, & Plomin,2008),但也有不少研究發現CU 特質與一些重要的環境因素相關,如不良生活經歷(Dembo,Schmeidler, & Childs, 2007; Kimonis, Centifanti,Allen, & Frick, 2014)。不論是直接的受害經歷(如被虐待、被忽視),還是目睹創傷性事件(如目睹暴力行為),均與個體CU 特質顯著正相關(Kimonis,Frick, Munoz, & Aucoin, 2008)。已知與CU 特質增強有關的不良生活經歷主要有暴力暴露(Howard,Kimonis, Mu?oz, & Frick, 2012)、功能失調的家庭教養方式(Fanti & Munoz, 2014; Viding, Fontaine,Oliver, & Plomin, 2009; Waller et al., 2015)、不良同伴關系(Fontaine, McCrory, Boivin, Moffitt, &Viding,2011)、交往不良同伴(Kimonis, Frick, &Barry, 2004)等。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不良生活經歷可以預測大學生的CU 特質水平。
不良生活經歷如何影響個體的CU 特質呢?一些研究者認為,長期暴露在目睹暴力的環境中會影響個體移情和道德的正常發展(Farrell & Bruce,1997),可能導致對他人的痛苦信號不敏感(Howard et al., 2012),從而形成冷漠無情的人格。一些關于反社會行為的發展理論認為,虐待會降低個體的生理喚醒,進一步破壞情感功能,并對移情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Dackis, Rogosch, & Cicchetti,2015),從而增加個體CU 特質水平提升的風險。還有研究者發現,一些不良的家庭教養方式(如管教不一致、體罰等)可能會讓個體觀察并習得一些不良互動或者暴力的社交互動方法,而不是親社會行為和情感互動模式,從而導致CU 特質水平的升高(Lynam et al., 2009)。此外,有研究發現,交往不良同伴可以正向預測青少年道德推脫(高玲, 王興超, 楊繼平, 2015),而道德推脫會導致個體對違反道德行為的普遍容忍,導致個體在考慮他人的利益時缺乏同理心,進而變得冷酷無情(Muratori et al., 2017)。
本研究認為心理彈性可能是不良生活經歷影響CU 特質的重要中介變量。Staub(2005)提出“源于苦難的利他主義”(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ABS)的概念,用于描述個體不僅沒有因遭受苦難而變得冷漠無情,反而變得更有同情心、會主動去關心和幫助他人的現象。一些實證研究也驗證了該概念(Frazier et al., 2013; Vollhardt & Staub,2011),而個體能否將過去的痛苦經歷進行意義轉化是遭遇不良經歷個體出現ABS 的重要因素(Staub, 2005)。心理彈性是指個體經歷了逆境或者創傷后仍能保持或很快恢復正常心理機能,是“自我調適機制”的成功應對(Luthar, Cicchetti, &Becker, 2000)。有研究發現,富有心理彈性的人往往擁有較高的情緒覺知或管理能力、沖動控制能力和移情能力(Reivich & Shatté, 2002),在面臨困難時敢于樂觀面對,并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當別人有困難時,也傾向于以相同的方式去安慰和幫助(張睿, 2011)。心理彈性的增強有助于個體親社會傾向的提高(李會麗, 陳琦,2016),親社會行為是個體心理彈性積極發展的標志(Bell, Romano, & Flynn, 2013; Griese & Buhs,2014)。而依據 Garmezy,Masten 和Tellegen(1984)提出的心理彈性挑戰模型(適度的生活事件可以增強個體的心理彈性,但如果生活事件持續時間太長或程度太嚴重,則會有損個體的心理彈性),由于不良生活經歷的嚴重程度遠高于一般的負性生活事件,因此其可能對個體的心理彈性更具破壞性,一些實證研究也驗證了這一點(李奕慧, 劉小珍, 2016; 劉珊珊, 曹楓林, 李玉麗, 2011)。綜上,提出本研究的假設2:心理彈性能在不良生活經歷與大學生CU 特質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在重大生活事件之后,個體的外部資源(社會支持)有助于增加個人過渡期間發生的積極變化(Sommer, Baumeister, & Stillman,2012)。社會支持作用機制中的緩沖器模型認為,社會支持可以通過減弱或阻止個體對壓力事件嚴重性的主觀評價,為個體提供解決問題的策略,從而緩沖壓力事件對個體發展的不良影響(Cohen &Wills, 1985),即社會支持在壓力與個體發展之間起調節作用。已有社會支持的研究往往從不同社會支持的來源(如社會、家庭)或性質(客觀支持和主觀支持)和社會支持整體性的角度進行(宋潮, 邢怡倫, 董舒陽, 王建平, 2018),但社會支持能否對心理彈性起到保護效應,有賴于其是否能有效地被個體所利用(王志杰, 張晶晶, 潘毅, 高雋, 2014)。Humphrey 和Symes(2010)也認為,對處境不利兒童只提供社會支持是不夠的,應重點考慮社會支持的利用情況。還有研究發現,社會支持中只有社會支持利用度能夠預測男性戒毒者的心理彈性水平(張潤苗, 2013)。因此,基于社會支持作用機制的緩沖器模型和以往研究,提出假設3:社會支持利用度能在不良生活經歷與心理彈性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個體-環境交互作用模型”指出,個人特點(心理彈性)和他/她的環境(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可以緩沖高危因素和創傷性應激因素的不利影響(Lerner, Lerner, Almerigi, & Theokas, 2006)。人類發展的“保護因子-保護因子模型”(protectiveprotective model)則認為,不同保護因子在預測發展結果時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即一種保護因子(如社會支持利用度)對結果變量(如CU 特質)的預測作用可能隨另一種保護因子(如心理彈性)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存在“促進假說”和“排除假說”兩種觀點(鮑振宙, 張衛, 李董平, 李丹黎, 王艷輝, 2013):(1)“促進假說”,即一種保護因子可能增強另一種保護因子對結果變量的預測作用。根據該假說,心理彈性對大學生CU 特質的影響更多體現在高社會支持利用度而非低社會支持利用度的情況下。(2)“排除假說”,即一種因子反而會削弱另一種保護因子對結果變量的預測作用。根據該假說,心理彈性對CU 特質的負面影響更多體現在低社會支持利用度而非高社會支持利用度的情況下。考慮到目前研究證據仍較缺乏,本研究僅對社會支持利用度對心理彈性與CU 特質關系的調節作用進行探索性分析,而不對其具體模式作明確預期。據此,提出假設4:社會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彈性與CU 特質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綜上,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圖1),探討不良生活經歷與大學生CU 特質的關系,考察心理彈性在二者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并檢驗社會支持利用度在不良生活經歷與心理彈性、心理彈性與 CU 特質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從而回答不良生活經歷“如何”及“何時”影響大學生CU 特質的問題。

圖1 理論假設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抽樣法在湖南省4 所大學抽取大學生2000 名,以班級為單位,由研究生主試使用統一問卷進行集體施測。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1872 份,有效回收率為93.60%。其中,女生1095 人(占比58.49%),男生777 人(占比41.51%);大一899 人(占比48.02%),大二511 人(占比27.30%),大三462 人(占比24.68%);年齡范圍18~22 歲,平均年齡19.48±1.16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不良生活經歷量表
采用Lim 和DeSteno(2016)研究中使用的不良生活經歷量表(Adversity Life Experience Scale)。在征得Professor Daniel Lim 的授權同意下,首先由研究者將英文問卷翻譯成中文,回譯則由一名精通英文的心理學研究者完成,翻譯中不一致的地方由兩位譯者討論一致,確保翻譯后的問卷忠實于原問卷,最終形成中文版正式量表。該量表共28 個條目,包含6 類不良生活經歷:(1)傷害/疾病;(2)暴力;(3)親友喪失;(4)人際關系事件;(5)社會壓力/環境壓力;(6)自然災難/人為災禍。這6 類不良生活經歷已被列入創傷診斷訪談條目(Seery, Holman, & Silver, 2010)。被試對6類不良生活經歷的嚴重性、頻次和新近性(最后一次發生的時間)進行0~4 分的評估,總不良生活經歷分數通過不同類型經歷的嚴重性、頻次和新近性的均分加以計算。使用Mplus7.4 軟件對量表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的結果表明,該量表的結構效度良好:χ2/df=6.11,CFI=0.92,TLI=0.91,RMSEA=0.053,SRMR=0.047。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
2.2.2 冷酷無情特質問卷
采用Wang 等(2017)修訂的中文版冷酷無情特質簡版問卷(Inventory of Callous-Unemotional,ICU),包括不關心(uncaring)、冷酷(callousness)兩個維度,共11 題。量表采用4 點計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4 代表“完全符合”。其中有4個反向計分題,即項目2、4、8、9,對這4 個項目進行反轉處理之后,所有項目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的冷酷無情特質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7。
2.2.3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1994)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中的社會支持利用度分量表,共3 題。得分越高,說明社會支持利用度越高。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0。
2.2.4 心理彈性量表
采用高志華和楊紹清(2013)修訂的Wagnild-Young 心理彈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11, RS-11)中文版,共11 題,采取7 點計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說明心理彈性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
2.3 數據分析思路
所有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均采用方杰、張敏強和邱皓政(2012)所推薦的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法。為實現該方法,采用Hayes(2012)編制的SPSS 宏中的Model58(Model58 假設中介效應的前半段及后半段效應受到調節,與本研究理論假設模型一致)。在控制性別、年齡條件下,通過5000 次樣本抽樣估計中介及調節效應95%置信區間的方法對理論假設模型進行檢驗(連帥磊,孫曉軍, 牛更楓, 周宗奎, 2017)。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檢驗
由于本研究僅采用被試自我報告的方法來收集數據,結果可能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問卷排版、施測的過程中對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進行了程序控制,如匿名填寫、部分項目反向計分等。此外,采用Harman 單因子模型法來檢驗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龍立榮, 2004),即假定四個量表所有的題目同屬一個因子,使用Mplus7.0 軟件進行CFA。結果表明,單因子CFA 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標都很差:χ2=126759.056,df=6669,CFI=0.287,TLI=0.275,RMSEA=0.099,SRMR=0.098,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
表1 列出了各個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矩陣。結果發現,本研究中大學生CU 特質的均分為1.64,低于2 分(量表等級水平為“有點符合”),說明大學生CU 特質整體水平較低;不良生活經歷與CU 特質顯著正相關,與心理彈性顯著負相關,說明不良生活經歷可能是大學生CU 特質的助長因素、心理彈性的風險因素;社會支持利用度與心理彈性顯著正相關,與CU 特質顯著負相關,說明社會支持利用度可能是心理彈性的保護因素,CU 特質的風險因素。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和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3.3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首先,采用多元回歸,在控制性別和年齡的條件下,考察不良生活經歷對CU 特質影響的總效應,結果顯示不良生活經歷對大學生CU 特質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R=0.22,R2=0.05,F(3)=31.26,β=0.19,t=8.57,p<0.001]。之所以將性別和年齡作為控制變量,一方面是因為研究一致發現CU 特質存在性別差異(肖玉琴, 張卓, 宋平, 楊波, 2014),另一方面,雖然CU 特質表現出了較強的穩定性和遺傳可能性,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可能發生變化。如羅貴明(2016)研究發現,青少年的CU 特質存在年齡差異。還有研究發現,隨著青春期年齡的增長,男性CU 特質者的認知共情逐漸發展成正常水平(Dadds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將年齡和性別作為控制變量。
其次,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提出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程序,本研究采用Hayes(2012)編制的SPSS 宏(http://www.afhayes.com),在控制性別和年齡的條件下,構建了以心理彈性為中介變量,以社會支持利用度為調節變量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對上述方程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當放入心理彈性這一中介變量以后,不良生活經歷對心理彈性及CU 特質的預測作用均顯著,心理彈性對CU 特質的預測作用顯著,且心理彈性的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95%置信區間的上下限不包含0(見表3),表明心理彈性能夠在不良生活經歷對CU 特質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不良生活經歷與社會支持利用度乘積項對心理彈性的預測作用、心理彈性與社會支持利用度乘積項對CU 特質的預測作用均顯著,說明社會支持利用度能在不良生活經歷對心理彈性、心理彈性對CU特質的影響中起調節作用。

表3 心理彈性的中介效應
為了更清楚地揭示該交互效應的實質,本研究將社會支持利用度按正負一個標準差分為高低組,采用簡單斜率檢驗考察社會支持利用度在不良生活經歷與心理彈性關系中的作用。調節效應如圖2 所示,社會支持利用度較高的被試,不良生活經歷對心理彈性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其簡單斜率為-0.17(t=-5.37,p<0.001);而社會支持利用度水平較低的被試,不良生活經歷對心理彈性的預測作用不顯著,其簡單斜率為-0.01(t=-0.19,p>0.05)。

圖2 社會支持利用度對不良生活經歷與心理彈性的調節
與此同時,本研究還采用簡單斜率考察了社會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彈性與CU 特質關系中的作用。調節效應如圖3 所示,社會支持利用度較高的被試,心理彈性對CU 特質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其簡單斜率為-0.42(t=-15.16,p<0.001);社會支持利用度較低的被試,心理彈性對CU 特質的負向預測作用更顯著,其簡單斜率為-0.48(t=-19.01,p<0.001),表明隨著個體社會支持利用度水平的降低,心理彈性對CU 特質的預測作用呈逐漸增加趨勢。因此,該交互模式符合“保護因子-保護因子模型”的排除假說而非促進假說。

圖3 社會支持利用度對心理彈性與冷酷無情特質的調節
進一步分析表明,心理彈性在不良生活經歷與大學生CU 特質關系中的中介作用會受到社會支持利用度的調節,即隨著社會支持利用度的提高,心理彈性的中介效應呈上升趨勢(見表4)。

表4 在社會支持利用度的不同水平上心理彈性的中介效應
4 討論
4.1 不良生活經歷與大學生CU 特質的關系
本研究結果表明,不良生活經歷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的CU 特質,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Kimonis et al., 2008)。遭遇嚴重不良生活經歷的個體可能會深陷壓倒一切的背叛感、被拋棄感之中,因此關于世界是仁慈的或有意義的信仰也會減弱,還可能會形成“人是邪惡的、世界是一個危險之處”的想法(Schuler & Boals, 2016),從而變得冷酷無情,甚至用攻擊、暴力來報復社會和他人。因不良生活經歷導致的傷害和暴力會以暴力循環的方式進行的觀點已得到不少實證研究的支持(Dodge, Bates, & Pettit, 1990)。
4.2 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
在證實不良生活經歷與CU 特質的關系后,探討不良生活經歷怎樣影響CU 特質的問題就顯得很重要。中介變量是不良生活經歷影響CU 特質的內在和實質性原因。本研究探討了心理彈性在不良生活經歷與大學生CU 特質之間關系的中介效應。結果發現,心理彈性這一變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遭遇不良生活經歷大學生的CU 特質水平。因此,在看到不良生活經歷對大學生心理發展存在負面影響的同時,更要注重引導大學生認識到不良生活經歷的積極面,如不良生活經歷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個體的潛能,促使個體對自己和人生進行更深刻的思考,對他人遭遇的不良生活經歷更能感同身受。從而讓不良生活經歷成為心理彈性發展的催化劑,進而降低不良生活經歷對大學生CU 特質的不利影響。
4.3 社會支持利用度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利用度在不良生活經歷與心理彈性兩者關系中的調節作用顯著。具體來說,個體社會支持利用度越高,不良生活經歷對其心理彈性的損害會更大。需要指出,該調節模式并不意味著社會支持利用度是心理彈性的風險/不利因素。如圖2 所示,高社會支持利用度個體的心理彈性明顯高于低社會支持利用度的個體。原因可能是,社會支持利用度高的個體,其心理彈性也處于較高水平,因此隨著不良生活經歷水平的升高,其心理彈性的下降趨勢也就更明顯。而低社會支持利用度個體的心理彈性水平原本就不高,因此不良生活經歷對其影響較小。所以,本研究結果與社會支持作用機制的緩沖器模型一致,即社會支持利用度是心理彈性重要的保護因素。因此,要注重引導遭遇不良生活經歷的大學生主動利用自己的社會支持,積極求助,這樣才能更多感受到外界的溫暖和關心,盡快從不良生活經歷中恢復,從而保持心理健康。
本研究還發現,社會支持利用度在心理彈性與CU 特質兩者關系中的調節作用顯著。而且隨著個體社會支持利用度水平的降低,心理彈性對大學生CU 特質的負向預測作用更大。該調節模式符合“保護因子-保護因子模型”的排除假說而非促進假說。以往有關社會支持與心理彈性交互效應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即相對于高社會支持的個體,心理彈性的保護效應在低社會支持的個體中更顯著(席居哲, 桑標, 左志宏, 2011)。已有研究表明,不論是不良生活經歷發生前后還是發生時,個體所得到的支持都可促進其親社會行為,而社會支持利用度直接影響到個體是否能真正接受到幫助。因此,社會支持利用度較低的個體可能會更容易感到人情淡漠,對他人、社會產生失望甚至憤恨的情緒,進而變得冷酷無情。而遭遇不良生活經歷時,較好的自我恢復、調適功能(即心理彈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個體對外界支持的依賴,有效補償不能利用外界支持的消極效應,從而降低CU 特質提升的風險。因此,要特別注重培養低社會支持利用度大學生的心理彈性。
總的來說,本研究提示,對待遭遇不良生活經歷的大學生,應充分發揮心理彈性的單獨作用和適當發揮社會支持利用度的調節作用,降低其CU 特質水平升高的風險,這對于大學生心理品質的積極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促進尤為重要。
5 結論
本研究發現:(1)當大學生遭遇的不良生活經歷水平越高時,CU 特質水平也會較高。(2)不良生活經歷既對大學生CU 特質產生直接影響,也通過心理彈性對大學生CU 特質產生間接影響。(3)社會支持利用度是心理彈性中介不良生活經歷與大學生CU 特質關系的調節變量。具體而言,不良生活經歷對大學生心理彈性的影響,隨著社會支持利用度的增加而增加;心理彈性對大學生CU特質的影響,隨著社會支持利用度的降低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