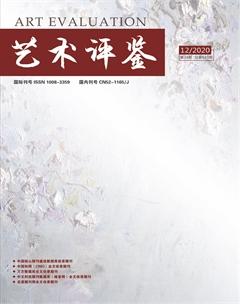博弈的戲劇與融匯的舞劇
黃婉蓄
摘要:本文從戲劇與舞劇的關系問題出發,以現代舞劇《雷和雨》為分析對象,系統考察了舞劇作品在情節設計、敘事方式、創作視角等方面的藝術手法。通過現代性、女性主義等思潮對藝術的影響,揭示了戲劇文學藍本與舞劇情節之間的依附關系。在作品的戲劇性呈現方面,通過對劇中幾個代表女性進行剖析,闡釋了舞劇在敘事層面人物關系的設置、文字語言至肢體語言的轉化,了解創作視角上表現出的藝術思維,對文學母題的分化與重構,探討了戲劇與舞劇在創作實踐上既互為聯系又相互獨立的藝術特性。
關鍵詞:戲劇 ?舞劇 ?《雷和雨》 ?敘事方式 ?創作視角
中圖分類號:J8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0)24-0153-06
提及與舞蹈藝術緊密相關的其他藝術,尤其以舞蹈藝術為主體視點的分析,首先映入研究視線的應是戲劇。吳曉邦先生在1994年的一篇文中記述了與友人應云衛在藝術創作中的一些回憶:“尤其戲劇和舞蹈是關系最為密切的兩門藝術,因此我們兩人幾乎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了”。也在文中記錄了1945年兩人有關對吳曉邦先生舞蹈作品《生之哀歌》《網中人》不同舞蹈人物的動作塑造問題的探討。除此之外,建國初期吳曉邦先生在構建“新舞蹈”概念時也有對二人舞中舞蹈情節、舞蹈情感的認識。可見,在舞蹈理論研究的發軔階段,舞蹈與戲劇的關系問題就已經走入舞蹈研究視野了。尤其作為兼容敘事和抒情功能的舞劇,其與戲劇藝術的關系在創作視角層面上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應用型理論意義。
戲劇藝術是塑造人物、揭示關系的藝術,對戲劇藝術的研究大多從戲劇沖突入手,進而再剖析戲劇結構。因此,戲劇沖突或者說人物的沖突、關系的沖突成為了戲劇表現的首要核心。舞劇也是以此為線索進行結構的藝術,雖然在表現手法上舞蹈動作語言與文字語言有很大差別,但敘事的任務仍然居為首要。可見,若要剖析舞劇與戲劇的關系問題,關鍵點在于對關系沖突的探索。就戲劇沖突而言,其體現的是人類世界最本質的驅動力,可以理解為對抗、欲望或是斗爭、博弈。人類在構建自我主體和他者客體時,“對立”是一個基本關系,在二者對立的基礎上疊增,這就有了多維的交織關系,于是便構成了社會。對立、融合、分裂、纏繞等等一系列關系既是現實主義的,同時也在浪漫色彩的藝術中得以發展。因此,戲劇的主色是博弈的,戲劇也是在博弈的過程中發展的。可以說,舞劇也是以戲劇中的博弈沖突為主體的,但舞劇在創作視角上又與戲劇的創作截然不同。舞劇在肢體語匯上的特殊性決定了舞劇敘事的獨特表達,繼而在舞劇的編劇和創作上就能體現出其與戲劇的不同。對兩者關系的考察也能在具體劇作的分析中逐漸清晰。
《雷雨》是劇作家曹禺的一部經典之作,以這部戲劇為藍本進行的舞蹈創作也不在少數,無論是獨立的舞蹈作品還是舞劇,都在創作上希望借助經典的光芒再散發熒熒光點。本文選擇現代舞劇《雷和雨》進行創作視角分析,以期在闡釋過程中進一步思考和歸納戲劇與舞劇這兩門藝術之間的關系。
一、從舞劇情節到戲劇情節——依附關系
舞劇《雷和雨》的基本情節是在文學劇作《雷雨》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在人物的刻畫和關系鏈條上,在舞種類型設計上進行體現。例如情人關系的雙人舞、情敵關系的三人舞、關系糾葛的群舞等。如果將男女之間的追逐稱之為“性別的游戲”,那么了解和掌握其中的游戲規則就成了角逐勝負的重要因素。舞劇中四人舞中你追我趕的動作路線由三角單向發展覆增至四角多向發展,其中有兩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追逐、兩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追逐,四者碰撞,必有兩者交匯,兩者被排斥在外。基本相同的奔跑、驟停、轉身等舞蹈動作,利用了位置的變化、節奏的行進,巧妙地在男女關系中說清了女人之間的關系。這種說明不是濃墨重彩的,包括繁漪被侍萍孤傲的愛情神話所同化也都是利用短促的群舞輕描淡寫的,當侍萍夸夸其談儼然早已獲取了擄獲男人的必勝法寶,而繁漪并沒有跟侍萍做過多的肢體交流,只是在侍萍自詡周樸園青春事件中美麗的告別者時,恍惚的將自我犧牲當作一種自我滿足,其舞蹈身體朝向并不在意侍萍的出現。如果對蘩漪所處的時代、自身教養、家庭屬性等進行分析,不難看出蘩漪具有資產階級女性和舊式女人的兩種特質。新女性意識讓她敢于追求周萍的愛,舊式女性的本性又讓她困陷于周樸園的控制,因此說明了那個時代的女性在生存矛盾中產生的自我覺醒和自救意識是極其微弱的。
與繁漪相比,侍萍可能是一位苦難深重的好女人,但是她的主體意識還是在人性的本質中存在著的,舞劇《雷和雨》中,編導有意地使用舞蹈肢體動作和聲音語言共同還原了她懦弱、虛榮、狹隘、嫉妒、依賴的真實習性。任何人都阻止不了衰老的步伐,而對于女性來說這一點又極為殘酷,現代社會很多女性通過炫耀自己任憑時光流逝依舊光鮮的容顏來達到欺人和自欺的效果,以保留自己在社會領域中的地位。可以說,舊時代的好女人不是主體,她以客體方式存在的功能是為男性生下合法的繼承人,侍萍就是這類女性的代表。舊時代的壞女人也不是主體,她的客體功能是滿足男性性欲,繁漪是代表。雖然侍萍和繁漪在時代背景下的客體功能得以名正言順地被利用,但是女性主體意識的成長仍然滯后。舞劇《雷和雨》基本保留了原作故事情節的各個線索,但在人物發展線索上有所改變。例如,劇中侍萍的幻想終究像泡沫似的容易破滅,當周樸園露出男人偽善的本性后,面對已經飽受多年的苦難,侍萍依然用女性防御式的舞蹈體語默默接受男性進攻式舞蹈體語的牽制被男人推搡著,女人仍然沒有靠這一絲被男人迷戀的籌碼完全控制男人。可以說,在這場性別斗爭中侍萍作為舊式傳統女性的代表毫無占上風的機會,但舞劇加入該段后給觀眾帶來的不適之感,正是編導在創作侍萍形象時采用了還原女性自卑本質的視角及手法,雖略帶夸張,但也確實帶有真實性。仔細分析,這種情節設計實際上是在原作劇情的基礎上產生的,既沒變化、也有變化。沒變的是魯侍萍、周樸園這兩個直接相連的人物沖突,變化的是對魯侍萍在這段對立矛盾的關系中又煥發出的女性色彩和現實色彩。
雖然《雷和雨》的故事情節著重圍繞三位女性展開,蘩漪、四鳳和魯侍萍三個角色表現出的女性自覺與自省依然是編導圍繞著戲劇原作的情節進行的二次創作。同樣,在《雷和雨》之后出現的舞劇《情殤》也是在《雷雨》的情節基礎上而改編的作品,雖然作品使用了諸多方式去增加其戲劇性,但對于人物和人物之間關系的塑造仍然是《雷雨》的延續。由此可見,舞劇情節對于戲劇情節存在著一種依賴和依附的關系。文學劇作《雷雨》給舞劇創作帶來了更為廣泛的欣賞群體,這一點無疑是情節的功勞。尤其《雷雨》在情節上的悲劇精神已經在近代文學中演化成了一種獨特的悲劇觀念,影響著各個藝術門類的創作。恩格斯對悲劇性沖突的概括,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指明了帶有本質意義的悲劇特征,是衡量古今中外的一切悲劇作品的共同尺度。對于悲劇的釋讀和再塑造成為了藝術創作中一股強勁的驅動力,因此,戲劇情節,特別是悲劇情節,給予一切表現故事的藝術形式以不竭的源泉。
二、舞劇與戲劇的敘事方式——連帶和轉化關系
(一)人物之間的關系連帶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認為“悲劇感興趣的是人類而不是事件”。人物在劇作情節的構成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雷雨》原著中的侍萍是一個典型的舊中國勞動婦女的形象,善良、正直、備受欺辱和壓迫。中國封建禮法早就將性和道德統一的合理性否定掉了,侍萍應尊崇的女德也早以將她在愛情里的權利和性別特征否定掉了。經過舞劇的改編,《雷和雨》中的侍萍表現出了女性在男性世界中僅能存在一瞬間的自戀和自豪,這并不是毫無緣由的,而是在她被周樸園多年的留戀和追憶感動之后獲得的。看似是女性隨著時代環境的進步獲得了一定的主體生存意識,但其實這是一種自欺,一種來源于女性性別自卑中的自欺,是一種病態的心理和淺薄扭曲的觀念。
從女性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繁漪在考察自己生存境遇的同時,首先挑戰了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男性在兩性關系上具有強權地位,并持這一強權占有、使用、掌控女性等等。這些傳統觀念實際都來源于父權制文化對男女性別角色不同的要求與規定,是由后天的、社會的力量決定的,與性的生物學基礎并無內在關聯。而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定位也就在這些規定之中被塑就了,成為影響久遠且強大的傳統力量,女性由此淪為一個受控制、受支配的“次”群體。在女性解放運動浪潮中,女性不斷深入的認識到作為獨立的“人”的思想、情感價值,作為單獨個體的“人”,會不可避免地被社會和環境影響著、改變著,當外界發生變化時,作為具有社會屬性的“人”的意識和思想也會產生變化。繁漪作為一位在社會新舊形態交替中存在的女性,反抗意識和自我覺醒急于在女性權利、性安全、話語權、實踐自由權等方面凸顯出來。
《雷和雨》中的魯侍萍,在那個還未盛行整容的年代里,靠著男人對年輕時自己的多年留戀,幻想出了在繁漪面前應有的驕傲。侍萍說到:“所以我就是那個傳說中永遠年輕的魯侍萍。三十年來他可以為我不開窗不換家具,為我還穿著原來的舊衣服。盡管實在是寂寞難耐,但是這寂寞讓我如此美麗”。因此舞劇中最令觀眾一頭霧水的情節——侍萍孤傲的向繁漪炫耀自己愛情神話,也就得以最好的解釋了。這也正是侍萍以一個鮮活女性的視角來看待自己所產生的藝術表達。再談在舞蹈過程中說話這件事,編導王玫并沒有讓戲份最重的繁漪發聲,而選擇了侍萍大聲的呼喊著由積攢了多年的怨念變為自傲的愛情幻想,表現了女性在受男性話語權操控下長期處于失語狀態下的一種解放。這種解放使得此段舞蹈語言風格與前段現實困境中焦躁、恐懼的身體風格形成了一種非理性的對立。在社會形態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兩性在權利地位上的斗爭從未間斷。最早母系社會時,男人必須討好女人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條件,而在父系社會,女人在抵抗男性霸權的同時,也在極其有限的生存空間中謀取自由,甚至試圖使用性別資本操控男人。可往往徒勞,最終只能借由幻想對女性的自卑情結進行補償。
(二)從文字語言到肢體語言的轉化
在藝術語言上,戲劇和舞劇有極大的區別。從文學劇作到舞臺話劇,其表達依托的文字語言占據著核心。而舞劇則是無聲的語言,僅靠肢體去展現故事。在《雷和雨》繁漪的獨舞舞段中,王玫使用了呼吸、彷徨、奔跑、靜止、跌倒、跳躍等強烈的舞蹈動作,塑造了一個發泄式的人物。用男女之間愛恨情仇的復雜關系對女性的擠壓表現繁漪對愛情的渴望、對自由的向往以及對男權制度的深惡痛絕,這是女性主義思想對王玫創作的影響。她從繁漪的創作視角入手,不僅是一種社會人文反思,也是一種對中國傳統舞劇中以男為主、以男襯女模式的挑戰。在創作時,王玫以繁漪打破藥碗為矛盾主線,將舞蹈人物的動作語言與舞蹈調度中的敘事結構相結合,用“我是繁漪”“我的丈夫周樸園”“我的情人周萍”“我的情敵四鳳”等第一人稱,塑造了她眼中的這個女人。與戲劇《雷雨》截然不同的,正是編導王玫在創作過程中無處不在的女性主義敘述視角的體現。
通過繁漪與周萍的雙人舞可以看出,男女舞者徹底剝去了浪漫的接觸、托舉舞段,用控制與被控制的身體關系赤裸裸的揭示了兩性之間的情愛糾葛。而對于和自己同性的四鳳、侍萍,繁漪在舞蹈中卻不做重點關注。身體的重心和中心全被兩個男性角色所吸住,不停的表現無謂的掙脫和不厭其煩的吸附。從世界女權運動的歷史中可以發現,繁漪身上帶有第一代女權主義者的特征:依舊是在以男人為中心的性別世界中表現出了以自卑為主導的反抗。所以,繁漪女性意識的萌發不是偶然的,先從自身受到吃人禮教的束縛,再到她獲得了周萍精神上的解救,繁漪這種自由意識是微弱的。她一遍一遍追逐著周萍、像依賴的孩子一樣掛在周萍身上想重新獲得愛情;她一次一次轉身回避周樸園,用閃躲的眼神和收縮的手臂在內心抵抗,是女性敢于追求愛情的自覺、追求自由的自覺。
舞劇在以侍萍為主要人物視角的群舞中,王玫主要采用了與整部舞劇中肢體語匯相異的動作,極具誘惑性。扭腰晃胯直白的表現了女性在取悅男性時的身體表現,挖出了侍萍心底女性特征最明顯的一面,使同為女性的繁漪也輕易的被侍萍同化并一起而舞,再加上劇中最年輕的女性四鳳,三個女人在西班牙風格的音樂伴奏下,扭動身體,翩翩起舞,對一種完勝男性的愛情想象竊喜不已。這時的侍萍仿佛是一個領導者,領導著年輕的女性們如何讓男人屈服在自己的性別魅力中。仿佛周樸園、周萍、周沖拜倒在三個女人的萬種風情下,環繞、親吻著她們,奉上所有的殷勤和崇拜,為之傾倒、投降。回到現實社會看來,這不僅僅是魯侍萍、繁漪和四鳳三個女人的幻想,也是存在于所有女性心中的幻想。
從上述分析來看,無論是戲劇還是舞劇,人物的塑造和藝術的語言在其中承擔著敘事的主要任務。舞劇《雷和雨》雖然是無聲的戲劇,但在敘事上仍然具有舞蹈藝術獨特的手法。其創作視角和藝術思維選擇從女性人物出發,在現實層面和藝術的理想層面都有所凝結。與當代許多戲劇作品一樣,《雷和雨》的女性主義視角在現代藝術創作潮流中逐漸嶄露頭角。如果說新時期初始階段的女性戲劇還在爭取和男性同等的“人”的自由獨立與保持“女人”的自然天性之間搖擺和掙扎的話,那么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推進以及社會現代化的逐步實現,女性開始接受自己的社會身份,女性戲劇打破女性“緘默”與“缺席”的歷史,跨越性別的鴻溝勇敢去表達自己。因此,在戲劇與舞劇的敘事上,批判現實、思考人生在同一人物和情節下呈現出了連帶的關系,在藝術語言的使用中,舞劇對戲劇敘事也實現了相互轉化的過程。
三、舞劇與戲劇的創作視角——全異關系
(一)文學母題的分化與重構
無論是戲劇還是舞劇,一個藝術作品的主題往往包含著若干文學母題。從性別的角度來說,人類文化無外乎是由男人的剛性文化和女人的附屬文化構成。美國女性主義者凱特·米里特所著的《性政治》一書中具有這樣的說法:男性控制與支配女性的制度要比種族與階級間的壁壘嚴酷得多,無論目前這些思想表面上是多么沉寂,但實際上卻仍是“我們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識、最根本的權力概念”。在人類生存進化的歷史中,世界曾多次淹沒、遮蔽女性的存在,甚至扭曲她的真實,但是女性用她們的肉體和心靈所塑造出的第二性文化一直在現實世界和藝術世界中掙扎并存活著。現代舞劇《雷和雨》就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化藝術產物,從舞劇的名字中就可以發現編導王玫要說一個什么樣的《雷雨》,題中一個“和”字凝煉了整部作品的主旨——“關系”,不僅表現了女人眼中的男人、女人眼中的女人、更表現了一位女編導眼中的兩性世界。在人類社會中“關系”是互為產生的,王玫把這一點放大并植入到舞臺人物之間,只留下性別標識并褪去年代、住所、衣著等藝術裝飾,只靠一種功與守的調度語匯和類似游戲的模擬形式去舞蹈,而這恰巧就體現了編導在藝術創作時以自身作為一名女性的視角所闡述的性別競爭。
西方現代舞先驅伊莎多拉·鄧肯在創立看似無技術的“自由舞”時,實際上將女性身體從“肉欲的對象”變成藝術的自然,也從女性主義角度推動了現代舞打破束縛的精神追求,掀起了一場舞蹈革命。王玫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專業的現代舞人,真實自然的個性也促使她在創作時展現出先鋒女性的一面,這部舞劇的誕生并沒有打上原作小說的烙印,也沒有遵循傳統舞劇以男女愛情雙人舞為主線的敘事結構,更是她創作自由的證明。舞蹈藝術創作的天窗,幾乎都先從身體這一媒介打開革新的口子,西方現代舞蹈在反叛傳統芭蕾舞蹈之初,就是通過變異、異化的身體語言傳達了舞蹈敘述層面的文化隱喻。王玫作為一名女性編導,在作品《雷和雨》中重構了劇中的角色模式和舞段內容。她放棄交待時代語境、推進情節主線,就人物關系規劃錯綜復雜的“關系鏈”,以女人為主體、以女人看女人的敘述視角突破了文學作品轉化為舞蹈語言的演繹新說。《雷和雨》的編導王玫無疑是后現代女性主義者的代表,在這部舞劇中,我們很難把王玫跟藝術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分開來看。
(二)創作思維的相互獨立
后現代女權主義開始于20世紀70、80年代,她的產生大概和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由于“性解放”和將男女對立起來的女權思想,帶來了無數的家庭破裂,單親母親、問題兒童和艾滋病流行,于是人們反思:社會值不值得為性解放和女權主義付出那么大的代價?另一個因素是,8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女人占據了政府企業學校傳媒的領導地位,當了老板,男人們驚呼:母雞打鳴了,女人也開始懷疑:還會不會生蛋?于是,后現代的女權應運而生。后現代女權主義不再以“女權主義價值”為單一鵠的,而是力圖展現一種作為存在方式和話語方式,既非男性化的,也不是純粹女性化的“第三態”思維。曾有學者這樣評價王玫:“她就是她,一個真實的舞蹈人,出自“學院派”,但她從未被學院派規約,她最大的勇氣就是用藝術的方式直面舞蹈界的病癥和社會的病癥。王玫近些年的藝術追求,就是探索以現代藝術特有的認知世界的方式,去理解和表達中國文化,以及正在進行時態的中國國民的生存狀態,是“現在進行時態”且“在地化”的創作”。在創作舞蹈作品時,編導王玫作為一個女性卻將自己跳出性別的框架來看女人,重視超出女性范圍的性別思考。王玫對繁漪形象塑造的本身就是一個現代女性看舊式女性的藝術視角,是以無性別意識為出發點看待性別差異和競爭的創作視角,是女性的自省表現。她認為,曹禺《雷雨》的不朽在于“戲中很多東西能在現代人心理上找到對應,每一個女人都是由四鳳而繁漪、由繁漪而侍萍,就像許多男人的心理成長都要歷經周沖到周萍,最后是周樸園的多個階段”。這是進入中年階段的王玫對女性情感問題的解讀。這種藝術視角帶有濃厚的兩性文化色彩,也是女性藝術先鋒在創作過程中與自己性別的對話。
王玫創作繁漪角色時使用的是以男人為主體的視角,她大部分舞臺時間是被切割給男人的,被男人消耗,繁漪的悲歡離合也總是在男人身上跳出來。男人眼中的女人都是個性中帶有共性的,所以繁漪與四鳳、侍萍舞蹈動作的相遇總是相斥中帶有淺淺的吸引、背離中帶有淺淺的探索。相比四鳳和侍萍這兩個同性角色,周萍和周樸園這兩個異性角色更容易激發繁漪的情感。單從舞蹈構圖的角度來看,繁漪與四鳳、侍萍的舞蹈都以分離為主。這種舞蹈身體表現還未延伸到自我認知和對同性性別群體的深思中,所以繁漪在舞臺敘述中看四鳳、侍萍的視角是弱視的。而她與周萍和周樸園的舞蹈卻不停重復著分離與接觸,繁漪追尋的是男人,想逃離的也是男人,這說明繁漪生命的重心始終傾向至男性世界。繁漪在性別關系緊密程度上的表現雖然顯示了她敢于接近、反抗男人而追求自我的覺醒,但也奠定了她最為深痛、悲愴的結局。
從創作中王玫看繁漪的視角來談,這不失為是一場女性的自省。王玫很大程度上把《雷雨》的戲劇性弱化了,把性別的差異性強化了。男性世界里或許有這樣一個觀念:婚姻是為了傳宗接代,而女人幻想出來的愛情則是對婚姻的一種玷污。這是曹禺先生在文學原著中想體現的一絲微弱的性別信號。王玫主要通過繁漪的肢體語言在周樸園視線范圍內的逃脫與反抗、在周萍視線里的祈求與強烈、在周沖視線外的無視與閃躲,來表現一個女人對丈夫、不倫的情人、兒子這三位男性存在空間里的豐富情感。在王玫眼中,繁漪依舊是最悲愴的一個,但繁漪也是女性中最具生命力的一個。舞蹈時,演員用外在動作表現心理獨白,四鳳對繁漪的懼怕和厭惡、侍萍對繁漪的不屑與隔離,都體現了王玫在編創中凸顯性別競爭的思維模式:女人總輕易被男人捉住又容易被男人拋棄;女人既容易被女人激怒也容易被女人同化;就在這一追一趕的游戲中,王玫繼繁漪和周萍的第一段吸附雙人舞編排了第二次排斥雙人舞,直截了當地表達了繁漪對男性和真愛的渴望、追逐和糾纏,把女性的自我表達真實化了。
總的來說,這部作品主要采用了以編導王玫自己的女性視角對文學作品進行了二次創作,用現代舞簡潔的身體語言形式拼貼敘事,處理之后,升華了原著的戲劇效果。基于王玫最初的編創主題,舞劇的結尾稍顯冗長和模糊,有點破罐子破摔式的拋出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局:男人女人都在這場暴風雨中傷痕累累,天堂里的明亮和諧之舞表現了理想以自殺式極速回歸至現實,這場悲劇的最終矛頭沒有被指向男人,而被王玫寫成了人性的統一性和同一性。與很多男性主宰的舞劇作品結局相比,王玫只是淡淡的引出了一個有關人類能否走出男性價值觀造成的困境的思考,并沒有明確說出哪一性勝利,筆者認為這或許也是女性編導在藝術創作中都毫無戰勝意識的體現。
四、結語
總體而言,戲劇沖突是強調博弈的,而舞劇則是在包含著博弈的戲劇之外,又與各種文化的色彩進行共構和融匯的藝術。通過分析現代舞劇《雷和雨》的創作視角,可以發現戲劇與舞劇之間的關系也充滿著“戲劇性”色彩。既在敘事空間上有所包含和交匯,又在人物塑造和藝術語言上有所轉化和裁切。最終,戲劇和舞劇的創作又在編劇和舞蹈編導這兩類不同藝術家的個性化藝術思想下相互保持著各自的獨立,這何嘗不是一種帶有戲劇色彩和藝術張力的關系。可見,在這種關系的研究和考察過程中,對于具體作品的分析和題材的比較具有一定的實踐性意義,有助于在藝術理論的整體視閾中對戲劇和舞劇創作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
參考文獻:
[1]吳曉邦.戲劇舞蹈結情誼[J].新文化史料,1994(04).
[2]大衛·勒布雷東著.人類身體史和現代性[M].王圓圓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3]王季思.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4][美]湯尼·白露.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M].沈齊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印大雙.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想評析[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7年.
[6]湯旭梅.舞劇《雷和雨》對《雷雨》的解構與創生[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7(03):107-112.
[7]董英豪,王婧.舞蹈中的女性表述[J].民族論壇,2012(08).
[8]劉曉真.一百年,在舞蹈中爆發的女人們[J].藝術評論,2005(08).
[9]慕羽.一位具有悲憫情懷的現代舞人——王玫[J].文化月刊,2014(01).
[10]張磊.現代性理論視角下的新時期話劇發展與藝術特點研究[D].中國藝術研究院,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