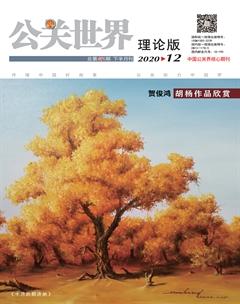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的多模態話語分析
高攀
摘要: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是發布中國重要外交活動信息和與外界溝通交流的重要平臺。本研究選取4月28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中澳洲記者和外交部發言人的問答為語料,運用話語分析和視覺語法,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旨在揭示問答互動的詳細過程。研究發現,話語分析理論和視覺語法適用于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語料,邏輯拆解重組有助于理清雙方觀點,而語速、停頓、重音和節奏則會影響信息傳達的準確度。此外,從視覺角度而言,近景鏡頭的運用、側面平行的取景視角、問答雙方不同時出現在畫面中間的安排,則體現出“客觀”與“平等”的立場。
關鍵詞: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話語分析 視覺語法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是外交部發布中國重要外交活動信息、闡述中國對外政策工作的平臺,同時,它也承擔著國家重要外事活動,是與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然而,它作為特殊的會話語料,也引起了學術界人士的關注:劉瑞文(2016)選取多篇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語料,探究其語類結構潛勢;周霞、王慧芳(2016)運用明示-推理交際理論剖析政治話語,認為外交話語多運用多級二步推理模式,多級角色聽者普遍存在。上述研究多聚焦于外交辭令、語義、口譯教學等層面,鮮少有研究從話語分析視角切入,探討問答互動過程。本文以4月28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為語料,選取澳洲記者和外交部發言人的問答過程進行研究,運用話語分析和視覺語法理論,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旨在揭示問答互動的詳細過程,為外交問答模式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1.問答互動的話語分析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作為特定的會話場合,其問與答遵循一定的秩序,話輪轉換方式相對固定,話輪分配大致均等。按照慣例,記者負責提問,外交部發言人負責回答。因本片段是由后期剪輯而成,集中呈現了澳洲記者與外交部發言人的問答,下面將按照議題的順序開展探討。
每一輪問答都有其整體結構組織,包括開端-提出問題-處理-結尾這四個階段。第一輪問答共有4個話輪,二人遵循一問一答的模式,交替發言,且每個發言人話音剛落,另一個發言人便立刻開口,銜接緊密。首先,《澳大利亞人報》記者提出問題前做了大量的鋪墊,且在問題之后又進行補充性說明。這一做法使得問題的提出顯得深思熟慮,同時也給回答者施加了一定的必須做出回應的壓力。在外交部發言人回應后,該記者調整了發問的方式,轉迂回為直接,顯露其真正目的。反觀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方式,他先是以反問來質疑澳洲記者的問題,接著強調對方駐華記者的身份,歸結問題的根本在于其沒有深入中國民間,了解民意,以至于產生片面的觀點。此外,澳洲記者發言語速較快、少有斷句,而外交部發言人在整個發言過程中則時有停頓,重點突出,從容不迫。
第二輪問答共有6個話輪。澳洲記者與外交部發言人各持有3個話輪。除回應澳洲記者的感謝外,外交部發言人采用反問的策略,質疑澳洲記者的提問根本,指出對方可能因自己不能與妻子團聚而有失偏頗,并表達了對他的美好祝愿。此后,澳洲記者繼續追問,外交部發言人則直指澳洲記者的因果邏輯漏洞,有理有據,措辭嚴謹又不失風度。
第三輪問答共有4個話輪。面對澳洲記者層層鋪墊的提問,外交部發言人并沒有急于回應,沉默長達6秒。接著,他面帶微笑,將問題邏輯鏈一一拆解,指出澳洲記者問題的癥結所在。此后,澳洲記者堅稱澳洲政府的提議十分合理,外交部發言人便提醒該記者注意自己的立場,應客觀全面地看待問題,而不是明顯地偏袒澳洲政府,最后再次禮貌地祝愿澳洲記者能夠早日與妻子團聚。此輪問答,外交部發言人的應對顯得有禮、有利、有節。
第四輪問答共有10個話輪。面對澳洲記者對未經核實的消息進行細節性提問,外交部發言人直截了當地指出消息源未知,沒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接著,澳洲記者補充消息來源,外交部發言人則建議他直接向獲得消息的渠道核實。數次交鋒之后,澳洲記者終于袒露真正目的,他迫使外交部對此消息是否屬實做出回應。外交部發言人則堅持表示,消息源未知,便無法提供任何消息。最后,他以開玩笑的語氣向路透社記者求救,緩解了緊張的態勢。縱觀此輪問答,不論澳洲記者如何旁敲側擊,外交部發言人都堅守論點、機智應變、穩據陣地。
縱觀4月28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全程,澳洲記者多次提問,講話語速較快,信息輸出密集,這固然可解釋為個人說話習慣所致,但也說明該記者準備了很多問題。此外,澳洲記者總在大量鋪墊后進入問題,又在提問之后做細節性的補充,這一做法使問題變得含蓄,且給予回答者一定的外部壓力。而外交部發言人則基本維持恒定語速,停頓、重音得當,節奏適中,可感受到其鎮定自若、應對自如的氣場。二人激烈交鋒之時,面對澳洲記者層層包裹的問題,外交部發言人往往能夠一語中的,使得澳洲記者顯露出提問的真正目的。而針對澳洲記者對一些問題窮追不舍的做法,外交部發言人則堅守觀點,時而玩笑調節氣氛,時而適度反擊應對,使得問答過程精彩連連。
此外,話輪設計是通過遣詞造句得以實現,詞匯的選擇與交際環境和會話參與者緊密相連。一方面,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是相對正式的場合,無論是澳洲記者還是外交部發言人都措辭謹慎、斟字酌句、善用模糊語以避免正面的沖突。另一方面,該場合是面對面的問答,也具有顯著的現場性特征,具體體現在雙方都存在口語化的表達,比如字句的重復或不完整的句子等。
2.視覺語法
20世紀90年代,受韓禮德概念、交互、組篇三大功能的啟發,Kress與Van Leeuwen提出并于2006年完善了視覺語法理論。他們提出了圖像的三大意義——再現意義,互動意義和構成意義。再現意義是指任何符號模態都可用以再現客觀事物及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包括敘事再現和概念再現。敘事再現是指互動參與者與再現參與者通過矢量產生互動,它分為行動過程和反應過程。行動過程中最為突出的參與者可以通過尺寸,位置,顏色等判斷,而當矢量是由目光的延伸實現時,它被稱作反應過程。
互動意義揭示了圖像參與者與觀察者之間的關系,它通過接觸、收、放社會距離、個人態度等來實現。接觸指的是圖像參與者對觀察者實施“提供”行為或“索取”行為。社會距離通過特寫、近、中和遠鏡頭實現,揭示圖像參與者與觀察者的親密程度依次由深到淺。態度體現了取景的視角:正面取景意味著“卷入”;斜側取景意味著“超脫”;仰視取景意味著“尊崇”;平行視角意味著“平等”;俯視取景意味著“憐憫”。
構圖意義是指圖像的再現意義與互動意義是如何整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的,它通過三方面來體現:信息值,顯著性和邊框。左側信息意味著已知或常識信息,右側代表新的或有待探索的信息。上方與下方則分別意味著理想的狀況和現實情境。顯著性可通過多種途徑如位置,大小,顏色等得以實現。
縱觀所選片段,敘事再現被大量應用,大部分鏡頭聚焦于外交部發言人的眼神,矢量多由目光的延伸來實現,故反應過程較多,他時而低頭聆聽問題,時而看向提問者示意。就互動意義而言,不論是澳洲記者還是外交部發言人,都沒有直視鏡頭,因而他們實施了“提供”行為。鏡頭的距離使觀察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上半身甚至表情,此為近景鏡頭,說明觀察者與他們之間的社會距離較近,也展示出圖像參與者與觀察者的親密度。取景角度多為“側面”和“平行”,分別意味著“客觀”和“平等”。針對構圖意義而言,外交部發言人經常出現在畫面中部偏左的位置,代表了已知信息,澳洲記者則出現在畫面偏右的位置,意味著他要提供新的信息。此外,外交部發言人與澳洲記者在畫面中的尺寸與比例相當,則說明了兩者的提問與回答引起了同等的關注。
3.結論
本研究深入探討了4月28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中澳洲記者與外交部發言人的問答過程,運用話語分析理論分析其語言,并運用視覺語法探討其構圖。研究發現:該片段中,針對話語內容而言,面對澳洲記者的連連發問,外交部發言人巧妙拆解其邏輯漏洞,堅守己方觀點,適當運用模糊語言,或調侃或反擊,使得問答過程精彩連連;就講話方式而言,外交部發言人穩定的語速、適當地停頓、適時的重音和適中的節奏彰顯出其鎮定自若、游刃有余的氣場。從視覺層面而言,近景鏡頭的運用體現出觀察者與問答雙方較為親密的距離;外交部發言人或低頭聆聽、或看向提問者示意,顯示了其對問題的重視和對提問記者的尊重;側面平行的取景則體現出“客觀”與“平等”的視角;畫面中間偏右與偏左的位置,則代表了澳洲記者和外交部發言人一問一答的不同立場;且問答雙方都未直視鏡頭,代表他們實施了“提供”行為,使觀察者獲得信息。總而言之,話語分析理論和視覺語法適用于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語料,并為有效地問答提供借鑒意義。但限于篇幅和技術手段,本研究所選語料還不夠充分,研究結果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后續研究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劉瑞文.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的語類結構分析[J].海外英語,2016(09):189-190+194.
[2]周霞,王慧芳.明示-推理交際觀下亞投行例行記者會的話語研究[J].海外英語,2016(22):204-206.
[3]Halliday,.M.A.K..(1973)..Explorations.in.the.Functions.of.Language.[M]..London:.Edward.Arnold.
[4]Kress.G.&.Van.L.T..Reading.Images:.The.Grammar.of.Visual.Design[M]..London:.Rutledge,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