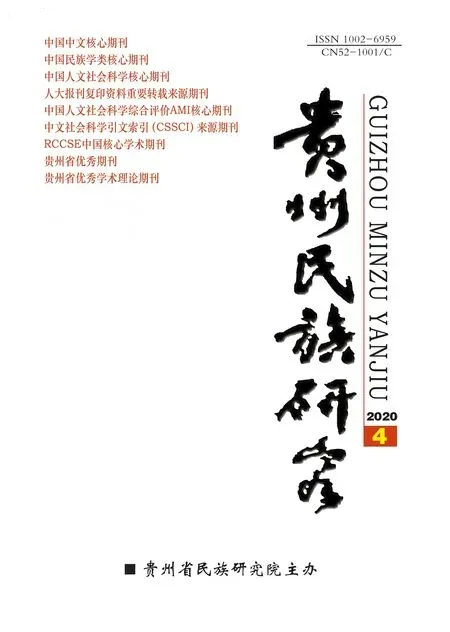少數人權利保護的法理述評
湯振華 秦前紅
(武漢大學 法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權利正當性或權利來源問題一直是現代政治哲學研究中至關重要,但也是最抽象的難題[1]。少數人權利的法理基礎,即探究少數人權利保護正當性的理論基礎。梳理少數人權利保護理論,既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也有利于推動國家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的理論探索。
西方現代政治哲學更為重視個體權利來源問題,對現代集體權利的探討略顯不足。從少數民族權利保護的角度來說,少數民族權利保護是現代民族政治研究的重要課題,甚至可視為現代民族政治的核心議題之一[2]。少數人權利的基礎理論之爭,分為反對派和肯定派。反對派以保守自由主義為代表,肯定派主要是社群主義以及自由主義陣營中的部分流派,如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關于少數人權利保護的論爭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對少數人文化權利不予承認和保護。保守自由主義是這方面的重要代表,代表論者如格萊澤(Glazer)、洛蒂(Rorty)、錢德蘭·庫卡薩斯(Chandran·Kukathas) 等,他們否認少數人群體權利,主張從個人權利角度對公民予以平等保護。第二,社群主義的“差異政治”肯定少數人權利。代表人物為泰勒(Taylor)、沃爾茲(Walzer)、艾利斯·馬瑞恩·楊(Iris·Mrion·Young) 等,他們認為群體的差異化權利值得肯定,主張給予少數人群體權利并提供特殊保護。第三,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認為每個人的文化價值背景都應予尊重,國家建設過程中無可避免地需要對少數群體予以補償。代表人物威爾·金利卡(Will·Kymlicka) 主張對少數人權利進行特殊保護,但將特殊保護限于內部自由的文化群體。金利卡明確指出,少數人權利是特殊權利,這種特殊權利與自由主義所追求的個人自治是一致的。第四,憲法愛國主義倡導對憲法觀念、憲法文化的尊崇。代表人物為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和揚-維納爾·米勒(Jan-Werner·Muller),他們主張淡化族群、血統等因素的考量,宣揚憲法觀念對于公民理念更新的重要性,希望借助于憲法觀念認同來凝聚一國公民。
一、自由主義與少數人權利保護
古典自由主義學說至今具有重要影響。在最初,自由主義主要指向經濟領域,崇尚思想自由,強調以法律限制政府權力,保障自由貿易。現代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是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其在《論自由》 中標志性地提出了個人自由的重要價值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界限,即個人自由是第一位的,只要不涉及、不損害他人利益,個人的自由就應該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護,不得受到任何干涉和限制[3]。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產生了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發展。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思潮,則是20世紀30年代至今的各種新自由主義流派和學說的總稱[4]。
古典自由主義學說將自由放在第一位,而自由來源于個體,所以自由主義的本原是以個體自由、個體權利的捍衛為旨歸,認為沒有個體自由,社會就失去了創新發展的動力,任何社會制度的構建和完善都應滿足個體自由的發展,由此倡導尊重和保護生命、自由和財產。但自由主義的弊病也在于此,正如馬克思在對費爾巴哈哲學進行批判時所指出的:“每一個力圖取得統治的階級……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說成是普遍的利益。”[5]換言之,自由主義者無視現實存在的個體差異、群體不平等、階級不平等、貧富差距等問題,簡單地將平等、自由推銷給全社會,使得社會成員“自以為是在為整個人類的自由而斗爭”[6]。古典自由主義在根源上與功利主義理論有直接關聯,自由主義者過度推崇或夸大個人自由帶來的“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導致人淪為實現幸福的工具——至少是部分人成為實現多數人幸福的手段,從而人自身的尊嚴和幸福不能得到重視和滿足,少數人權利也被忽視。
19 世紀中后期,隨著以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為核心的立憲體制在歐洲主要國家先后確立,以及自由資本主義弊病的日益凸顯,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已經難以化解和闡釋社會公正問題。對于個人自由至上而言,其必須具備一個前提,即個人被賦予公平的條件。由此,新自由主義的出現標志著實質性權利正義的正式形成。其中,羅爾斯關于正義的理論學說將少數人權利保護問題推向了歷史前臺。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黑人運動、女權運動等風起云涌,少數族裔的公平保護日益受到重視,羅爾斯提出對由于出身和天賦不平等而處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補償,他希望在個人主義理論框架內進行解決[7]。如果說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仍然堅守自由的話,德沃金的理論就在平等價值上繼續深入和拓展。在德沃金的理論中,平等具有最高價值,或者說平等優先于自由。在他看來,造成人們不平等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不同的社會文化條件,一個是個人的自然稟賦,二者均是不可選擇的。對此,政府應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以糾正這種“不可選擇”[8]。
二、社群主義的少數人權利保護學說
“有人說,20世紀70年代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是新自由主義者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80 年代政治哲學的主要話題則是社群主義者的社群(Community) ……社群主義無論在方法論上還是在規范理論上都與自由主義形成了明顯的對照。”[9]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提出了批評。
邁克·桑德爾(Michael·J·Sandel) 主要對自由主義的自我觀念提出批評。他指出,自由主義者認為自我是一種混沌無知的自我,是沒有差異、同質化的存在,這顯然是脫離實際情況的。現實中,任何自我都必然受到各種歸屬的制約。更重要的是,我們所處的各種歸屬的制約是無法選擇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理性選擇對此幾乎無能為力。麥金太爾(Alasdair·MacIntyre) 認為,所有道德或政治原則和觀念都有其歷史,即便是正義,也有歷史傳統。脫離或拋開歷史,單純談論正義的普適性并不科學。沃爾澤(Michael·Walser) 認為,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正義原則,同時,任何個人都歸屬于一定的社群,這種“成員資格”表明了多元主義是現實存在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Taylor) 批評了自由主義“原子化”的個人觀,并將諾齊克視為原子主義的典型代表。在他看來,原子主義將個人權利置于社會利益的前面,將個人視為自我滿足的存在,可以獨立于社會之外。顯然,這是不符合現實的。
總之,極端的自由主義無視或無法辨識到社群利益的重要性,過度推崇個體利益,將個人權利的獲取視為當然,卻將個人對社會的義務視為有條件。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的過度推崇,導致部分群體利益在客觀上被漠視,如社會權利結構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人。其中,族裔少數群體在其中尤需保護。社群主義的論述在理論起點上看到了自由主義可能產生的極端傾向,并結合現實強調了族裔少數群體在權利結構中的不利地位。
在社群主義中,查爾斯·泰勒提出了“承認政治”理論,這一學說以嚴密的邏輯對平等理論作出新的闡釋。在泰勒看來,人對國家、社會、民族等的認同來源于承認,而承認的發生來自于他者。顯而易見,泰勒是從發生學角度探尋,他發現人類經歷了等級社會中的扭曲的承認、不平等承認、近代民主社會的平等承認,雖然近代民主社會更為進步,但平等承認只是在形式上注重平等,卻忽視了不同情況下人們所處的不同境遇,尤其是對于美國黑人等長期遭受不公對待的弱勢群體而言,他們長期置身于形式化的平等制度框架內,事實上并沒有享有真正的平等和承認。對于多民族國家而言,不同種族、民族、文化背景的弱勢群體更應該受到差異化的承認,這種承認源自對差異性文化的尊重和包容[10]。泰勒雖然倡導承認政治理論,認為少數群體的差異應予尊重和保護,但他也對加拿大魁北克問題提出了一定質疑。在他看來,處理少數人權利的最佳選擇是既尊重差異,也不過度放大這種不能夠普適的差異對待,他更傾向于通過對話和斗爭來實現承認政治。
三、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是當代西方比較興盛的一種理論學說,主張尊重和肯定少數群體的文化價值,贊同族群身份平等和權利保護。該理論認為,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差異性的文化既是少數群體的自由選擇,也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財富與資源。國家應該將少數群體視為獨特的文化群體,通過合適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妥善安放少數人權利,實現少數群體與其他族群的和諧共處、多元共生。
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具有一定的理論獨立地位,但整體而言,該理論仍然歸屬于自由主義者陣營。應該看到,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是自由主義內部的論戰,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固然存在,但二者在很多問題上存在著普遍共識,而且兩種理論范式在相互交鋒中不斷完善自身理論,使得兩大理論陣營越來越完備。從理論陣營上劃分,加拿大學者威爾·金利卡在少數人權利保護領域有著卓越而重要的影響力,他很大程度上屬于自由主義者,更加傾向于自由主義陣營。自由主義認為文化價值背景不屬于個人領域的問題,而金利卡認為,文化價值背景與個人自由是可以并存的:文化價值背景是個人權利和自由選擇的范疇,應該予以尊重和肯認。同時,他看到了在國家建設過程中,難免要優先考慮或傾向于某種文化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少數群體的文化價值保存和發展。為了彌補這種國家建設層面不可避免的選擇造成的不公,國家就應該尊重和包容少數群體的文化價值選擇。由此可見,金利卡致力于調和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對此,他認為:一方面,要允許個人對不同文化的選擇,任何公權力不得干涉和否定這種選擇,這是自由主義立場的體現,亦即外部保護;另一方面,要提防群體內部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的侵犯,這同樣是自由主義立場的體現,亦即內部限制[11]。
四、憲法愛國主義
少數人權利保護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議題,與兩次世界大戰緊密相關。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民族主義在德國納粹的鼓吹下,演變成為民粹式、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帶有強烈的侵略意味。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德國整個民族陷入反思,開始思考人類慘劇為何發生、憲法制度為何被摒棄以及少數群體的權利何以被踐踏。對此,施密特(Carl.Schmitt) 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誰來保衛憲法?誰來保衛‘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立憲民主國家?”[12]憲法愛國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這也表明,理論學說的臻于完備正是現實社會內在催生的結果。
“憲法愛國主義”可以追溯到自由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政治參與行為,但最早對其作出詳細闡釋的是他的學生——德國海德堡政治學家斯登貝格(Dolf·Sternberger)。在斯登貝格看來,所有的愛國主義都是憲法愛國主義,其意義是對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熱愛[13]。他倡導全體公民尊崇憲法的制度和價值,而不是過度倚重語言、血緣、文化等因素,換言之,一個法治國家的公民應該更加崇尚憲法制度和法治精神[14]。于他而言,憲法愛國主義目標在于維護立憲政治,保護憲政自由,而在其所依托的力量上則借助非民主因素,借助公民對國家的忠誠——在這里,國家是憲法愛國主義的核心。
在哈貝馬斯那里,憲法愛國主義得到了新的詮釋,核心關注不再是國家而是憲法。一方面,哈貝馬斯對斯登貝格的學說進行超越,他不再強調國家的重要性——或許這在于他看到了國家在德國的危險性,畢竟“二戰”期間國家、政府的權威過度膨脹,極權主義、沙文主義才得以發生,某種意義上講,哈貝馬斯必然要與強調“絕對命令”的國家主義立場的康德分道揚鑣。哈貝馬斯更重視憲法,無論是憲法制度,還是憲法觀念、憲法精神、憲法程序,都是哈氏所關注的。另一方面,哈貝馬斯對憲法的關注和肯認,最終目標是超越傳統的民族國家觀念,淡化對血緣、地域、民族、種族、語言文字、習慣等的認同,將公民認同——公民對國家憲法的認同以及公民在憲法中的公民身份的認同作為首要目標。綜合而言,哈貝馬斯致力于服從“自1989年以來一直滾滾向前的民主政治進程”[15],期待將德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公民國家。
揚-維納爾·米勒對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理論進行了進一步擴充和闡釋,但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米勒看來,憲法愛國主義的對象不是具體的憲法規范,而是憲法觀念,所謂“憲法觀念”,即“個體彼此視為自由且平等的,并尋找共同生活的公平條件”[16]。在米勒的理論中,憲法觀念依托于憲法規范而又超然于憲法本身,具有規范性、崇高性和一致性,有助于社會成員形成普遍的、一致的認同,這種認同比認同憲法規范更加深刻、牢固。
總的來說,與斯登貝格相比,哈貝馬斯和米勒的思想更加符合當代民族國家建設的發展方向,而不是訴諸于傳統的古典共和理論。但這并不意味著哈貝馬斯和米勒的理論不關注國家。有學者指出,憲法愛國主義并不像米勒認為的那樣,僅是對抽象憲法觀念的認同——“這是自由主義立場出發下的偏見”,憲法愛國主義應是國民主義(公民身份)、國族主義(多元文化與族群關系) 和國家主義(主權空間) 的結合[17]。從根本上說,憲法愛國主義始終不會脫離國家,也不可能憑借單純的憲法文化和憲法理念來凝聚國內不同族群,公民的憲法觀念事實上是服務于對所在國家的忠誠,服務于建構自由、平等、公正的國家,亦即服務國家建構。
在憲法愛國主義的理論框架下,首要的是增進公民對本國憲法理念的認同,在此基礎上形成凝聚力。因此,憲法愛國主義更加關注的是公民身份認同、對憲法文化的認同,而淡化處理族群身份。事實上,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來看,其從頭至尾幾乎沒有關于少數民族的規定,就充分體現了德國立憲更多地關注公民身份,以公民的權利、義務、自由、平等來承載落實憲法治理。這就意味著少數群體只能通過公民身份與憲法規范來尋求權利實現的權威依據,憲法愛國主義在德國這樣的同質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受到推崇,但能否在多民族國家發揮重要作用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和探討。
五、我國少數民族權利保護的理論敘事
在我國實行民族平等政策(包括民族識別政策) 的過程中,理論界有著比較獨特的敘事方式,即將階級分析與歷史分析結合起來,批判王朝社會與中華民國時期的民族壓迫政策,進而在歷史比較中顯示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政策的進步性。我國對少數民族權利的保護,在法理上主要是基于少數民族整體在發展上的不利地位,需要予以差別化的對待和“補償”,民族平等理論是核心和基礎。1950年6月26日,周恩來就漢族與少數民族關系指出,“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在民族地區貿易上,“由于過去對不起人家,今后就應該多補貼、多支出一些,讓少數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18]。李維漢也在不同場合指出,“民族問題的根本解決,有待于改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狀態。”[19]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兩種主義(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 的反對,還是在改革開放以來倡導的民族團結互助,都始終圍繞和離不開的是民族平等理論。
隨著時代變化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少數民族權利保護單純依托民族平等理論已經遠遠不夠,需要整合汲取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憲法愛國主義等理論的觀點和理念,對少數民族權利保護作出更加充分的論證和解說。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社群主義的論證,它們都承認個體歸屬于某個群體,而特定群體的文化本身是有價值的。憲法愛國主義力求在憲法框架內實現不同社會成員、不同文化背景的整合,既要以憲法保障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又要通過憲法來尊重和承認公民可能具備的多元文化身份。
對于我國而言,團結、統一、發展始終是新時代開展和做好民族工作的總要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工作的主線。“中華民族”在2018年正式寫入憲法文本,以憲法規范、憲法精神、憲法觀念培育國家公民觀念和法治觀念,促使全國各族人民形成命運緊密相聯的命運共同體。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多元文化在統一國家框架內發展,要逐漸優化調整民族政策和相關制度建設,促使各族群眾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同步實現,讓更多少數民族群眾在憲法實施過程中有更大的獲得感,要不斷提高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全社會培養形成法治思維和尊崇憲法理念,這已然成為時代賦予我們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