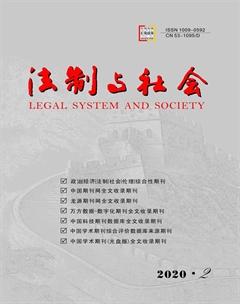探討刑法中社會危害性概念之界定
陶禹霖
摘要 我國刑法中關于社會危害性概念,需要經過相應的標準原則的限定,使其具體化以及明確化。作為刑法有關的概念,需要擺脫國家哲學的約束,保持相應的規范性。社會危害性屬于以憲法以及法律對行為做出的負價值評價。客觀主義視角下的刑法立場,價值評價的目標原則方面主要為行為對他人產生的直接危害結果。基于此,本文對刑法中社會危害性概念之界定做出分析探討,以此為有關人員提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 刑法 社會危害性 概念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006
位于我國刑法學界,有關社會危害性,存在彼此對立的兩方面觀點。對于刑法學界,社會危害性屬于犯罪的根源本質;與之對立的觀點則認為,社會危害性屬于犯罪的根源本質,不可將范圍同危害社會行為進行劃分與區別。致使此種局面產生的關鍵主要為對立方均存在自言自語的行為,并未充分認識了解到社會危害性是能夠基于多為視角做出界定以及分析的概念。
一、關于社會危害性概念的爭論
我國刑法學界,關于社會危害性的解釋存在各不相同的看法,涵蓋事實說、屬性說與法益說的重要學說。事實說以及屬性說,主要是說明社會危害性具體范圍相關的問題,即社會危害性屬于對行為造成的危害的客觀事實還是行為存在的本質屬性,并未解釋刑法層面社會危害性基于何為具體內容。法益說則對社會危害性解釋成刑法所保護的利益,基于刑法層面對其做出相應的規范界定,將利益當作相應的實體內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以及進步性。不過,正如部分學生做出的批評,法益說嘗試位于社會危害性的概念之中,完成將社會危害性存在的一般以及犯罪情況做出有效區分的任務,以此使刑法學能夠將社會危害性概念的具體使用權做出全部壟斷,這也是不切實際的。同時,法益并非刑法學領域存在的專屬概念,位于其他法律領域同樣對法益概念有所使用。關于社會危害性具體范疇問題方面,馮亞東教授曾提出有關社會危害性的具體論斷,即社會危害性屬于對行為的價值評價的具體范疇,自在的東西并不關乎善惡,不存在價值評價則不會存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則不存在犯罪。價值、事實屬于哲學領域的重要概念,位于刑法理論存在長時間的交錯糾纏,這也同傳統文化以及人們思維方式息息相關。位于刑法領域,提及相應的具體犯罪行為,人們便會清醒意識到對社會造成相應的危害;提及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形象思維勢必會同犯罪之間產生聯想。如此,事實判斷以及價值判斷彼此相容,事實即體現出相應的價值,價值同樣展示出真實的事實。我們的理論則穿插于價值以及事實彼此之間,致使理論存在抽象性以及模糊性特點。
二、社會危害性的概念界定
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主要為憲法與法律對行為做出的負價值評價,此價值評價的目標原則上主要為行為對他人產生的直接危害結果。此外,基于《刑法》第13條但書具體規定,“嚴重”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屬于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這也成為社會危害性概念量的具體規定。基于此,社會危害性概念存在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社會危害性存在于價值評價的基本范疇。犯罪主要為人的行為,行為若是客觀,則并不關乎善惡,行為唯有通過特定主體做出的價值評價方可歸為犯罪范疇。因此,關于社會危害性,其存在于價值判斷的基本范疇,并非行為導致的客觀危害或是行為具備的屬性。
第二,行為是否存在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基礎評價基于法,并非各類社會標準規范。社會危害性屬于一般性概念,并非刑法層面的專屬概念,位于不同法律領域存在的社會危害性或許是以文化、倫理道德等對行為做出相應的價值評價,而刑法層面社會危害性評價,需對法外因素產生的影響以及干擾予以完全排除。刑罰是針對個人權利形成的最為嚴重的具體干涉,非規范因素存在相應的模糊性以及主觀性,以非規范性因素當作刑法層面水危害性評價的關鍵基礎,會使國家權利對于個人權利造成相應的侵犯。盡管通過刑罰對部分行為做出具體懲罰,或許對某種社會倫理規范產生相應的鞏固或是促進,不過切不可以社會倫理規范當作刑法層面社會危害性評價的根本基礎,刑法層面社會危害性屬于規范標準的概念,需基于法當作評價基礎。
對于社會危害性,其是存在于立法的概念,立法者基于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量度評價,選擇何種行為需納入刑法做出規制,同時設置相應的刑罰。立法過程中,對于社會危害性評價,其法律基礎主要為憲法。憲法屬于法制國家的重要基本法,成為制定部門法的關鍵,刑事立法同樣需基于憲法的標準規定與法制精神,對行為是否屬于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做出具體評價。即符合憲法的標準規定與法制精神的行為,并不存在社會危害性,無需做出犯罪處罰。司法層面,對行為社會危害性做出具體評價,其規范標準主要為刑法,若行為充分符合刑法分則構成要件,即表示行為存在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且情形基本上相似一致。
第三,社會危害性基于對他人產生的直接危害結果當做基礎評價標準。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關注重點為負價值評價的目標存在怎樣的問題,通過各不相同的評價目標為主要基準,會致使在相應刑法問題中呈現出各不相同的最終結論。本文基于自由主義刑法理念,強調對個人的刑法保護,因此通過相應的標準原則,對社會危害性概念做出界定,避免國家權利對個人自由產生相應的侵犯。所以,社會危害性評價標準原則僅局限在行為對他人產生的直接危害結果。可分解為如下:首先,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對他們產生的直接危害。這也表示,不以不具備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原則上不可當作犯罪進行處罰,前文已有論述。其次,社會危害性評價,需基于評價行為產生的危害結果當作標準原則,對行為與行為的反倫理性評價,則需視作例外。危害結果涵蓋實害以及危險,物質性危以及精神性危害結果。刑法層面危害結果基于實際、物質危害結果當作評價目標。所以,刑法切不可僅以行為違背倫理或是行為人存在主觀惡性當作基礎,以此運用刑罰。此外,精神性危害,無法做出精準把握,交易導致刑罰權出現擴張問題,刑法需重點基于物質性危害結果當作具體標準原則,對未遂犯、侵害精神利益與危險犯等犯罪,則屬于刑法層面存在相應的例外。
第四,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務必是量達到嚴重程度方可定義為社會危害性。《刑法》第13條但書做出明確具體規定,被認為是對量的具體標準規定。我國《刑法》第13條但書與分則個罪定量因素的具體標準規定,基于總體為入罪設定相應具體量的標準,所以我國刑法理論較為健全完善。如此,我國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兼具質、量的具體內容,僅僅存在危害不過并沒有達到刑法標準規定的具體范圍情況下,行為并不具備刑法層面的社會危害性,所以不將其當作犯罪。
三、結論
綜上所述,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范圍與內容并非沒有邊界,是通過刑法做出具體規定,存在相對的確定性。基于刑法,對社會危害性概念做出相應的界定,對刑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時,對社會危害性的具體量度,要求立法者對刑法做出相對明確的標準規定,更加要求學者以及司法人員根據個案情況做出全面綜合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