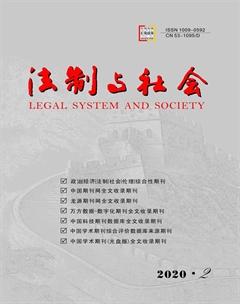論訴訟解決行政爭議的局限及改進
摘要 我國行政訴訟法將解決行政爭議作為立法宗旨之一,對行政審判實質性化解行政糾紛提供了依據。但是,法院對涉訴行政行為合法性評價具有事后性的特點,達致“案結事了”困難重重。“紀元案”作為典型案例,為揭示行政審判原告實際利益得不到有效救濟的局限提供了實證切入點,提出解決問題的設想,可為司法理論和實務提供參考。
關鍵詞 紀元案 行政審判 行政爭議 局限改進
基金項目:本文為江蘇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與創新計劃校級項目結項,項目內容為論訴訟解決行政爭議的局限及改進;主持人:李佳潤,項目編號:2018YXJ093。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045
一、問題緣起
2016年8月,江蘇省徐州市事業單位招聘工作人員考試中,紀元在通過了報名資格審查并且筆試、面試第一,體檢、考察合格的情況下,在擬聘人員名單公示前卻被口頭告知專業不符招聘條件拒絕錄用。紀元于2016年8月9日聘請律師向法院起訴,據2018年2月23日法院判決書顯示,確認“被告徐州市人社局在2016年上半年徐州市事業單位招聘中取消原告紀元聘用資格行為違法;駁回原告紀元的其他訴訟請求”。紀元上訴,后以“糾紛已解決”提出撤訴申請經法院裁定準許。此案在行政審判中彰顯“解決行政爭議”的立法宗旨,有效救濟原告實質性權益方面有研究價值。
二、行政訴訟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的局限
行政爭議也稱行政糾紛,從法理來看,定分止爭是訴訟法的天然功能,失去此功能,訴訟就會陷入“程序空轉”的局限,就會出現監督依法行政,卻無力保護原告正當訴訟請求,司法權威弱化社會效果不佳的被動局面。“紀元案”,反映出行政訴訟解決行政爭議存在以下局限:
(一)確認違法判決的制度設計,弱化了行政審判對行政機關的監督權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1條圍繞宗旨的制度設計存在問題,特別是“確認違法判決”存在選擇性適用的漏洞,“紀元案”可見一斑。“紀元案”一審判決,法院適用了《行政訴訟法>第69條和第74條第一款第一項作為主要判決依據,避開了第70條“明顯不當的”合理性審查,但由于此案按一般正常人的理解違法性及不當性明顯,法院最終確認了被告取消原告紀元聘用資格行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第74條確認違法的判決,在學理上屬于情況判決,此類判決本身就是法益平衡的產物,只有在判定行政行為違法,參酌可能導致國家利益以及公共利益遭受損失的可能時,才能援用此條之第一項,本案是否可能導致國家利益及公共利益受損值得商榷,但確認行政機關行政行為違法,以行政機關敗訴結案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紓解民怨的作用。
(二)原告勝訴但實質性訴求未支持,存在訴訟利益的救濟空白
“對于行政相對人而言,行政訴訟則是一種行政法律救濟制度,是一種以追求公正為主要價值目標的行政相對人權利救濟機制,是行政法治化的產物。行政訴訟作為一種事后救濟機制,在沒有建立憲法訴訟的國家是公民合法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保障線”。原告勝訴但實質訴求未保障,是法院應下大力氣解決的突破點。
第一,從“紀元案”一審判決書來看,原告拿到的是一份勝訴判決。但是原告訴請判令被告重新作出恢復聘用資格的行政行為被法院駁回,這才是原告啟動訴訟的主要意圖,是原告實現成為事業單位人員進而實現勞動就業權的主張。勞動就業權是原告的憲法性權利,此種權利受到侵害求助司法機關,按照“有權利必有救濟”的法則,法律的天平向弱者傾斜的普世法律價值規則,法院應予以判決支持才符合情、理、法和諧統一的法治思維。
第二,實質性訴求其實就是解決行政爭議,而行政爭議沒有被實質性解決是此類判決的關鍵所在。我國行政審判在一審程序中未能成功化解行政爭議的情況比較嚴重,據2018年度上海市行政審判白皮書披露,2018年上海“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審、二審行政案件9262件,其中一審5466件,二審3796件”,上訴率較高。
第三,由于原告勝訴實質性訴求未救濟,實際上法院只是保障了原告的訴訟權利,而實體權益的損害依然處在延續狀態。原告花錢請律師,耗盡心力打官司,維護自身私益是根本,維護公益是附隨性追求。但是,判決結果往往本末倒置,像“紀元案”多名涉案領導被問責,行政機關得到了警示,推動了地方的依法行政,公益效果顯著,但主要私益訴求未實現。
(三)審判人員的利益平衡心態,致原告實質性利益難維護
舊的行政訴訟法設計了既保護原告合法權益,又維護和監督被告依法行使職權的制度,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強調“監督與維護,是行政訴訟功能兩個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片面強調一面忽視另一面,都會使行政審判工作偏離正確的軌道。”在此法治路徑指引下,行政審判的法官們會形成利益平衡心態。雖然現行行政訴訟法已經將“維護”去掉了,但行政機關的“面子”以及敗訴了影響行政執法權威的心理作怪,行政機關的威權對行政審判的干擾依然存在。
(四)行政訴訟單一模式難以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
我國采用行政復議及行政訴訟為主的行政爭議解決體制,但是目前情況是“復議機關已然變成‘維持會”雖然這并非《行政復議法》立法的初衷。現行行政訴訟法也設計了復議機關維持決定后的“雙被告”的制度,但考慮到行政復議自體監督的天然缺陷,及不服行政復議還要走行政訴訟的冗長程序,行政相對人為盡快維護自身利益,除復議前置案件外,多數寧愿直接選擇行政訴訟程序。
(五)審理效率低,增加原告訟累,影響爭議實質性解決
行政審判的獨立性是解決行政爭議公正性的保障,但現實情況是“司法審判的行政化是司法地方保護的幫手”,法院行政審判的獨立性受到一定干擾,雖然相關機關出臺了干預司法“三個規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審判組織為了解決行政爭議煞費苦心,組織雙方協調,做原告、被告的工作,工作之辛苦令人佩服。不過像“紀元案”2016年8月16日一審立案受理,2018年2月23日審結,后紀元不服上訴,2018年8月28日二審裁定準予撤訴終結,前后耗時兩年。應聘崗位早已鳩占鳳巢,影響了爭議的實質性解決效果和社會效果。
三、行政訴訟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的改進設想
“從本質上講,行政訴訟是一種解決行政爭議的制度”。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從受理、審判、執行的許多制度設計都圍繞著解決行政爭議展開,“法律不只是與行政審判的內容有關而且與法律在行政審判中被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適用有關。法律并非由固定的基本原則所確定,而是由目的性和自由選擇確定的”秉持此種思路,對行政訴訟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做如下改進設想。
(一)起訴階段通過立案法官釋明,銜接行政復議解決
《行政復議法> 2017年修改,初任行政復議工作人員要求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行政復議工作人員法律專業水準已有所提升,但普通群眾并不知曉,建議最高法和司法部聯合制訂規范,立案法官行使釋明權,像鄉政府作出的土地房屋征收決定、公安機關違法罰沒款物之類明顯違法的案件,由法官向相對人釋明后,聯系行政復議機構接收復議申請,快速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節約司法資源。
(二)推行“行政爭議多元調處中心”的模式
行政爭議多元解決機制是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的較好選擇,上海的“行政爭議多元調處中心”模式值得借鑒。“上海高院聘請的調處委員中,不僅有行政復議機關人員,還有退休司法工作者,律師、專家學者等。”塑造了依法裁判與協調化解的新模式。現在全國各地諸多人民法院在復制上海“行政爭議多元調處中心”的做法,建議最高院出臺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的專項司法解釋,以使此項改革與法有據。
(三)借鑒域外行政爭議實質性解決經驗
1.日本行政訴訟前的相關制度。日本有行政訴訟前傾聽民怨,助力百姓溝通涉事機關的制度,該制度被稱為“苦情處理”。“由民間的有識之士中委任行政商談委員,該委員受理居民的具體苦情商談,并向商談人出主意或將有關情況通報給相關機關”,這樣就形成了百姓、中立專業民間組織、行政機關之間的良性互動鏈。另外,提起行政訴訟前相對人還可以選擇“行政不服申請”途徑。該制度是“受罰人先向作出該處罰的行政廳或其上級行政廳提出不滿,促使其撤銷該處罰的制度。”這種讓行政機關自我糾錯化解行政爭議的做法,發揮了行政自我監督的作用,減少了相對人訟累和法院的負擔。
2.英國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改革經驗是獨立于行政機關。“讓行政爭議解決機關完全司法化,列于司法體系之下。”用獨立性確保公正性,贏得公眾信賴。
3.法國、美國在行政系統內設置行政爭議解決機關。雖然在行政系統內設置行政爭議解決機關,但是用司法制度和程序約束,規制其獨立辦案,公正裁決爭議。
4.議會監察專員救濟行政爭議相對人權益。瑞典、丹麥等國家的議會監察專員,接受相對人投訴,監察不當行政行為和不良行政,救濟行政爭議相對人的人權及利益。
(四)立法上修正“訴訟不停止執行”規則,實現法律的公正價值
“訴訟不停止執行”規則的設計初衷之一是行政效率,從法律價值的位階分析,除非為了個案平衡,行政效率應讓位于行政正義,即行政爭議的實質性解決,給原告一個公正的訴請回應。因為“任何解決糾紛的制度,其核心要求都是公正,公正是司法或準司法行為的靈魂”建議立法機關修法放寬法院行政審判中向涉訴行政機關就其行政決定暫停執行權,只要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且會給原告權益造成不可挽回損失的情況,就可以發出中止執行的裁定,增加行政爭議實質性解決的條件。
(五)強化行政審判人員的專業及倫理素養,用好人民陪審員
行政法律關系交織著復雜的社會關系,行政權的不斷膨脹催生了法律規范的不斷出臺,加之行政法理論多為舶來品,這就要求行政審判人員下苦功提高專業和倫理素養。同時,用好具有專業特長人民陪審員的智慧,提升行政審判解決行政爭議的效率。
四、結論
“紀元案”為我們研究行政爭議實質性解決難題,提供了生動的研究素材。實質性解決行政爭議需要行政審判的公正性、獨立性、專業性和協調性,特別是涉案行政機關、相關機關及原告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