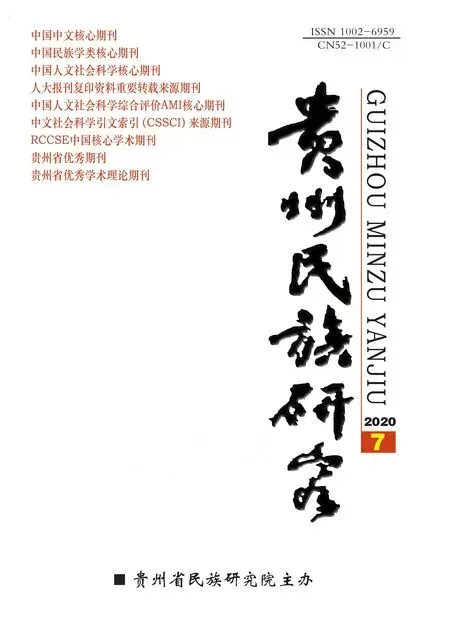近40年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變遷研究
周 芳 胡興東
(1. 云南大學 職業與繼續教育學院,云南·昆明650091;2. 云南大學 法學院,云南·昆明650091)
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的主要內容和特征
(一) 20世紀80年代
云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基層社會中制定村規民約至少始于1981年。1981年9月15日,昆明市吳井生產大隊制定了《昆明市官渡區吳井大隊鄉規民約》,該民約共有9條,由當時吳井生產大隊管理委員會和治保委員會聯合制定。此后,云南很多少數民族開始根據自己村寨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制定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傳統性、時代性的村規民約。20世紀80年代,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大量制定各種類型的村規民約,對當時少數民族村寨社區治理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文山州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村規民約已經成為民間社會的重要規范。“到1986年已經有85%以上的鄉村制定并實施了鄉規民約”[1]。這個比例是十分高的,體現了村規民約在當地少數民族社會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處在這一時期的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其村規民約最大的特點是民間自發制定。20世紀80年代是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第一波村規民約制定高潮。
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復興的主要原因是自1980年開始,云南省開始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各類財產的“私有性”越來越明顯,為自己“所有財產”維權行為越來越多,于是社會糾紛數量隨之增加,而當時國家層面不管是立法數量還是國家糾紛解決機制體系都無法適應這種需要。于是,少數民族村寨為了讓各自村寨內的各種財產保護、社會生活管理有序,紛紛根據自身存在的問題和需要,制定村規民約,建立起土地、森林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此外,在家庭承包責任制下沒有辦法對各戶村民的日常生活像在集體生產隊時代那樣進行直接有效的管控,導致各類違法犯罪行為大量出現,村民對村寨內的社會秩序需要有新的維持機制,于是只好從村寨自身秩序的需要出發制定村規民約。
上世紀80年代,云南少數民族村寨的村規民約最大特點是集中反映各民族村寨的風俗習慣,體現出各民族村寨習慣的特點。這個時期的村規民約由于具有很強的地方性、傳統性、民族性、文化性等特點,導致多與當時黨和國家的政策、憲法、法律相抵觸。其中,最突出的是很多村規民約在處罰條款上,不僅數量多而且處罰重。“有的鄉規民約各種罰款項目多達二十多種,罰款一般都超過行為人所侵犯財產的幾倍乃至幾十倍”;“如亂搞男女關系的要罰殺豬祭寨門、洗寨子,請大伙吃拼東”[1]。此時期云南少數民族中的村規民約一般是按他們村寨或社區中公認的風俗習慣制定,解決當時突出的社會問題。
(二) 20世紀90年代
20 世紀90年代,特別是1993年后新的法治理念成為國家治理的主流,云南少數民族中村規民約的傳統性、地方性、民族性等很多內容越來越與現代法治國家,特別是“國家主義”下的法治理念沖突。這個時期,學術界和各級政府開始對村規民約中的很多反映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內容進行大量批判,甚至通過各種形式對其進行審查和否決。20世紀90年代村規民約在法治建設和法治原則下,為了保證其在形式和內容上與國家法一致,越來越受到國家法的影響。在形式上,行政村一級的村規民約基本上采用國家立法格式來進行,具體分為序言、正文和附則;正文分為章、節、條、款、項等。在內容上,表現出對一些傳統習慣進行禁止;在處罰上與國家治安處罰相符合,多數在50-200元之間;在內容上強化村民的權利;在具體事項上,多把相關國家法作為規約來源。
20 世紀90年代,政府為了加強對農村村規民約的管控,最直接的辦法是制定村規民約樣本,讓各個村寨在制定村規民約時以樣本為準,或作為參考。當然,這種做法的后果是大量村規民約內容高度同質化,失去了村規民約以地方性、民族性為內容的特點,失去了村規民約的自治性和回應性。但是從國家角度看,這種辦法獲得了國家對村規民約在內容上的管控,實現了對村民行為的管理。這個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村規民約在內容上,政府會通過各種形式要求村規民約反映和體現國家的政策、法律等。如1999年潞西三臺山政府與勐丹村公所簽訂《三臺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責任書》中,明確要求各合作社通過制定“村規民約”“社規民約”來實現自己對當地村寨治安的管理目標。這樣制定的村規民約成為基層政府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目標責任落實”的量化考核指標[2]。
20 世紀90年代,隨著學術界對村規民約中處罰條款的大力批判,特別在200元以上罰款受到國家法限制后,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村規民約在處罰條款上開始發生明顯變化:一是處罰數額開始減少,多數在200元以下;二是不再稱為罰款,而是用“違約金”,理由是村規民約是村民之間的“契約”,違反村規民約屬于“違約”行為,罰款是一種“違約金”。同時,這個時期少數民族的村規民約在反映當地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上有所減弱,或者更加隱蔽。
在此階段中,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很多時候是回應當時社會中的突出問題。如1997年《通海縣納古回族鄉鄉規民約》在內容上就體現了當地民族習慣和社會問題。在第二條中規定“加強民族團結”,“在社會交往中,做到互諒互讓,互助互愛,一旦發生矛盾,依靠各級組織解決,嚴禁‘私’了,禁止鳴炮聚眾,尋釁滋事,違者罰款1000元-3000元,造成嚴重后果的,依法處理”;第3條中規定發生交通事故及矛盾后在解決上“依靠有關部門解決,嚴禁‘私了’。車輛亂停亂放罰款50元-100元;強拉硬要,欺哄嚇詐及‘私了’的,罰款500元-2000元”。這些內容反映了當地回族社區在糾紛解決上的特點。此外,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中各種不良社會風氣大量涌現,其中有賭博、吸販毒、電子游戲等三個問題較為突出。為此在村規民約第五條中規定“嚴禁賭博”、第六條禁止開電子游戲室、第七條“嚴禁吸毒販毒”[3](P357)。這些內容反映出當地回族的社會習慣和突出社會問題,通過村規民約對這些問題做出了回應。
(三) 2001-2010年
2001-2010 年間,云南省很多少數民族地區的村規民約都存在較為嚴重的格式化問題。其中以行政村一級最為典型,很多行政村為了與上面保持一致,往往把上面頒發的樣本進行簡單改動或讓村民開會通過后公布。如《云龍縣諾鄧鎮天池村村民委員會村規民約》、2000年《騰沖縣界頭鄉永樂村村規民約》、2006年《騰沖縣中和鄉石坪村村規民約》、2007年《騰沖縣猴橋鎮上街村村規民約》、2007年《騰沖縣馬站鄉興華村村規民約》等,認真分析這些村規民約的主要內容都是一致的,很少反映當地民族、社會中突出的社會問題。
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由于自身社會特殊性決定了村規民約不可能完全受制于國家制定的范本。于是,很多少數民族在保留國家規定的政策性、法律性、宣傳性用語時大量制定體現自己特色和需要的村規民約。如2000年《瑞麗市姐勒鄉喊沙寨村規民約》雖然在形式上大量適用政府制定的標準格式,但很多內容卻是傳統習慣。如第二條社會治安中第三項規定“年輕人在外惹事生非,無理取鬧,經兩次教育不聽者,第3次由村小組罰款500-1000 元,并要寫保證書,如不服收回責任田”。第三條規定外來人“上門落戶”時需要有本村寨的介紹人和擔保人,同時交納一定費用;第三項規定“來本村寨落戶者要遵守本寨的村規民約和當地民族習慣,違者可隨時取消本人戶口”。這里的“本人戶口”是指傳統村寨認同的“村籍”習慣,而非政府戶籍管理中派出所上的“戶籍”。第九條在盜竊行為上,第一項規定“如盜竊10元以上物品兩個以上的,由村民小組收回盜竊者責任田一畝”;第二項規定“如盜竊者沒有田地也拿不出罰金,由村民小組全村成員把他趕出寨子,永遠不許回寨”。這里對偷盜行為采用處罰收回承包責任田方式,從國家法上看是“不合法”的,但在當地村寨傳統下,這種處罰是得到全村認可的。這種規定體現了當地傣族在土地制度、村寨成員認同和管理方面的傳統習慣。從此可以看出,當地傣族仍然保留有村寨共有制習慣,在村寨成員管理上,“開除村籍”仍然是最有效的處罰方式等。這部村規民約是這個時期最能體現云南少數民族村寨為解決本村寨中突出問題而制定村規民約的典型代表。
這個時期在云南少數的民族村規民約中,常常把國家推行的重要政策寫入,其中最典型的是計劃生育和義務教育政策。2000年后,云南很多少數民族對義務教育越來越重視,村規民約中有越來越多的內容涉及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從村規民約規定看,主要是針對義務教育實施,對教師和學生的保護,對上高中及大學等高級別學生給予支持和鼓勵。2008年《軍賽民族鄉岔路村民委員會岔路組村規民約》中第八條規定“經過教育仍拒絕送適齡兒童入學,拖孩子后腿,不供女孩子讀書,拉孩子回家勞動的家條,依照有關政策規定,不得享受任何優惠待遇”。當然,在自然村寨層面上的村規民約與行政村上的村規民約在內容上表現出明顯的不同,很多自然村寨在制定村規民約時往往是解決當地社會的重要社會問題。如2002年《西疇縣駱家塘村村民委員會上壩尾村村民小組生態恢復與環境管理規定》是由于當地自然環境石漠化嚴重,生態脆弱,所以當地村民為了保護生態環境,制定了詳盡的森林保護公約。2002年元陽縣哈尼族制定的《元陽縣新街鎮箐口村規民約》中第十條規定“不允許在白龍泉、長壽泉洗衣物、沐浴,違反者每次罰款5元”[3](P258)。這里就對水源進行了保護。
(四) 2011-2019年
2011 年后,國家對村規民約越來越重視,特別是2012年后,國家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開始大力推行重構自治體系的努力,讓村規民約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從全國來看,各地在2014年興起了制定村規民約的再一次高潮。從調查看,2014年后,云南省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開始全面制定村規民約,其定位也較為復雜。對這種復雜定位可以從臨滄市滄源縣《永和社區村規民約》中第一條看出,對村民基本行為的約束,在不與國家法律法規相違背的前提下,它既要體現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又要立足于本村的實際情況,促進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這種復雜多樣的要求是這個時期村規民約的基本特征。此外,這個時期村規民約的復雜還反映在國家對農村治理中很多政策出現變化。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建人居環境、計劃生育松動、土地林地權益允許流轉、義務教育加強、傳統家族的族規族訓重新承認、移風易俗改革運行的推行等。這些都為少數民族地區恢復和保持民族傳統習慣提供了條件。同時,這個時期一個重要變化是國家希望把各種政策、政治目標轉化到村規民約中。于是,讓村規民約承擔了太多國家政策、政治目標。如清潔衛生開展、社會風俗改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甚至是脫貧攻堅、義務教育、產業發展等。大量的國家政治、政策的賦予,讓村規民約逐漸成為國家各種政策、法律的大雜燴。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村規民約的篇章和條文都越來越多。2011年后,在村規民約制定中,為了讓村規民約與國家政策、法律統一,有些地方開始對村規民約進行審查和考核,或者制定樣本,讓所在地區各村、居委會參用,即加強對村規民約合法性審查。2019 年開始,村規民約由于受到2018年民政部7部聯合發布文件的影響,在內容上文件中規定的內容成為主體,有些地區甚至把文件中的規定作為整個村規民約的基本內容,再一次讓村規民約走向形式化。
二、近40年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變遷思考
(一) 云南少數民族村規民約變遷深受時代話語的影響
(1) 在形式上。20世紀80年代后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在形式上越來越受到國家法律結構的影響。很多村規民約在結構上是一部村民制定的綜合性“法典”。村規民約在結構上通常分為“總則”“分則”“附則”三部分,分則由“章”“條”“款”“項”等構成。如1992年曲靖市《富源縣古敢水族鄉補掌村公所村規民約》,在結構上由序言、第一章生產和生活、第二章森林、第三章環境衛生、第四章民事糾紛、第五章治安管理、第五章公共秩序、第七章計劃生育和婚姻、第八章妨礙公務構成。從整部村規民約看,從整體結構到章都受國家立法形式的影響。
(2) 在用語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云南少數民族村規民約在用語上深受時代影響。分析這些年的云南少數民族村規民約用語,主要體現出政治化、標語化、時代化三種特征。如1991年瀾滄縣拉祜族制定的《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糯福鄉南段村公所公民條例》最能體現云南少數民族在村規民約上是如何在用語上受到時代影響。此條例“序言”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規定了人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必須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主義秩序。”第一條規定“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每個干部、社員的頭腦”,第三條開頭是“要確立精神文明政治標準”,但具體是規定結婚要按國家規定法定年齡,反對早婚及通奸現象和處罰。整個村規民約都盡量用了當時流行的政治用語來表達當地社會問題,讓整部村規民約在“合法性”上顯得十分充分。這種特點現如今仍然存在,不少村規民約中包含著“遵紀守法”“基層治理”“助力脫貧”等用語,體現了是當下的政治事件和時代性。
(3) 在內容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云南少數民族村規民約在內容上基本特點是國家法律、政策和當地社會問題三塊內容決定了村規民約的內容。如1981年制定的《昆明市官渡區吳井大隊鄉規民約》中第七條規定“嚴禁亂設舞會,如發現私設舞會沒收錄音機,對參加舞會者進行教育處理”。這一內容是20世紀80年代剛改革開放時,人們興起跳舞高潮,但從當時主流政治看,此種行為屬于“資產階級”性的“腐朽文化生活”,所以要禁止。再如,1982年4月28日制定的昆明市《崇明縣羅良大隊鄉規民約》中第一條規定“土地(包括自留山、園地、宅基地)、山場屬于公有,個人不得買賣、出租或轉借。違者,除收回土地,沒收所有錢物外,罰款20-50元”。這里對承包土地轉讓嚴格禁止,體現了那個時代存在很強的集體所有制傳統。這些內容很多是黨和國家在基層治理中的政策。
(二) 國家政治行為深刻影響村規民約的內容
村規民約深受政治目標和政策的影響是20世紀80 年代以來整個中國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特點。20 世紀80年代,中國基層社會治中的村規民約還具有很大的自發性,很多村規民約是以解決各自村寨中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為中心。如20世紀80 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2014年提出的鄉村振興、精準脫貧戰略等。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國家對村規民約的重視和管理,村規民約內容越來越受到國家政治目標、政策影響,很多村規民約變成國家政治目標、政策在基層社會中的再確認。在制定村規民約時關注“如何辦好紅白喜事”“如何保護好生態”“如何處理好鄰里關系”等問題,并把公共環境衛生、公共基礎設施設備、移風易俗作為重點內容,擴大了村規民約的調整范圍,從居住環境到鄉村文化建設,從村民事務公開到黨員教育活動,從家庭小我到社會大我[4]。這些都讓村規民約成為國家各種政策的“大拼盤”載體。當前,為了能夠有效地實施村規民約,很多地方紛紛制定了“恥辱”處罰。為了保證實施,還采用“紅名單”“黑名單”的管理形式,為了紅十條的列入紅名單,為了黑十條的列入黑名單。最終形成村內具體恥辱處罰性質的“紅戶”和“黑戶”管理機制。這種公開使用“恥辱”性質的處罰,雖然存在著與國家法律精神相沖突,但在秩序管理獲得為目標下被廣泛承認和推廣,讓當前的村規民約在內容上出現時代性的變化。
(三) 村規民約中的自治性體現復雜的變遷
云南少數民族的村規民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自治性上就存在復雜變化,不能簡單地說是自治性線性變弱,也不是線性增強。分析過去40年間在制定村規民約中的“自治性”變遷歷程。20 世紀80年代,村規民約的存在與運行更多是一種自發性,是各少數民族回應國家在基層社會治理上,從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強制控制轉向以個體家庭自由生產的家庭聯產責任制后出現的基層社會治理上,國家力量消減后出現的治理空缺而出現的產物。當時的村規民約體現很濃的地方性、民族性和傳統性特點,所以20世紀80年代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中自治性較強。20世紀90年代,在國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后,國家的現代法治建設開始全面開展。隨著國家法律的完善和現代法治理念的形成,對村規民約中很多內容開始進行國家法視角下的審視,大量村規民約的具體內容與國家法律、法治理念沖突明顯,于是國家開始通過制定范本或審查否定村規民約中“不合法”的內容方式進行干預,進而導致村規民約的自治性出現減弱。這種現象持續到2010年后,隨著國家對農村治理的改革,特別是農村出現空心化、村內治理失缺等問題,村規民約重新被國家確定為農村治理重要的機制,于是村規民約中的自治性開始得到重新加強。
(四) 區域和民族習慣在云南少數民族村規民約中存在差異
20 世紀80年代后,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村規民約雖然越來越同質化,但仍然有不少村規民約的內容反映當地民族、地區的習慣。如《師宗縣馬廠村公所鄉規民約》中第一條:“為美化村莊環境,翠云山屬風景林禁區,照過去規定不變,如有違反者照樣殺豬封山。大牲畜進入禁區除放映一場電影外,每頭一次罰10元,小牲畜進入禁區打死不負賠償責任,禁區內不準堆糞、堆柴草,違者每堆一次罰10元。”[3](P438)這里沒有明確記載制定的時間,但從處罰放電影看,應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之間。這里雖然沒有用傳統用語,即保護“神林”而是用“風景林禁區”,但在處罰上采用殺豬祭神,卻是傳統習慣。此村規民約從內容看是對當地傳統神林保護習慣的承認。20世紀90 年代,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由于旅游開發,為了吸收游客,有些村寨會在村規民約中對傳統習慣公開承認和保護。如1999年曲靖市羅平縣《魯布革蘋鄉多依村村規民約》的第三章“社會治安及村風民俗管理”中第九條“村風民俗”規定對本村布依族傳統節日保護,如“祭老人房、祭神山、祭龍潭以及三月三等就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節日,我們應保持并遵守”。考察云南少數民族村規民約40 年的發展和實施情況,會發現很多時候,村規民約是否有效,關鍵在于是否采用當地民族認為是“合傳統的處罰方式”,否則僅僅按國家法處罰卻很難達到效果。
三、當前村規民約的定位:一種鄉村社區社會治理的回應之路
村規民約作為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特別規范,應以回應每個村寨或社區中當前社會的突出問題為目標,而不是成為實現村寨或社區中國家治理目標上的各種政策和法律的工具,所以村規民約在內容上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當地社區的主要社會問題和風俗習慣,否則會降低村規民約的有效性。前兩年在網上成為“網紅”的《云南省開遠市紅石巖村委會村規民約》,根據報道該村規民約雖然只有十二條,但由于制定的內容與村民生活息息相關并用方言表達,所以效果較好。如遵守法律法規方面規定“國家法律法規要認得,見著壞人壞事要敢說”[5]。
從報道和實地調查看,村規民約中那些實施到位,效果較好的村規民約是那些針對當地突出社會問題,需要集體或全村村民集體解決,通過村民自發制定的村規民約。這類村規民約往往是內容較少,針對性強,強制力明確。如2000年文山州廣南縣制定的《舊莫鄉昔板村委會先干村規民約》規定:“墳地各村只能在各村地域內隨意選用,原來葬墳地按原界線保留,不能以祖墳為借口,逾界啟用。凡1961年四固定后,逾界埋墳的要清理,限制搬遷,屬干部或私人受賄擅自同意,清理退還賄款后同樣搬遷,以免后患,如逾期不遷,墳地權屬本村,可幫挖出置于地面后轉告搬走。”[3](P545)這條村規民約是因為當地墳山爭議太多,為解決墳山糾紛而制定。這些內容的寫入讓村規民約具有較好的社會回應性,成為村規民約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