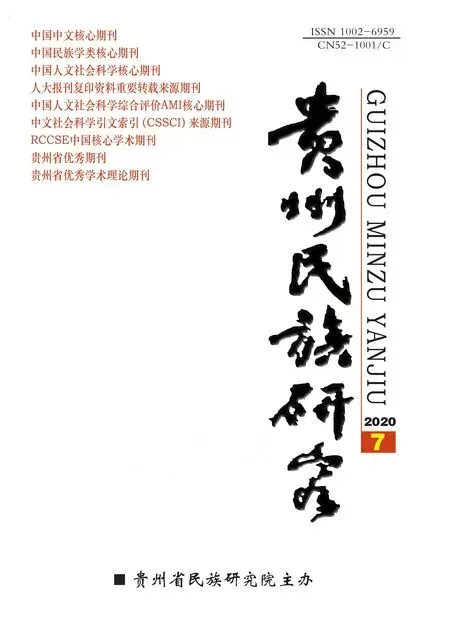民族八省區的文旅融合發展
——以歷史文化名城的“傳統—現代”轉型為例
2020-08-29 03:22:46張繼焦
貴州民族研究
2020年7期
張繼焦 吳 玥
(1.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100081;2. 中國社會科學大學[研究生院] 民族學系,北京100081)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幾年,文旅融合成為熱點問題,但學者多是研究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狀況,且以個體研究為主,很少有人探討中西部民族地區的文旅融合整體發展。對此,筆者意識到,文旅融合是一件復雜而艱巨的任務,要想真正實現文化和旅游相互賦能,須對各地文旅融合的實際發展狀況進行全面系統的討論。中西部民族地區擁有東部沿海地區所沒有的自然景觀、人文資源和獨特的民族文化,本文以民族八省區的歷史文化名城為例,探討中西部地區在“傳統—現代”轉型中如何實現文旅融合發展。
二、本文分析框架
歷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文化遺產資源,民族地區富含獨特的民族旅游資源,這是民族八省區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的基礎所在。在當前的城市化進程中,歷史文化名城本身是一幅金字招牌,是深化文化根脈與發揚旅游城市品牌的重要推動力,但也需要實現當代轉型。關于文化遺產與歷史文化名城的“傳統—現代”轉型,有的學者主張對其進行“生產性保護”[1]“原真性保護”[2],合理利用文化遺產,重現歷史文化名城的原本模樣;還有些學者主張對文化遺產進行活態利用,開發文化創意產品與旅游業。但這兩種看法或注重傳統原真性繼承,或關注現代轉型發展,沒有將文化遺產的“傳統—現代”轉型置于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3]中整體看待,仍處于傳統的二元對立分析框架之內。……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英語文摘(2022年4期)2022-06-05 07:45:12
童話世界(2018年13期)2018-05-10 10:29:31
今古傳奇·故事版(2016年24期)2017-02-07 04:29:04
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 07:13:06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4期)2015-05-14 07:25:32
數學大王·低年級(2014年7期)2014-08-11 16:36:44
海外英語(2013年8期)2013-11-22 09:16:04
南風窗(2004年15期)2004-04-29 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