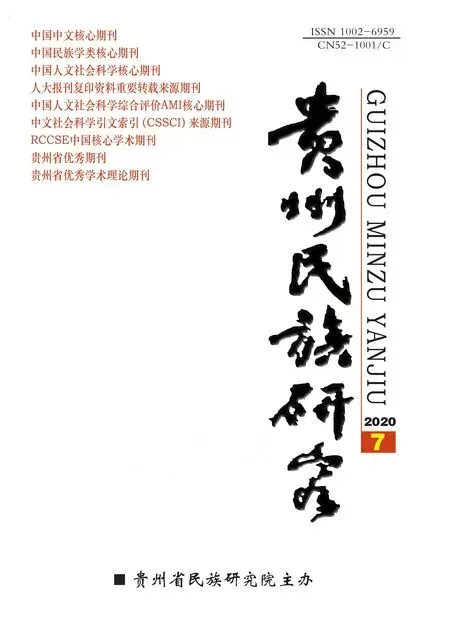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漢民族史記》 的人類學視野
丁蘇安
(廣西民族大學 管理學院,廣西·南寧 530006)
《漢民族史記》的橫空出世,為泱泱漢民族樹立了一塊523萬字的歷史豐碑。主編徐杰舜先生,以50年的學術積累,20余年的團隊研究,5年的奮筆撰寫,把中國的漢民族研究推上了一個學術高峰。
《漢民族史記》的學術內涵極為豐富,黃振南教授撰寫了《〈漢民族史記〉成色說》 (《南寧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 一文已有論及,但筆者拜讀之時,卻被這套鴻章巨字中無處不在的人類學視野而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絕,歷史還可以這樣書寫!大有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一、人類學結構論視野:創立板塊結構模式
人類學的結構論試圖從雜亂無章的現象中尋找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結構,其最終目標是從結構認識事物的本質。
自近代以來,西學東漸,顛覆了中國二十四史傳統的述史方式,形成了以歷代王朝的框架為坐標的結構模式。但是,凡事都有個度,如果機械地把民族史塞進王朝的框架里,會把一部部好端端的民族史弄得支離破碎,不成體系。更有甚者干脆視漢族史為中國史,中國史就是漢族史。由于認識的混亂,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們對中國史的研究十分熱衷而趨之若鶩,而對漢民族史的研究長期冷淡且視而不見,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漢民族的歷史研究長期處于空白的狀態。對此,徐先生早在大學求學時就看在眼中,急在心里,暗下決心要為漢民族樹碑立傳。1999年,《文匯讀書周報》曾發表新華社著名文化記者孟凡夏的文章:《為漢民族樹碑立傳的人——訪徐杰舜教授》,表露了徐先生的這個心聲。
在徐先生50余年的治學生涯中,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對漢民族史書寫結構的探討和嘗試。讀過徐先生的成名作《漢民族發展史》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的人都清楚,當年,徐先生打破歷代王朝框架為坐標的模式,在探索按民族發展規律書寫民族史的初期,嘗試建構了起源—形成—發展—特征—文化的板塊結構模式,首次打破了王朝框架為坐標的結構模式,獲得了良好的學術反響。尤其是他關于漢民族起源、形成和發展的研究,很快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認同,2008年4月被斯坦福大學邀請在“漢民族研究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了主旨講演;2012年《漢民族發展史》 被馮天瑜先生收入《中國專門史文庫》,同時,也獲得了社會的積極認同,2016年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漢族”條,就采用了徐先生在《漢民族發展史》中所表達的觀點。
徐先生并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汪國真的成名詩《熱愛生命》曾說:“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從1992 年到2019年的27年間,徐先生“風雨兼程”,先后率領學術團隊完成了漢民族研究的三級跳,即《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五卷本《漢族風俗史》 (學林出版社,2004年) 和九卷本《漢民族史記》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的三級跳。正是這三級跳的最后一跳,積50年之學術功力,一跳而登上了漢民族史研究的巔峰。
結構論是人類學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重要工具。在《漢民族發展史》的基礎上,徐先生的《漢民族史記》又以歷史、族群、文化、風俗和海外移民的板塊結構,建構了漢民族的恢弘歷史。正如他在《漢民族史記·卷首語》中所說:“傳統結構模式沒有歷代王朝框架的束縛,眾所周知,《史記》所開創的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的專題結構,就具有開放性的特點,從而使歷史的編撰靈活機動,收放自如,不僅可使歷史生動起來,更可使歷史的敘述深刻起來了。所以我于1989 年在《中國民族史新編》的《自序》中就提出:‘中國民族史的編寫必須突破歷史王朝的框架,按民族自身發展的規律去編寫。’[1](P4)為此,我們這次編撰《漢民族史記》,正是按照民族自身發展的規律,繼承漢民族的史學傳統,運用傳統結構模式,將漢民族史的呈現分為發展史、族群史、文化史、風俗史和海外移民史五個專題。”[2](P5)
徐先生的這個做法,獲得了馮天瑜先生的贊譽,他在《社會科學報》 上撰文說:“徐君的《漢民族史記》追跡《史記》的結構方式,突破王朝述史的框架,按漢民族經歷的豐富性、多樣性部勒篇什,在比較舒展的框架內放手編寫,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悠久、文化繁富的一個大民族樹了碑、立了傳,實屬難能可貴。”[3]
可見,正是人類學的結構論打開了徐先生的“腦洞”,成就了《漢民族史記》的輝煌。
二、人類學整體論視野:書寫述史的新文本
表述問題是人類學的起點和核心。如何書寫歷史?也就是說如何建構和呈現漢民族的歷史?二三十年來,徐先生動足了腦筋。他認識到整體論是人類學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論和重要工具,是“把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4]。
那么,如何書寫漢民族史?徐先生在《漢民族史記·歷史卷》(上)中,從整體論出發,以漢民族的五帝時代、起源時代、形成時代、發展時代的邏輯結構,書寫了漢民族述史的新文本,向世界呈現了漢民族上下5000多年的歷史長卷。
更有意義的是,徐先生并非就漢民族研究漢民族,而是把漢民族置入中華民族的整體視野之中,使人們從他的敘述中,不僅可以清晰地認識漢民族浩浩漫漫5000多年的歷史路線圖,還可以清楚地明白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為什么是漢民族的歷史原因。所以,徐先生在本卷的結尾,自然而然地把浩瀚的漢民族史匯入了中華民族的主流之中,他說:“對于古老的漢民族發展來說,如果說兩漢是其幼年時期,隋唐是其青年時期,明清是其中年時期,近代則是其老年時期。這是民族發展規律之使然,從清王朝前期即開始的滿漢融合,滿族漢化,歷經267年(1644—1911年)最終并沒有徹底完成,其根本原因是世界變了,時代變了,一個長期封閉自守的中國開始融入國際社會,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應用,民族意識的覺醒和高漲,從此改變了中國民族交融的大方向,中華民族這個雪球,開始在中國滾動。漢民族將與中國所有其他的民族一道,凝聚和交融在中華民族之中!”[2](P446)《漢民族史記·歷史卷》 (上)的述史方式,構成了一個從漢民族的五帝時代到起源時代,繼而到形成時代,再到發展時代的獨具特色、自成系統的述史新文本。
三、人類學區域論視野:建構漢民族區域史的體系
區域作為人類學解讀人類文化的方式,是人類學的重點研究范疇之一。周大鳴曾說:“民族志是人類學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區域研究則是以民族志為基礎的一種提升,或者說是對民族志的超越。”[5]早在20世紀末,徐先生就開始關注漢民族區域的研究。從1996年12月開始,歷時3年,其成果《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在人類學泰斗費孝通先生“要重視和加強對漢民族的人類學研究”題詞的鼓勵下,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從此,一個漢民族研究的“雪球”滾向世界,其所提出漢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論”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同。20年后的今天,在研究和撰寫《漢民族史記·歷史卷》(下)之時,徐先生在《總后記》 中說:“從歷史演進的實際出發,以區域為邊界,分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和西南七個區域,分別展示了漢民族在這些區域形成和發展的生動態勢和精彩過程,正是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時期所形成的族群互動、磨合、整合和融合,才形成了漢民族歷史發展的豐富多彩。這一幅又一幅的地域歷史畫卷,可使人們從縱深上認識和了解漢民族的歷史及其多元性和多樣性。”[6](P577-578)從而構成了漢民族區域史的體系。這就應了田阡所言:“中國人類學的區域研究要在國際學術前沿研究的基礎上,借鑒發生學的方法,以現實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探討特定歷史形態和地理形態中文化發生的根源與基礎、發生的過程與規律、發展的環境和走向,就……需要一些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引領能力的分析單位和框架。”[7]這對人口眾多、地域廣大、生態差異的漢民族史的表述是完全必要而不可缺少的。
所以,《漢民族史記·歷史卷》(下)對漢民族區域史體系的建構,生動而真實地呈現了漢民族在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同時,又存在一體多元的在線狀態,充分展現了漢民族來源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樣性、歷史的多彩性。趙巧艷在評論黃土文明研究時曾說:“對中國人類學乃至世界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顯著方法論貢獻就是區域人類學研究范式的確立和在黃土文明研究中的具體應用。”[8]那么,徐先生對漢民族區域史體系的建構也是“區域人類學研究范式的典型應用”[8]。
四、人類學族群論視野:對漢民族的族群結構進行分析
族群(Ethnic group) 論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人類學民族學界研究人類共同體的重大發展,90年代通過喬健和陳志明兩位先生的引介傳入中國學術界。徐先生作為早期的踐行者,不僅于1999年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中引入了族群論,并“發現族群問題有一個很重要的人文現象,即族群是有結構的,尤其是對歷史悠久、人次的研究時,其族群結構的特征就凸顯無遺”[9](P1)。于是,他初步分析了漢民族的族群結構,還于2002年在《民族研究》上發表了《論族群與民族》一文,按中國話語的邏輯,將族群概念概括為“族群是對某些社會文化要素認同,而自覺為我的一種社會實體”。在此,他特別指出族群可能是一個民族,也可能不是一個民族,而民族不僅可以稱為族群,還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10]。此文一出,族群概念的使用為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開辟了一片新天地。
正因為有了這樣深厚的學術背景,所以,近20 年來,徐先生為了研究漢民族的族群結構,以行萬里路的精神和毅力,除西藏外,走遍了中國大陸及臺港澳各地,感生態環境,考民情風俗,查方言俗語,搜資料文獻,以語言、族群形成和人文特征的敘述結構,在《漢民族史記·族群卷》(上)(下)兩卷中,以100余萬字的篇幅,考察和研究了東北的沈陽人、大連人、長春人、哈爾濱人;華北的河北人、山東人、山西人、北京人、天津人;華中的河南人、湖北人、湖南入、江西人;華南的廣府人、客家人、閩南福佬人、平話人;桂柳人、高山漢、疍民;華東的上海人、南京人、徐州人、蘇州人、鎮江人、徽州人、安慶人、杭州人、寧波人、紹興人、溫州人;西北的關中人、陜北人、寧夏人、天水人、河西人、河湟人;西南的四川人、云南人、貴州人、屯堡人等41個漢族族群。其中有大的族群,如山東人、山西人、上海人、北京人等;也有小的族群,如高山漢、疍民、屯堡人等。但無論大小,均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
在徐先生的筆下,漢民族的族群個個活色生香,生動有趣,如俠義忠誠又戀家戀鄉的河北人,好漢、好客和好禮的山東人,樸實厚道、勤儉耐勞、外向內斂的山西人,京味、善侃、傲慢的北京人,草根、混搭、樂呵的天津人,敢為天下先、崇商重利、嗜食生猛海鮮、講迷信重意頭的廣府人,重商賈善經營、以家族為核心、漂洋過海闖世界的閩南福佬人,聚居城鎮、隨遇而安、詼諧樂天、“死仔”義氣的桂柳人,以舟為居,萍蹤無定,民間信仰,龐雜多樣的疍民,古道熱腸、懷舊情結、平民意識的南京人,敢做敢為、有情有義、南北交融的徐州人,柔情似水、氣質高雅、心靈手巧的蘇州人,聚族而居、興師重教、左商右儒的徽州人,天堂情結、悠閑安逸、文質彬彬的杭州人,求心求實、師爺風范、水鄉風韻的紹興人,冷娃性格、刀客文化的關中人,尚武出將、南北相融、重教重男天水人,盆地意識與天府心態、“格老子”與擺龍門陣、“粉子”與“耙耳朵”并存的四川人,壩子情懷,知足常樂,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的貴州人,儀式社會、軍人氣質、以孝為先、明朝遺風的屯堡人。凡此等等,舉不勝舉。面對這些鮮活而多樣的漢民族族群和族群文化,人們又不能不驚嘆所有這些族群無不對漢民族保持著高度的認同,使人們“在體驗漢民族‘一體多元’的多彩在線和多元結構之中,深感漢民族的‘多元一體’與‘一體多元’,真是世上最巧妙而又精當的民族結構和民族認同。一方面是歷史悠久而結構復雜,另一方面則是文化多姿而高度認同。這樣,在漢民族的生命‘馬拉松’中,孕育、凝聚、磨合、整合和融合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6](P579)
重要的是徐先生對漢民族進行人類學的族群分析,按不同的類型,對其族群結構做了解剖和分類,其成果的學術價值,就像X光機的透視作用一樣,不僅可以從結構的深層次上認識民族的整體性,還可以從結構的可變性上把握民族過程。這無論是對認識漢民族滾雪球從多元走向一體,還是以此為示范,認識中華民族也會滾雪球從多元走向一體,都是極具參考意義的。所以,《漢民族史記·族群卷》應該是一個有價值的嘗試,不啻是一個學術創新。
五、人類學文化論視野:對漢民族的文化演進作解讀
文化是人類學研究的核心內容,而在人類學的視野里,文化就是人和人的一切行為方式的表達。所以“一個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呈現是其重要的表征”[6](P579)。漢民族雖有極豐富的文化樣態和極深厚的文化傳統,但十分遺憾的是學術界有多種版本的“中國文化史”,也有一些“中華文化史”,甚至許多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史,偏偏沒有一部“漢民族文化史”。其中之原因當然如前所述是人們在中國與漢民族之間畫了等號所致,在此無須多言。
重要的問題是漢民族的文化如何呈現,漢民族的文化史走的又是什么路線圖?據我所知,徐先生從1992年《漢民族發展史》出版以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對此,他有三點反思:
一是回顧了1992年《漢民族發展史》中對漢民族文化的呈現。 《漢民族發展史》 從琴、棋、書、畫;吃、穿、住、用;民族禮儀;民族節日;民族戲曲;民族武術;民族醫藥;民族工藝;漢民族文化的象征——泰山、長城、大運河9個方面,橫向地描繪了漢民族的文化圖像。但這種圖像呈現缺乏歷史的縱深感。
二是反思了1999年《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中對漢民族文化的表達。其從多元的視角,將漢民族文化的呈現分為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和西南七大區,分別呈現了各區漢民族的歷史、族群和文化。這種多元態勢的表達,雖然展示了漢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結構和態勢,但僅就漢民族的文化史而言,不僅缺乏整體性的觀照,仍然缺乏歷史的縱深感。
三是考察了近二十年來國內漢民族文化研究的動態,區域文化研究方興未艾,嶺南文化、閩臺文化、云貴文化、川渝文化、中原文化、燕趙文化、東北文化、齊魯文化、江浙文化、贛徽文化、湘湖文化、甘青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三晉文化等研究蜂起。在這種漢民族區域文化的熱流中,我們曾設計將漢民族的文化史以區域文化的形式來呈現。但仔細一想,這仍然克服不了以往的研究缺乏歷史的縱深感的缺陷[6](P580)。
經過反復斟酌,徐先生在《文化視野:漢民族文化史分期綱要》一文中提出了漢民族文化史分期的五項原則:要注意中國歷史對漢民族文化史的觀照,要注意漢民族文化史與中國文化史的區別,要注意漢民族文化史在中國文化史中的位置,要注意漢民族本身起源、形成和發展的規律與漢民族文化史的關系,要注意把握漢民族文化本身發展變化的生命規律[11]。最后決定從縱的方向上呈現漢民族文化及文化史,看來,這是一個很明智的決策。這個決策,使徐先生的《漢民族史記·文化卷》一下子突破了中國學術界各種文化史的包圍圈,從而創立了“漢民族文化史”新的表達形式。
在徐先生《漢民族史記·文化卷》 (上)(下) 兩卷,也以100余萬字的篇幅,考察和研究了從先秦到民國,漢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化史。更難能可貴的是,徐先生深入研究,勤于思考,精于概括,善于提煉,對浩瀚的漢民族文化史,以文化底蘊、文化凝聚、文化定型、文化融匯、文化變古、文化重建、文化開新為關鍵詞,建構了文化底蘊,漢民族文化的來源;文化凝聚,先秦華夏民族文化的構建;文化定型,從秦到漢漢民族文化的圖像;文化融匯,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漢民族文化的圖像;在以文化變古,從北宋到南宋漢民族文化的圖像;文化重建,從元到明漢民族文化的圖像;文化開新,從清到民國漢民族文化的圖像七章的結構,在縱向的視野中,勾勒了漢民族文化史發展的軌跡和路線圖,把世界上唯一一個有連綿五六千年歷史,波瀾壯闊、跌宕起伏漢民族的文化發展、演進和融匯的圖像,動態地、有歷史縱深感地呈現給了讀者[6](P580)。
徐先生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發生、起源、形成、變異、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如同一個生命體,有孕育期、發育期、成熟期、衰弱期。漢民族這樣一個歷史悠久連綿、人口眾多的民族,其文化史也必然悠長、起伏、多彩、多變,在世界上應該是唯一的”[11]。所以,他在撰寫漢民族文化史中牢牢把握住漢民族特有的文化表達,如在論述春秋戰國華夏民族文化的匯聚時,從百家爭鳴:學術思想的經典化;仁者愛人:倫理道德的人本化;玉不去身:玉器文化的人格化;出禮入刑:法律文化的法制化;教之春秋:史學文化的多樣化;大象無形:文學文化的明道化;天人合一:信仰文化的世俗化等7個方面展開,每一項都是漢民族文化的獨具表達[12](P240-285)。
還需要提及的是,徐先生對漢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有許多獨到之處,讀后使人不得不擊節叫絕。如道家何以會在漢代脫穎而出而成為漢民族本土宗教的問題,徐先生另辟蹊徑,從儒道對峙切入,他認為:
儒家雖尊,但并非“罷黜”了“百家”,正如楊清虎有《論故“罷黜百家”其實是融合百家。但為什么同樣具有吸納和融合“百家”,在政治上強過道家的儒家沒有蛻化而成儒教,反而是弱于儒家的道家脫穎而出了呢?關鍵是道家眼睛向下,扎根民間;儒家眼睛向上,迎合上層。在理論上比較,從帛書《道德經》 可見儒道理論的對立:儒剛而道陰。儒家思想講求自強不息,大同思想、內圣外王之學,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主張,以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13]的心態,無不反映出剛健有為、奮進不止的精神,大有“天下者,我的天下”的氣概,政治意識極強;而道家思想清心寡欲,見素抱樸,渴望回到小國寡民的社會,主張無知、無為、無欲、不爭,貴柔、守雌、主靜,純任自然,泯滅主體能力,崇尚自然高遠,鄙棄狹隘功利主義,強調的是一個“靜”字[14](P413)。……于是,道教的創立者抓住、借用、發揮、膨脹了這些思想,使“道”成為至上神[12](P414-415)。
“道家眼睛向下,扎根民間;儒家眼睛向上,迎合上層。”徐先生一語點明了道家之所以能成為漢民族本土宗教,而儒家不能成為漢民族本土宗教的根本原因。此說有根有據,深入淺出,又接地氣,且抓住了儒道不同之關鍵,不能不令人嘆服。諸如此類的論述,在《漢民族史記·文化卷》中俯身可拾。如變:古今漢字的轉折點;秦兵馬俑:漢民族古代雕塑的巔峰之作;“變土為金”:從原始瓷到真瓷;漢樂胡舞:漢民族歌舞藝術融會的高潮;學派林立與人格建構:理學成熟;平民宗族:宋代漢民族鄉村社會的轉型;從楷書到宋體:穩定了漢字千年的字形;從《史記》 到《資治通鑒》 的大變古;從“六藝”到“四部”:漢民族學術文化的追根溯源;學科蜂起:漢民族學術文化的轉型,等等,等等,不勝枚舉。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由地域、語言、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構成的,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從《漢民族史記·文化卷》所展示的文化圖像中,可見“漢民族的文化史是一條川流不息的大江大河。這條大江大河從史前、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元到明、清到民國一路奔騰而來,使人們共享了一次心靈的巡禮。習近平總書記曾說:“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15]文化史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徐先生娓娓道來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漢民族文化的歷史生命力,感受到漢民族文化的歷史胸懷,感受到漢民族文化的歷史定力,感受到漢民族文化的多元張力,感受到漢民族文化的多彩魅力,感受到漢民族文化的靈魂呼喚”[12]1。正因為《漢民族史記·文化卷》 形塑了漢民族的靈魂,才使《漢民族史記》超凡脫俗而可成為鼎扛之大作。
六、人類學離散論視野:描繪漢民族走向世界的路線圖
令人驚異的是徐先生的《漢民族史記》竟然有一卷“海外移民史”。我作為徐先生指導的碩士,由于具有較好的英文基礎,有幸成為他撰寫此卷的學術助理。
離散(Diaspora),既是一個歷史的現象,亦是當今存在的社會現象。人類字學的離散論是近20 年移民研究的新理論,劉冰清和石甜認為“二戰后,關于離散的研究不僅僅是關注猶太人,視野范圍也擴大到了美籍非裔、海外華人以及因為持續戰亂所流離失所的亞美尼亞人,討論的內容也不僅僅是家園故土與客居他國的族群的關系,擴大到了第二代與故國的想象,因為勞動市場的開拓而引發的遷移等等。新的用法則涉及分離的任何類型,包括諸如中國人的貿易離散,或像土耳其人和墨西哥人的勞動遷徙離散。”[16]郝國強則認為“離散是全球化背景下,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新人口現象”,但“總體而言,國內外離散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有待繼續深入”[17]。
其實,徐先生早就開始關注族群的離散研究了。原來早在《漢民族發展史》出版之后的20世紀90 年代,徐先生就為當時研究漢民族史沒有包括海外華人、華僑而深感遺憾[6](P582)。此后,他心中一直記掛著這件事,并一直默默地進行著學術準備。機會不負有心人。2015年,徐先生開始撰寫《漢民族史記》就把“海外移民史”專列一卷,以還三十年前許下的心愿。
在徐先生眼中,漢民族不僅是中華民族視野中的“凝聚核心”,而且還是全球視野中的“太陽民族”。正是“凡有陽光的地方就有華人”,“看今天的世界,五大洲何處無華人?從東半球到西半球,從北半球到南半球,天涯何處無華人?漢民族真可以堪稱永不落的‘太陽民族’了。”[6](P582)在《漢民族史記》中,徐先生以漢民族海外移民的萌動時期、漢民族海外移民的開啟時期、漢民族海外移民的初發時期、漢民族海外移民的曲折發展時期、走向世界:漢民族海外移民的大發展時期五章,近60萬字的篇幅,向人們描繪了漢民族走向世界的路線圖。
由于是漢民族海外移民的開端之作,徐先生牢牢地抓住了三點:
一是把與漢民族移民有關的學科,如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宗教學、航海學、災害學和外交學等學科打通整合在一起,抓住民族史、移民史、航海史、造船史、災荒史、外交史、華僑華人史、佛教史等與漢民族移民有關的部分,努力打通,實現跨學科的交融和整合,來建構漢民族的海外移民史。
二是用大歷史的視野,把漢民族的海外移民置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思考“安土重遷”的漢民族為什么會從江河走向海洋?為什么會冒百死,反海禁,下南洋?為什么又會從南洋下西洋而走向世界,如《易經·系辭下》所云:“致遠以利天下”。成為一個對世界的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太陽民族”或“海洋民族”。
三是借華僑華人史的學術高地,盡力吸收華僑華人史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從而極大地豐富了《漢民族海外移民史記》的內容,使之有血有肉而可立于學術之林[6](P583)。
這種腦洞大開,“不二法門”[3]的創新之舉,呈現了漢民族2000多年波瀾壯闊的海外移民史,真正是難能可貴。為還20多年前許下的心愿,徐先生在《漢民族史記》的卷首扉頁上赫然寫上了“獻給全球華人”5個大字!正如王華博士所言,展示了徐先生“開闊的視野,偉大的胸懷”[18]!
七、結語:滿園春色關不住
人們常用“春色滿園關不住”來形容春天的生機盎然。其實,我們翻開《漢民族史記》,黃燦燦的帶有“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標志的護封,紅彤彤的精裝封面上印有一個大大的墨黑“漢”字,大氣之勢撲面而來。翻閱各卷,時不時地感受到濃濃的人類學味道和意韻。難怪此書的出版,得到了中國人類學會會長郝時遠先生和中國民族學會會長楊圣敏先生的鼎力推薦。郝時遠先生說:
徐杰舜先生能夠成就這樣一部漢民族史記的鴻篇巨制,是他幾十年來筆耕不輟、深入思考、不斷積累的結果,他先期的《漢民族發展史》、《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和《漢族風俗史》等研究成果,都是這一領域具有開創性的學術成就,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漢民族歷史研究中的權威學者地位[19]。
楊圣敏先生說:
該書不僅淋漓盡致地向讀者生動而形象,深刻而樸實地展示了漢民族驚天動地的歷史和文化,也寓意深切地向讀者明示了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偉大歷程的艱難和漫長,這是一般民族史著作很難有的境界和很難達到的高度[20]。
《漢民族史記》厚重而深邃,全面而系統,多彩而生動,以百科全書式的視角,向世界呈現了一個從歷史深處走來、陽光而偉岸的漢民族,將漢民族史研究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它既是一部有規模、有分量、有深度、有品位的里程碑式的漢民族通史,又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漢民族專史。當然,《漢民族史記》的價值和意義現在可能還難以充分顯現,還需要在歷史的“酒窖”中慢慢發酵,慢慢彰顯。正如馮天瑜先生所言:
《史記》能夠成就百科全書式的史學巨著,依靠其建立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位一體”的結構模式。……徐君的《漢民族史記》 追跡《史記》的結構方式,突破王朝述史的框架,按漢民族經歷的豐富性、多樣性部勒篇什,在比較舒展的框架內放手編寫,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悠久、文化繁富的一個大民族樹了碑、立了傳,實屬難能可貴。徐君把他的學術歷程比喻成“馬拉松”。這個研習漢民族史的“馬拉松”跑了半個多世紀,堪稱“在崎嶇小路上攀登不畏勞苦,今天,終于到達了又一座高峰,這是值得載入學術史的事。
唐代詩人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云:“天若有情天亦老”。說的是倘若上天也有感情,也會隨著歲月蹉跎而老去,也指自然法則是無情的。徐先生自己在《總后記》中也深有感觸地說:
《莊子·養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確實我們的生命是有限度的,而知識是沒有限度的,以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沒有限度的知識,就會弄得很疲困;既然這樣還要去汲汲追求知識,就會弄得更加疲困不堪了!說實話,雖然五年來研究和撰寫《漢民族史記》的經歷,使我深深體驗到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的疲困不堪,但吾初心不改,能為偉岸的漢民族,為“太陽民族”或“海洋民族”的全球華人,貢獻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吾心不悔
俱往矣!我們今天能讀到滿滿人類學味道的《漢民族史記》,真應該為徐先生的“吾心不悔”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