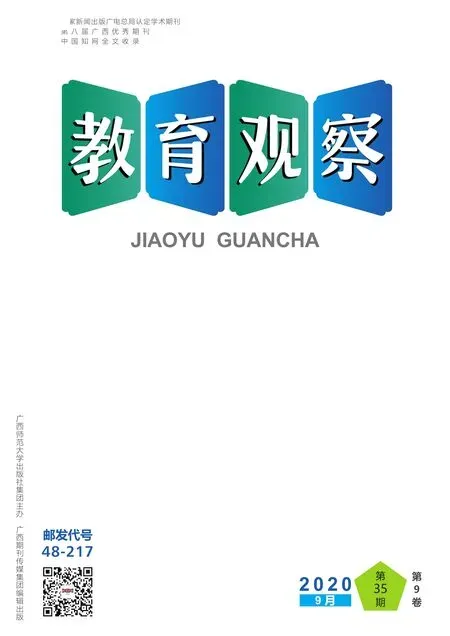疫情期間中小學教師參與在線教學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賴德信,李一飛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研究中心,北京,100036)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為了保障廣大師生的生命安全,教育部于2020年1月27日發布《教育部關于2020年春季學期延期開學的通知》,要求2020年春季學期延期開學,學生在家不外出、不聚會、不舉辦和參加集中性活動,鼓勵各地充分利用互聯網信息化資源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持,保證“停課不停學”。[1]各地政府、教研機構和學校紛紛制訂了學生在線學習方案,組織教師開展在線教學。社會各界專家和學者對此非常關注,比如,祝智庭等對教育部提出的“停課不停學”政策進行解讀,指出“停課不停學”過程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并給出了應對舉措。[2]焦建利等通過對“停課不停學”在線教學典型案例的剖析,針對不同實踐主體提出開展在線教學的相關建議。[3]全面了解疫情期間廣大中小學教師參與在線教學的基本情況、遇到的問題及提出的需求,提出政策建議,對未來進一步改善在線教學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為深入了解疫情期間中小學教師參與在線教學現狀,課題組通過問卷星對全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北京市、廣東省、浙江省、江蘇省、江西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遼寧省、陜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和重慶市進行了網絡調查。調查采用自編問卷,問卷內容包括教師基本信息、參與在線教學情況、對在線教學的認知和態度以及在線教育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與訴求四個方面,其中,參與在線教學情況包括疫情前使用網絡教學平臺的頻率及操作熟練程度、每天在線教學的時間,對在線教學的認知和態度包括是否支持在線教學、對在線教學的滿意度。調研采用隨機抽樣法,共對2276位中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最終共回收有效問卷2259份,有效率為99.25%。
一、疫情期間中小學教師參與在線教學的現狀
(一)疫情前在線教學參與度:整體水平較低,中西部和初高中學段教師的參與度明顯處于劣勢
針對“疫情之前,您運用網絡平臺開展在線教學情況”的問題,25.98%的教師選擇“經常運用并能熟練操作網絡平臺開展在線教學”,25.68%的教師選擇“運用過網絡教學平臺開展在線教學,但操作不夠熟練”,14.61%的教師選擇“只是偶爾利用網絡平臺開展過在線教學,操作基本熟練”,33.73%的教師選擇“幾乎沒有利用過網絡平臺開展在線教學”。從調查結果來看,雖然有一半中小學教師運用過網絡平臺開展在線教學,但是熟練操作在線教學的教師占比非常低。這表明疫情前中小學教師運用網絡平臺開展在線教學的情況不夠理想。
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區域(F=4.013,p<0.05)和學段(F=7.453,p<0.01)的中小學教師在開展在線教學的頻率和操作熟練程度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說,東部地區的中小學教師開展在線教學頻率和操作熟練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學教師。小學教師開展在線教學的頻率和操作熟練程度高于初中教師,初中教師高于高中教師。學段越高,中小學教師開展在線教學的頻率和操作熟練程度越低。
(二)在線教學支持率:整體水平較高,男性、教齡長、職稱高以及中部教師的支持率優勢明顯
針對“在線教學支持率”的調查結果表明,48.43%的教師表示非常支持,27.89%的教師表示比較支持,20.19%的教師表示一般,2.74%的教師表示比較反對,0.75%的教師表示非常反對。總體來說,支持開展網絡在線教學的教師占絕大多數,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或反對的教師約占1/5,明確表示反對的教師占比不到4%。
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性別(F=22.823,p<0.001)、教齡(F=4.209,p<0.01)、職稱(F=4.323,p<0.05)和區域(F=11.023,p<0.001)的教師對疫情期間開展在線教學的支持態度均存在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男教師比女教師更支持在線教學。在教齡方面,教齡越長的教師對開展在線教學的支持率越高,其中,1—3年教齡教師的支持率最低,20年及以上教齡教師的支持率最高。在職稱方面,職稱越高的教師對開展在線教學的支持率越高,未評職稱教師對在線教學的支持率最低,一級教師、二級教師和三級教師的支持率居中,高級職稱教師對在線教學的支持率最高。在區域方面,東部地區教師對開展在線教學的支持率最低,西部地區教師的支持率居中,中部地區教師的支持率最高。
(三)在線教學時間:多數教師參與在線教學時間短,15—20年教齡、中部和鄉村學校教師參與在線教學的時間相對較長
問卷中涉及的在線教學時間是指教師每天參與在線教學直播、輔導、批改作業、交流與反饋等所有時間的統稱。調查統計結果顯示,25.98%的教師每天參與在線教學的時間為1小時以內,33.51%的教師為1—2小時,18.99%的教師為2—3個小時,8.72%的教師為3—4個小時,只有12.79%的教師每天參與在線教學的時間為4個小時以上。總體來說,疫情期間,中小學教師每天參與網絡在線教學的時間比較短、教學任務相對輕松。
由于各地教育部門對在線教學的要求和做法不同,因此,不同群體教師每天參與在線教學的時間也不同。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教齡(F=4.230,p<0.01)、地域(F=4.079,p<0.01)和學校類型(F=6.782,p<0.001)的教師群體參與在線教學時間均存在顯著差異。在教齡方面,10—15年教齡段教師參與在線教學時間最短,1—3年、4—9年和20年以上三個教齡段教師緊隨其后,15—20年教齡段教師參與在線教學時間最長。在區域方面,東部地區教師參與在線教學時間最短,西部地區教師次之,中部地區教師參與在線教學時間最長。在學校類型方面,各地區重點(示范)學校教師參與在線教學時間最短,縣城學校教師和城市一般學校教師居中,鄉鎮或鄉村學校教師每天參與在線教學時間最長。總體來說,辦學質量越好的學校的教師每天參與在線教學的時間越短。
(四)教學效果滿意度:整體水平不高,中部、小學和重點學校教師的滿意度相對較高
疫情期間,在線教學效果深受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中小學教師對在線教學效果的滿意度如何?問卷統計結果顯示,12.13%的教師表示非常滿意,39.31%的教師表示基本滿意,34.97%的教師表示一般,11.20%的教師表示不太滿意,2.39%的教師表示非常不滿意。總體來說,中小學教師對網絡在線教學效果的滿意度不高,僅一半教師對在線教學效果感到滿意,另一半教師表示不滿意。
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區域(F=3.839,p<0.05)、學段(F=23.460,p<0.001)和類別學校(F=6.060,p<0.001)的中小學教師對在線教學效果的滿意度均存在顯著差異。在區域方面,中部地區中小學教師對在線教學效果的滿意度最高,西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最低。在學段方面,小學教師對在線教學效果的滿意度最高,初中教師次之,高中教師最低,即學段越高的中小學教師的滿意度越低。在學校類別方面,各地區重點學校的教師對在線教學效果的滿意度最高,城市一般學校教師次之,縣城和鄉鎮或鄉村學校教師最低。
(五)最希望得到的幫助和支持:優質課程內容資源或素材的獲取、家長的理解與支持和學生家庭網絡條件的保障位列前三
疫情期間,不少中小學教師首次接觸網絡在線教學,對網絡教學平臺的操作、教學形式和教學模式都不熟悉,需要得到更多幫助和支持。調查結果顯示,教師最希望得到的幫助和支持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優質課程內容資源或素材的獲取、家長的理解與支持和學生家庭網絡條件的保障,占比分別為74.86%、52.50%和49.05%。“優質課程內容資源或素材的獲取”成了疫情期間教師最希望得到的幫助和支持,這說明疫情發生后,教師對教學資源的選擇和使用需求發生了較大轉變。為進一步適應在線教學需求,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教師對紙質學習材料的需求相對減少,對優質網絡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家長的理解與支持”和“學生家庭網絡學習條件的保障”也是中小學教師的需求。這反映出與學校集中課堂教學相比較,在線教學有其自身不足和缺陷。教師要開展好在線教學,不但需要學生家庭良好網絡條件提供保障,還需要家長的全力支持與配合。
同時,教師還普遍關注“在線教育平臺和工具的科學選擇”和“網絡直播、視頻剪輯技術培訓”等需求,占比分別為43.74%和46.61%。這說明中小學教師對在線教學平臺和工具的科學選擇能力比較薄弱,對在線教學平臺使用不夠熟練,希望通過加強網絡直播、視頻剪輯等技術培訓來提升自身的教育信息化技術水平和在線教學能力。
二、疫情期間中小學教師參與在線教學所遇到的問題
(一)教師缺乏與在線教學相適應的“互聯網+教育”理念
“互聯網+教育”是當今教育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互聯網+”背景下的信息化教育不再是以知識灌輸和傳授為主的教育,而是以學生個性發展、核心素養和綜合素質全面發展為目的的教育。[4]“互聯網+”給傳統教育理念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它強調教育機構的多元性、教育資源的開放性、學習的自主性以及教學的互動性。學校不再是教育的唯一載體,社會教育機構、新型教育組織將成為傳統學校教育的有效補充;教育資源集聚不再局限于相對封閉的校園,而是通過互聯網渠道擴展到世界各地,使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成為可能;學習者自主選擇課程、自我評價和自我分享;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教師角色的作用從教學的主導者變成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服務者。[5]
疫情期間,中小學教師開展的在線教學只是停留在把教育技術與教學活動進行簡單的疊加運用上,直接把傳統學校課堂教學照搬到網絡上,教學資源選擇過分依賴現有教材和課程內容,教學設計沒有充分考慮學生居家學習的特點。教學直播仍然以教師講授為主,出現了講課時間過長、師生間缺乏有效溝通等問題。因此,在線教學活動折射出中小學教師比較缺乏“互聯網+教育”理念。盡管我國出臺了《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等多個政策性文件,但由于缺少政策解讀的專門培訓,中小學教師對相關文件精神的學習領會不夠,對“互聯網+教育”的本質和內涵的理解不夠深刻。
(二)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不能完全勝任在線教學任務
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是指以促進學生發展為目的,利用信息技術、資源從事教學活動,完成教學任務的綜合能力。[6]調查結果顯示,中小學教師的信息化教學能力總體比較薄弱,40.10%的教師表示不會或不能熟練使用網絡教學設備,44.57%的教師表示對在線教學平臺不熟悉,37.26%的教師表示對在線教學的形式不熟悉。這反映出中小學教師在疫情發生之前參與在線教學的機會較少,對在線教學平臺和形式不夠熟悉。另外,57.58%的教師表示對在線教學的課程資源建設準備不夠充分,這表明教師的資源整合和融合能力比較欠缺。以往開展的教師信息技術技能培訓多是關注信息技術在具體教學中的運用,缺乏對信息資源整合和融合能力提升的關注。與傳統課程資源不同,網絡課程資源非常豐富,但是質量卻參差不齊。如何科學地甄別網絡課程資源并為己所用,要求教師具備一定的資源整合和深度融合的能力。信息化時代,中小學教師原有的知識和能力已經不能勝任在線教學任務,教師需要具有更高的教育信息化素養。
(三)教師缺乏在線教學經驗,在線課堂的互動效果不夠理想
“互聯網+教育”為在線教育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使在線教學的課堂更具有現場感。在線教育強調教學團隊發揮作用,更加注重對學習過程的引導,強調學生的參與和學習效果的體現,注重學習體驗和學習反饋。[7]在在線教學課堂中,只有讓學生充分參與師生互動和同伴交流,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學生的學習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很多教師表示疫情期間的在線教學有許多問題期待解決。其中,在線教學的互動效果是教師比較關注的重要問題。調查結果顯示,60.42%的教師認為開展在線教學活動時的互動效果不夠理想。在線教學的互動效果差可能是由多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最為根本的原因在于教師缺乏在線教學經驗。比如,在在線教學課堂中,教師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開展教學互動、如何拋出一個互動話題才能夠吸引學生積極參與互動等,都需要參與在線教學的教師認真思考。
(四)部分網絡環境和硬件設備不能滿足高位運行的在線教學需求
信息網絡是教育信息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教育信息化的物質基礎和先決條件。目前,我國絕大部分中小學都實施了以“校校通”工程為代表的信息化網絡基礎工程建設,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為我國教育信息化奠定了基礎。然而,在開展在線教學活動過程中出現了非常尷尬的現象,即有些網絡服務器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宕機、網路堵塞等現象。比如,調查統計結果顯示,31.78%的教師遇到過“沒有網絡、信號不好、不時有掉線斷網情況”,26.51%的教師遇到過“上課時教學設備時有發不出聲音或看不到圖像的情況”。造成服務器宕機和網絡不暢通的直接原因在于,現有的網絡服務器遠遠不能滿足實際訪問人數的需要。雖然全國各大網絡公司、地方各級教研機構建有網絡教育平臺,全國大部分學校也建有“校園通”網絡平臺,但平時真正利用這些平臺開展在線教育的教師并不多,一些問題平時顯現不出來,一旦網絡平臺使用人數突然劇增,很多問題就會集中爆發出來。疫情發生初期,參加在線學習、教學的師生數量在短期內呈現出幾何級的增長,使得網絡不堪重負,出現網絡堵塞甚至服務器宕機的情況。
三、進一步完善教師參與在線教學的對策
(一)樹立“互聯網+教育”理念,適應未來教育新常態
包括教育部門領導者、科研機構研究者、學校管理者和一線教師在內的廣大教育工作者要認真學習《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等政策文件,領會文件精神,深刻理解“互聯網+教育”的內涵,樹立“互聯網+教育”理念,謀劃未來教育規劃和發展大局,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創新管理機制,提升學校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尤其是教研人員和一線教師要在“互聯網+教育”理念下重新審視日常教育教學工作,重新規劃和設計教學內容,適時調整教學方式,不斷創新教學方法,保障在線教學質量。樹立“互聯網+教育”理念不僅是疫情期間在線教學的需要,更是適應未來教育新常態的要求。
(二)加強資源融合主題的專項培訓與實踐,不斷提高教師的教育信息化綜合素養
信息化時代,信息化能力是中小學教師信息化綜合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線教學暴露出教師的教育信息化能力整體偏弱的問題,其中,資源融合能力弱的問題尤為突出。為此,相關中小學教師培訓部門要做好培訓頂層設計,在完成日常教師教育信息化能力提升培訓的基礎任務外,要僅僅圍繞資源融合主題開展專項培訓。同時,中小學要為教師參加培訓提供必要的實踐場景支持,保障教師培訓的真實、有效。中小學教師要增強問題導向意識,結合學科特點,帶著在疫情期間在線教學中所遇到的問題參加培訓,將學到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結合起來,做到有的放矢,讓培訓更有針對性。主題式專項培訓可以幫助中小學教師提高資源融合的理論水平和強化實踐認知,不斷提升教育信息化綜合素養。
(三)要適時調整角色和課堂提問的策略,保障在線教學互動的有效性
在線教學的互動效果不理想,一是因為在線教學平臺本身不夠完善,二是因為教師沒有及時調整角色,缺乏一定的課堂提問策略,使在線教學互動效果大打折扣。在在線教學課堂的討論過程中,教師要適時調整自身角色,由傳統的傳授者和主導者轉變為促進者和指導者,與學生平等交流,消除學生的緊張感,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互動,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同時,教師在開展在線教學的過程中要及時調整提問策略,重視課程提問設計,注重提問方法的選擇性運用,關注課堂提問的有效性,掌握線上教學問答技巧。[8]
(四)更新硬件設備,優化網絡環境,為教師提供良好的在線教學環境
針對疫情期間集中暴露出的“網絡堵塞”問題,網絡服務運營主體要重視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加強中西部地區省市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網絡基礎設施進行全面“體檢”,更新硬件設備,優化網絡環境。中小學要成立由網絡技術、教學資源兩方面人員構成的在線教學服務支持團隊,技術人員負責提供在線教學過程中出現的技術故障消除服務,教學資源支持人員負責提供教學資源安排、教學過程監控等服務,為教師提供良好的在線教學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