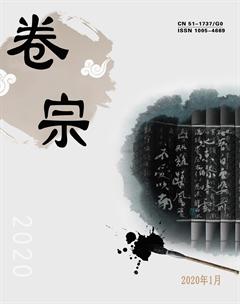淺談六朝墓葬出土憑幾
馬馳浩
摘 要:六朝的南方墓葬中出現了憑幾,并逐漸成為中一種常見的隨葬器物。憑幾最初作為實用器用于陪葬,后逐漸明器化。考古發現的憑幾多出現在等級較高的墓葬中,具有標識身份的含義,少數低等級墓葬亦有憑幾隨葬,可見憑幾并非上層貴族所獨享的一種器具。憑幾與祭臺、牛車伴出,反映了兩種不同的使用場景,也是墓葬制度在六朝時發生變革的重要標志之一。
關鍵詞:憑幾;明器;墓葬;晉制
西晉以來,南方的墓葬與東漢時期相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開始出現一批獨有的隨葬品。憑幾即為其中的一種,其由彎曲的幾面和三足組成,幾面下部中空,幾足外折,多數作獸足狀,部分作尖足。
考古出土的憑幾可分為木、陶和石質三種。木質憑幾出現時間最早,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木質憑幾為安徽馬鞍山朱然墓[1]所出,西晉晚期至東晉早期的個別墓葬中偶有發現,但數量極少。陶憑幾開始出現于東晉早中期,數量最多,均為明器,如鎮江諫壁磚瓦廠東晉墓出土的憑幾[2]。南朝時期憑幾變小,更具明器特點,如南京虎踞關、曹后村兩座東晉墓中所出的憑幾[3];石質憑幾的出現晚至六朝晚期至隋唐初年,如常州戚家村畫像磚墓即發現石憑幾一件[4]。總體而言,墓葬中的憑幾出現及流行的時段為西晉末年至南朝末年,流行地域多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以南京地區最為集中。憑幾最初是作為實用器陪葬的,約在東晉以后逐步明器化,開始具有喪葬禮器的功能。
出土憑幾的墓葬等級較高,朱然為東吳大將,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極有可能是東晉帝陵,南京郭家山東晉溫氏家族墓的墓主為安郡公溫嶠,是目前正式發掘的規模最大的可明確墓主的東晉墓葬[5]。因此,憑幾應是六朝貴族普遍使用的重要隨葬器物。此外,亦有少量普通墓葬出土憑幾,如鎮江東晉紀年墓M3[6]、鎮江丁卯“江南世家”工地六朝墓M1[7],兩墓規模小,隨葬品簡單,墓主人身份等級不高,均為一般平民。
憑幾出現于六朝的墓葬之中,是具有代表南朝墓葬變革含義的一種隨葬品。作為明器用于喪葬活動中,其功能并不是單獨表現的,往往通過與其他隨葬品一同組合使用。從考古發現的情況來看,與憑幾一同伴出的隨葬品還包括陶牛車、瓷香薰、唾壺、多子盒、雙沿罐、束頸罐和三系罐等。不同的組合形式反映了憑幾不同的使用方式,同時也具有不同的喪葬含義。
憑幾與牛車是六朝南方地區特有的一種隨葬組合,此類實例不多見,墓葬等級較高。南京象山東晉七號墓內的陶憑幾置于牛車內,環形開口朝向牛車車門,由此推測,此憑幾主要供乘坐牛車之人背靠支撐。牛車在東晉、南朝時期已成為社會上層貴族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是身份等級的重要標志,陶牛車是當時墓葬中重要的隨葬品。實際上早在2世紀前期,士大夫已喜乘牛車,至遲在西晉時期,憑幾已經作為一種重要的出行工具與牛車一同出現了[8]。《晉書·輿服志》記載:“古之貴者不乘牛車,……其后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世庶遂以為常乘”[9],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六朝。社會上層人物出行時以牛車代馬車,是車制上的重大變化。
憑幾常與各種陶、青瓷器伴出于墓葬的祭祀空間。例如在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甬道磚地上,原有一陶案作祭臺之用,案上即放置陶憑幾一件,與之伴出的還有陶盤、陶耳杯、陶盆、陶果盤、青瓷盤、青瓷耳杯、青瓷雞頭壺、青瓷雙耳壺、青瓷四耳壺、青瓷六耳罐和青瓷四耳蓋罐等[10];南京象山M7墓室前部有長方形四足陶案,其上亦有一件陶憑幾[11]。由此可見,憑幾的另一個重要身份是祭祀用品,作為其中唯一的家具明器,與眾多容器共同構成了六朝墓葬中新的祭祀用器組合。《通典》所引賀循《議禮》的內容常被用于六朝墓葬隨葬品的討論[12],其中便提及憑幾。
正如齊東方先生所言,“自東漢以來,祭祀空間從先秦時期的廟祭逐漸向墓祭轉變。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葬多流行單磚石墓,墓祭的形式從東漢時期前堂向墓室內的祭臺轉變。墓葬形制改變了祭祀方式,祭祀方式又使器形發生變化,陶憑幾,瓷香薰、唾壺、多子盒、雙沿罐、束頸罐和三系罐等成為祭臺上新見的器形,與漢墓前堂磚臺上面放置陶燈、碗、盤、魁、博山爐、方盒、耳杯、案、筷、刀等器類組合不同。漢代器物組合宴飲的意味更濃,而西晉的祭臺上的器物更多帶有祭奠的感覺”[13]。
綜上所論,憑幾的出現及流行是南朝墓葬的新氣象。憑幾放置位置的不同,反映了憑幾不同的使用方式及場合,一種是作為日常休息倚靠之物;另一種則作為祭祀用品參與到對墓主人的祭奠活動中來。在南朝時期,社會上層人物追求清談玄學,不問社會俗事,憑幾的使用正是這種社會風尚的真實反映。至于少數出現憑幾的等級較低的墓葬,其墓主人極有可能是當時社會上的沒落貴族或少數效仿者,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憑幾的使用雖然有明顯的等級界限,但這種等級的差別似乎不是由官方的強制規定所致,而應是上層士大夫貴族階層的一種約定俗成的行為,以致社會上偶有少數效仿者使用的現象出現。
東晉、南朝以來的墓葬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無論在墓葬形制還是隨葬器物上,均出現了與前代不同的新氣象。俞偉超先生將這種新的墓葬制度稱為“晉制”,以單一磚室墓為明顯特征[14]。這引發了學術界的討論,霍巍先生認為除了墓葬形制的演變之外,對“晉制”的研究亟待從更多方面加以考量[15]。齊東方先生深刻剖析了構成“晉制”內涵的四個概念:喪葬觀念、喪葬習俗、喪葬儀式、喪葬制度。認為晉制的存在與否,應該從這四個要素的動態形成過程來觀察。曹魏墓葬的不封不樹首開先河,西晉墓葬承其流風,衣冠南渡以后,以中原為正朔的東晉王朝繼承了北方墓葬制度。由此可以確定,魏晉時期由于上層觀念的轉變,使得原有的喪葬觀念受到沖擊動搖。原來東漢時期前堂后室的墓葬形式發生了改變,原有的橫前堂被祭臺代替,表明了喪祭禮儀的轉變。漢代墓葬中習見的日用品組合,在魏晉時期逐步向祭奠儀式感更強烈的用器過渡。牛車、陶俑、儀仗組合成為兩晉墓葬的普遍風尚,并逐漸被社會各層面接受,進而成為群體記憶而被固化成為一種習俗[16]。而憑幾則是這種變化的重要標志之一,它與眾多六朝時期特有的隨葬品共同構成了新的文化內涵與時代特征。
參考文獻
[1]丁邦鈞.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J].文物,1986(03):3-17+99-106.
[2]肖夢龍.江蘇鎮江諫壁磚瓦廠東晉墓[J].考古,1988(07):47-61+102-104.
[3]周裕興.南京虎踞關、曹后村兩座東晉墓[J].文物,1988(01):79-86.
[4]駱振華,陳晶.常州南郊戚家村畫像磚墓[J].文物,1979(3):32-41.
[5]岳涌,張九文.南京市郭家山東晉溫氏家族墓[J].考古,2008(6):3-25.
[6]林留根.江蘇鎮江東晉紀年墓清理簡報[J].東南文化,1989(02):159-164+140+202.
[7]鎮江博物館、鎮江市文管辦:《鎮江丁卯“江南世家”工地六朝墓》,《東南文化》2008年第4期。
[8]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8—119頁。
[9]《晉書·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434頁。
[10]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J].文物,1973(4):38-52.
[11]袁俊卿.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J].文物,1972(11):23-41.
[12](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八六《喪志四·薦車馬明器及棺飾》,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325—2326頁.
[13]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J].考古學報,2015(3):345-366.
[14]俞偉超.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15]霍巍.六朝墓葬裝飾中瑞獸的嬗變與“晉制”的形成[J].考古,2016(2).
[16]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J].考古學報,2015(3):345-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