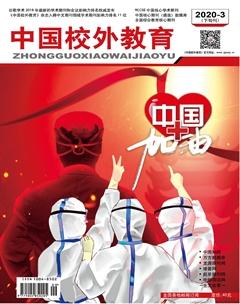論從“準五服以治罪”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轉變
關珊
【摘要】“準五服以治罪”原則是中國古代自晉以來歷代沿襲的法律制度,以遵守親疏血緣關系和尊卑地位等級為核心,體現了宗法社會對于儒家綱常倫理和禮制的維護。在古代社會,“準五服以治罪”有利于維護家庭的穩定、社會的和諧和封建國家的鞏固。但隨著封建社會的結束,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準五服以治罪”原則中體現的“同罪異罰”原則違背了現代法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觀念,已不能和現代社會相適應。以古代“準五服以治罪”到現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變化為著眼點,討論二者的區別以及導致該變化的因素。
【關鍵詞】準五服以治罪法制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引言
喪服制度是中國古代傳統禮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古代傳統家族中的等級尊卑觀念。傳統認為在《晉律》中首次確定的“準五服以治罪”原則是將喪服制度上升至法律層面的源頭。自此以后,“準五服以治罪”因其與傳統宗族觀念相契合,在中國古代法律中一直被保留并且地位不斷提高,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準五服以治罪”制度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因為“準五服以治罪”在古代作為定罪量刑的制度有著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對其的研究也是中國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中,大多對該制度持否定態度,認為“準五服以治罪”與現代社會所公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對立。有鑒于此,筆者將以從古代“準五服以治罪”到現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變化為著眼點,討論二者的區別以及導致該變化的因素。
二、“準五服以治罪”的概述
1.“準五服以治罪”的含義
喪服制度是中國古代服喪期間的一種服飾制度,指人死后其親屬要按照與其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穿著不同材質的喪服以及規定不同的居喪時間。喪服分為五個等級,分別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等級,稱為五服。與這五個等級相對應的是五個不同的居喪時間,分別是3年、1年、9個月、5個月、3個月。血緣關系越近,喪服材質越差,居喪的時間也越長。
“準五服以治罪”是指在親屬相互侵犯的行為中,以五服制度中所規定的血緣親疏及尊卑關系作為定罪量刑標準的法律原則。在該原則中,服制越近,以尊犯卑者,所處刑罰越輕,以卑犯尊者,所處刑罰越重;服制越遠,所處刑罰越輕。
2.“準五服以治罪”的意義
“準五服以治罪”強調家族中的等級尊卑關系,符合古代宗法制度中的等級觀念和儒學所提倡的“親親尊尊”觀念,是儒學法律化的重要體現。孔子在《論語》中說道:“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句話意在強調孝敬長輩不只是贍養他們,更應該尊敬他們。而“準五服以治罪”原則正是將這種對于長輩的尊敬上升至法律規范,如果違背孝道就要受到法律的懲治,以此用法律維護家庭的和睦,維系親情。小家和睦,那么由無數個小家組成的國家也自然就達到了和諧穩定。因此,“準五服以治罪”原則具有促進國家和社會和諧穩定的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君主的封建專制統治。
三、“準五服以治罪”的歷史發展原因
1.政治原因
中國古代的政治具有“家國一體”的特征,用倫理秩序來構建國家的統治結構,而家和國的同構是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礎之上的。西周時期宗法制確立,成為了鞏固國家統治的重要政治制度。宗法制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其實質是用血緣關系來維系國家的統治。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宗法制逐漸瓦解,但嫡長子繼承制、家族制度和尊宗敬祖的觀念,長期影響著中國社會。所以,在西周以后的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宗法作為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強調等級尊卑和血緣關系的“準五服以治罪”原則高度契合統治者以宗法鞏固君主專制的需求,因此該原則在歷代法律中有著重要地位。
2.經濟原因
在中國古代的經濟結構中,自然經濟一直占有主導地位。戰國時期形成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古代的基本經濟形態。小農經濟以家庭為單位,是一種男耕女織式的自給自足的經營方式。統治者為了維護專制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小農經濟,在歷朝歷代都采用“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以農業為本。在小農經濟和重農抑商的經濟背景之下,農業與家庭的關系極為密切,農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家庭穩定的基礎之上。因此統治者想要國家的農業和經濟發展就必須維護住每一個家庭的穩定,這也是“準五服以治罪”得以推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3.思想原因
孔子在春秋時創立了儒家學派,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和禮。儒家思想中強調人們應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和封建禮制,這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遵守家族和國家中的等級尊卑關系。“準五服以治罪”使得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律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是儒學法律化的體現,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儒家的綱常倫理。而在漢代董仲舒改變儒學,融合法家、陰陽家和黃老之學后,新儒學適應了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被漢武帝所推行。從此,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此后的歷代,儒學的地位不斷提高,因此符合儒家思想的“準五服以治罪”原則也一直被統治者推行。
四、“準五服以治罪”的歷史發展過程
傳統認為,晉制《晉律》是將喪服制度納入法律的源頭,著名歷史學家瞿同祖先生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到“《晉律》‘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治罪。開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在這以后,“準五服以治罪”原則在歷代不斷發展。
在唐代,“準五服以治罪”原則在《唐律》中處于核心地位,受到高度重視。“唐律十二篇中,反應了‘五服制度的篇目除衛禁、擅興、乍偽三篇無涉,其余各篇都有涉及,在名例、戶婚、盜賊、斗訟叫篇中,所占比例最大。全文502條律文,涉及‘五服制度的有154條,明確指稱親等、服制的條文81條,占全文百分之十六。”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唐朝時對服制的重視,從而體現了對禮法的重視。
唐朝以后,“準五服以治罪”原則宋、元、明不斷發展并體現出地位不斷提高的趨勢。隨著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在清代達到了頂峰,“準五服以治罪”的地位也可以說是達到了頂峰。從清代基本法典《大清律例》卷首的《喪服圖》和《服制》中不難看出服制在清朝的重要地位以及服制對清朝法律全面性的影響。
鴉片戰爭的打響,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始,隨著中國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西方的文化也進入中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西方的思想和法律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國的傳統法律開始向近代化轉變。直到新中國成立,“準五服以治罪”因其體現了傳統封建思想被視為封建主義的“糟粕”而被徹底廢除。
五、從“準五服以治罪”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準五服以治罪”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區別
從含義上來說,“準五服以治罪”原則是對于親屬間犯相同的罪行,而因其血緣關系的親疏和尊卑等級不同而進行不同的處罰,這體現了其“同罪異罰”的本質。同時,處于家庭中的卑幼等級的家庭成員因喪服制度和“準五服以治罪”的規定必須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和義務,而與這些責任和義務相比并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權利,這是對卑幼者的一種不公平的待遇,是權利和義務不對等的體現。
反觀現代的法律,規定凡是同類人和同類的案件都應該按照相同的規則處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現代的法律中人和人之間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我國古代的等級尊卑的關系,因此這也體現了“準五服以治罪”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質上的不同。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來說,現代人更加注重的是人權、平等和自由,而“準五服以治罪”與此相違背。因此在這個層面上來說,“準五服以治罪”的廢除符合社會進步發展的趨勢,存在其歷史的必然性。
2.導致該變化的原因
從政治方面來說,我國的國家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國古代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國家性質的不同導致了法律制度的不同。“準五服以治罪”原則本質上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工具,而現在的中國不是君主專制的國家,因此該制度已經不符合國家政治的需要,不能與現代社會相適應。
從經濟方面來說,在我國古代占主導的是自然經濟。而在鴉片戰爭后,中國的經濟結構開始發生改變,自然經濟開始解體,直到1956年底對農業、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自然經濟徹底解體。現在的中國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多種經濟共同發展,不再是小農經濟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因此經濟的發展和家庭的聯系變得不像古代那樣緊密,也自然不用通過“準五服以治罪”這種法律手段維系家庭的穩定,從而為國家經濟提供保障。
從思想方面來說,雖然儒家思想依然是中華傳統思想的組成部分,但人們對于儒家思想的態度并不是全部接受,而是辯證地看待儒家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于“準五服以治罪”體現的等級尊卑觀念,我們把它看作是古代儒家思想中具有局限性的部分。相比之下,現代的人們更加注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所以“準五服以治罪”并不能適應現代的社會大環境。
六、結論
“準五服以治罪”原則是中國古代自晉以來歷代沿襲的法律制度,以遵守封建社會大家長制中的血緣親疏關系和地位尊卑的等級為核心,體現了宗法社會對于儒家綱常倫理和禮制的維護,是儒學與法律相結合的體現。在古代社會,“準五服以治罪”有利于維護家庭的穩定,社會的和諧,在鞏固君主的專制統治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隨著封建社會的結束,現代社會的到來,“準五服以治罪”原則已不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共存,逐步走向消亡。現代的中國和古代中國已經在政治經濟方面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人們的思想也較傳統社會中人的思想更加開放和進步,因此“準五服以治罪”不能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其消亡有著歷史必然性。但同時我們也應辯證地看待“準五服以治罪”制度,我們不能否認該原則中對于尊老愛老思想的重視在現在的社會也仍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9.15.
[2]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207.
[3]陳奇.《唐律》中的“禮”——以服制為中心[J].雞西大學學報,2009,(01) :96.
[4]高學強.從喪服制度在近代的變遷看中國傳統法律的近代化[J].青海社會科學,2009,(01):112.
[5]殷躍飛.現代法治觀念視野下的唐代“準五服以治罪”原則[J].赤峰學院學報,2015,(0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