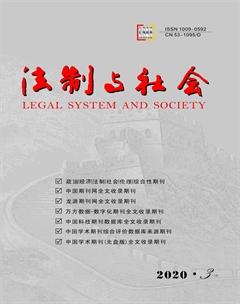“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初探
汪靖歡
關鍵詞立法 公眾參與 “互聯網+”
一、概念界定
陳斯喜指出,公眾參與立法就是在法的制定過程中,允許立法機關以外的人員公開參與并發表意見的制度。參與式民主并非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民主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補充和修正了代議制民主。公眾參與就是參與式民主的核心主題。“公眾”的范圍廣于“公民”,公民只是公眾的一個方面。通過公眾參與,公眾的意見、態度、觀點能夠或多或少地對立法工作產生的影響。
《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互聯網+”是將互聯網領域的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以構筑經濟社會發展新優勢和新動能。所謂“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就是將互聯網技術運用到立法的公眾參與過程中,發揮互聯網技術的優勢,在互聯網技術的幫助下,使得公眾真正參與到立法工作的各個環節、使得公眾的意見能夠被立法者所認知并對立法工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最終達到《立法法》要求的民主立法目標。
二、“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的現狀
我國立法者已經認識到了立法中公眾參與的必要性。民主立法原則已被寫入《立法法》當中。近年來,互聯網技術已經被或多或少地運用在立法公眾參與過程中,網站、電子郵箱等成為了公眾參與立法工作的途徑。這些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也得到了廣泛響應。比如在2011年,超過八萬人通過中國人大網對《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發表意見。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公眾參與立法的方式也更加多樣化,如天津市設立了立法微信平臺,專家學者可以在這一平臺探討相關工作。
由此可見,通過互聯網擴大立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已經在全國各地各級的立法活動中有了體現。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公眾通過互聯網參與立法工作的途徑和形式有了新變化。這些實踐都為今后“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的進一步深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三、“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一)公眾參與促進公眾對法的認同
現代實證法依靠強制力和威懾來確保法律的實施,如《刑法》通過規定各種刑事責任來懲治犯罪。在某種程度上,公眾守法是因為恐懼或是為了避免違法所造成的不利后果而不是基于對法律的認同。之所以強調公眾參與立法的重要性,是因為它能夠增進公眾對立法成果的接受程度。公眾在參與立法工作的過程中能夠或多或少地認識到法律是在自我意志影響下的產物,他們就更可能因為法律是自己意見影響下的產物而認可、認同法律,進而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此時,法的正當性就更多地來源于公眾的認同與尊重,法在實施中遇到的來自公眾的阻力也隨之減小。
(二)公眾參與是提升立法質量的要求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己經建立。我國的立法者曾主張“立法宜粗不宜細”。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法規要符合經濟基礎的發展狀況才能進一步推動經濟基礎的發展,所以要提升立法質量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因而,立法工作的重點開始由“重數量”轉向“重質量”,立法者開始將提高立法質量作為立法工作的目標之一,提高立法質量也成為立法工作的原則性要求之一。立法公開不失為提升立法質量的一個有效途徑。以公眾意見為基礎使得立法成果真正反映民意、滿足公眾的需求,公眾意見的監督也能夠幫助立法機關減少立法工作中的差錯,最終使得立法質量得到提升。有鑒于此,通過公眾參與征集社會各界意見和建議有利于提升立法質量,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于提升立法質量的需求。
(三)“互聯網+公眾參與”具有獨特優勢
傳統上,立法機關通常采用會議的形式(如座談會)征求社會意見。值得肯定的是,這些方法體現了民主立法原則,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立法過程中公眾參與的要求,有利于立法成果反映公眾意見。
然而,這些傳統方法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一般而言,這類傳統的意見征集方法的組織、運行過程較為復雜,開銷也并不低廉。此外,這些方法所能涵蓋的公眾的數量也是極為有限的。由于親身參與聽證會或座談會程序較為復雜,且需要一定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公眾參與這類意見征求活動的積極性也難以得到保證。譬如昆明市人大常委會曾在2001年召開了一次立法聽證會。但是這次會議只有一人報名參加,這位市民最終也沒有到會。。
截然不同的是,互聯網技術的運用可以很好地克服上述傳統手段的缺點。首先,立法機關可以通過既有的網絡平臺發布相關立法信息并征求公眾意見,這得通過互聯網途徑征求立法意見十分簡便且成本較低。這有利于提升立法者落實公眾參與的要求。其次,互聯網具有極為廣泛的受眾與極強的開放性,社會公眾可以平等地通過互聯網途徑參與到立法活動中去。這樣一來,通過互聯網,立法者可以收集更多的、更加全面的公眾意見,拓展公眾參與的深度和廣度。再次,公眾通過互聯網表達意見的成本也更低。在如今移動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公眾可以利用人手一部的聯網設備簡單高效地表達意見和見解而不需要付出較多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這能夠進一步激發公眾參與立法活動的積極性。
總之,公眾對立法成果的接受度因公眾參與而上升,公眾參與也是適應社會發展、提升立法質量的必然要求。然而,傳統的意見征集途徑存在著成本較高、效率較低、激發公眾積極性難等問題。借助互聯網的開放性、便捷性及其受眾的廣泛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文提到的問題。因而,將互聯網技術與立法的公眾參與結合有其現實意義和必要性。
四、“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的問題分析
固然,“互聯網+公眾參與”已經在各地立法實踐中有所體現,但這一公眾參與的途徑仍然可能存在或放大一些問題。
首先,大眾媒體報道的事件并非總是對公眾有益或是客觀的,其話語往往只會圍繞現實權力中心展開,這使得共同利益的需求可能無法得到反映,“傳媒話語的操控性干擾了大眾意見的自由競爭”。此時,許多以“公眾”名義制定的決策,只在被制定出來之后通過媒體發布才被公眾知曉。在更大程度上,公眾僅僅是媒體設置好議程的被動接受者,而無主動建構議程、影響決策的機會。鑒于互聯網大眾傳媒發布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受眾范圍遠遠大于傳統大眾傳媒,真實公眾意見被影響或干擾的程度和范圍可能更廣。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保證通過互聯網所收集的“意見”是公共意見的真實反映,提煉公眾真正的意見也變得更加困難。如此,依據受影響的、不真實的公眾意見所制定的法律也難以獲得公眾的認同。不得不說,這一隋況完全背離了“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所追求的目標,是立法公眾參與的“異化”。
其次,確保公眾通過網絡表達的意見是經過理性論證的也不容易。價值判斷或者意見表達如果想要獲得合理性的內涵,不能僅僅依靠擺明立場,更需要理性的論證才經得起推敲、才能獲得公眾或立法者的認同。然而,由于互聯網意見表達的即時性、快捷性(如互聯網平臺對發言的字數限制)、意見表達的低門檻和主體的多樣性,意見表達的理性論證過程容易被忽略,或是意見表達的主體本身不具備對立場進行理性論證的能力。如此,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偏激且缺乏論證的觀點就可能混雜在經過理性論證的合理公眾意見之中。提取真正有價值的公眾意見表達就更加困難,在法律中體現合理的公眾意見也更不容易。
綜上所述,雖然“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有著成本低、受眾廣、使用便捷等顯而易見的優點,但其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弊端。因而,必須要采取措施應對其缺點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互聯網+公眾參與”的優勢。
五、“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的完善構想
(一)避免孤立地使用互聯網技術進行意見征集
正如上文所言,互聯網中的公眾意見存在被大眾傳媒誤導的可能性,其客觀真實性并非是完全絕對的。因而,僅僅依靠互聯網中的意見表達進行立法是不具有全面性、不理性的。也就是說,雖然通過互聯網征集公眾意見十分便捷且高效,也不能因噎廢食而忽略了傳統的立法聽證會、座談會。通過多種意見征集渠道的同時采用,便可以在優勢互補的同時合理地將各渠道獲得的公眾意見加以比較和對照,進而最大程度上避免立法的公眾參與受到不良公眾意見的影響,使得立法成果真正反映公眾的意志。
(二)“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的規范化
針對上文所提到的互聯網中的意見表達缺乏合理論證的問題,將“互聯網+公眾參與”制度化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可嘗試通過立法的形式,合理設定公眾參與渠道和理性表達的論證要求。同時,還應當考慮設立意見的過濾機制,對意見表達設立一定的“準入標準”。通過這一標準對缺乏理性論證、過于情緒化等不符合法定標準的意見予以排除,進而提升立法過程中采納的公眾意見的質量及合理性。此外,由于立法征集意見活動具有一定特殊性和專業性,應當規范選擇立法意見征集網絡平臺。直接通過娛樂性較強的社交媒體征求意見是不可取的。立法者應追求意見征集網絡平臺嚴肅性和易用性的平衡,使得公眾能夠在便捷表達意見的同時不至于被網絡平臺內的無關內容所影響。
六、結語
綜上所述,立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不僅是我國相關法律和政策所提倡的,也是提升公民對法律的認同感、使立法質量適應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傳統的公眾參與形式存在種種缺點,而互聯網在立法公眾參與中的應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傳統方式的不足,使得立法公眾參與的受眾更廣、參與方式更簡便、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更高。當然,“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也存在其弱點,如意見缺少理性論證、大眾媒體對公眾意見的影響可能被放大而導致意見不真實等。所以,可以探索通過多種方式的共同運用、將“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規范化來應對其弊端,以期達到“互聯網+立法公眾參與”的最大化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