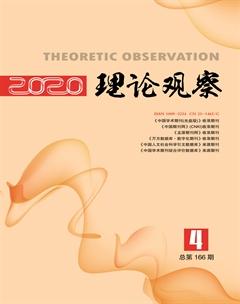基層政府扶貧執(zhí)行的主動(dòng)與被動(dòng)
況偉 何濤
關(guān)鍵詞:產(chǎn)業(yè)扶貧、鄉(xiāng)鎮(zhèn)政府、雙重角色、被動(dòng)、主動(dòng)
中圖分類號(hào):F323.8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 — 2234(2020)04 — 0070 — 04
一、問題的提出
脫貧攻堅(jiān)是有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和明確任務(wù)目標(biāo)的。中共十九大報(bào)告指出,堅(jiān)決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確保到2020年我國(guó)現(xiàn)行標(biāo)準(zhǔn)下農(nóng)村貧困人口實(shí)現(xiàn)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產(chǎn)業(yè)扶貧是精準(zhǔn)扶貧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脫貧之基。正如阿馬蒂亞?森認(rèn)為,貧困是對(duì)基本的可能能力的剝奪,發(fā)展所關(guān)注的是擴(kuò)展人們的“可行能力”以享受他們所珍視的生活〔1〕。產(chǎn)業(yè)扶貧試圖激發(fā)起貧困戶的內(nèi)生動(dòng)力,提升貧困群眾的生產(chǎn)能力,增強(qiáng)自我造血功能,從根本上幫助貧困戶改善生活、擺脫貧困,同時(shí)消除已脫貧戶的返貧風(fēng)險(xiǎn)。由此,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執(zhí)行的落腳點(diǎn)最終還是在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上面千條線,下面一個(gè)針。”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國(guó)家政權(quán)的神經(jīng)末梢,直接面對(duì)基層農(nóng)村。在執(zhí)行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過程中,鄉(xiāng)鎮(zhèn)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鄉(xiāng)鎮(zhèn)政府需要對(duì)上級(jí)政府負(fù)責(zé),貫徹上級(jí)扶貧政策,完成上級(jí)布置的各項(xiàng)扶貧任務(wù),是中央和上級(jí)政府扶貧政策的被動(dòng)接受者;另一方面,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國(guó)家在農(nóng)村依法建立的行政機(jī)構(gòu),承擔(dān)著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改善地方民生,帶動(dòng)貧困戶脫貧致富的責(zé)任,扮演著農(nóng)村基層事物的主動(dòng)管理者。兩種角色間存在著張力,上級(jí)政策接收者的被動(dòng)性與基層農(nóng)村管理者的主動(dòng)性之間、中央扶貧政策目標(biāo)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施政動(dòng)力之間的對(duì)立導(dǎo)致了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實(shí)施過程中被扭曲,給政策效果帶來不確定性。
上述研究給我們理解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角色提供了參考,但也留下了有待于我們進(jìn)一步思考的問題。比如,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雙重角色間存在何種張力?雙重角色如何塑造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扶貧行為?并如何影響到扶貧產(chǎn)業(yè)政策成效?本文以位于江西省某非貧困縣的G鎮(zhèn)為實(shí)證研究對(duì)象,主要分析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扶貧過程中的雙重角色,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通過對(duì)該鎮(zhèn)實(shí)施產(chǎn)業(yè)扶貧的案例研究,分析產(chǎn)業(yè)扶貧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困境,進(jìn)而提出完善產(chǎn)業(yè)扶貧的路徑。
二、理論分析框架 :鄉(xiāng)鎮(zhèn)政府雙重角色下的主動(dòng)與被動(dòng)
鄉(xiāng)鎮(zhèn)政府是建立在農(nóng)村的基層組織,是國(guó)家權(quán)力延伸到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一個(gè)表現(xiàn)〔2〕。鄉(xiāng)鎮(zhèn)作為連接國(guó)家和農(nóng)民的紐帶,在精準(zhǔn)扶貧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角色和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執(zhí)行效果。在當(dāng)前的科層制中,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位于政府機(jī)構(gòu)的最底層,沒有下屬單位,而作為國(guó)家治理農(nóng)村的接點(diǎn),鄉(xiāng)鎮(zhèn)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上級(jí)政策的被動(dòng)接受者,又是基層農(nóng)村的主動(dòng)管理者。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雙重角色之間的張力表現(xiàn)在角色的被動(dòng)性和主動(dòng)性特征。
上級(jí)政策接受者角色的被動(dòng)性,是指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位居政權(quán)層級(jí)的末端 ,自身沒有創(chuàng)制制度的權(quán)力 ,只能被動(dòng)地接受上級(jí)政府對(duì)其社會(huì)角色所做的制度安排和激勵(lì)〔3〕。在層級(jí)制內(nèi),受國(guó)家權(quán)威和責(zé)任約束,下級(jí)政府必須對(duì)上級(jí)政府認(rèn)真負(fù)責(zé)。而自分稅制改革以來,鄉(xiāng)鎮(zhèn)政府財(cái)政收入極大減少,沒有實(shí)質(zhì)性財(cái)權(quán)、人事權(quán)和事務(wù)權(quán),更加高度依賴上級(jí)政府〔4〕。同時(shí),在壓力型體制下,上級(jí)政府通過行政命令、政績(jī)考核、問責(zé)機(jī)制直接影響著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角色作用。可見,鄉(xiāng)鎮(zhèn)政府扮演著政策被動(dòng)接受者的角色。
基層農(nóng)村管理者角色的主動(dòng)性,是指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國(guó)家行政權(quán)力的末梢,不存在下級(jí)單位,國(guó)家政策的落腳點(diǎn)在鄉(xiāng)鎮(zhèn)政府這一層級(j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直接面對(duì)著鄉(xiāng)村社會(huì),代表著國(guó)家治理基層農(nóng)村。鄉(xiāng)鎮(zhèn)政府擁有著國(guó)家權(quán)力,承擔(dān)著改善地方民生、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和實(shí)現(xiàn)公共利益的管理者角色。鄉(xiāng)鎮(zhèn)政府是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者,有著不可替代性。而鄉(xiāng)村社會(huì)是一個(gè)熟人社會(huì),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結(jié)構(gòu)是一種“差序格局”,社會(huì)關(guān)系是逐漸從一個(gè)個(gè)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lián)系的增加,社會(huì)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lián)系所構(gòu)成的網(wǎng)絡(luò)〔5〕。這就更加要求鄉(xiāng)鎮(zhèn)政府主動(dòng)對(duì)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需求進(jìn)行回應(yīng),并提供公共服務(wù)和公共產(chǎn)品。
稅費(fèi)改革以后,鄉(xiāng)鎮(zhèn)政府沒有太多的財(cái)權(quán)和人事權(quán)。產(chǎn)業(yè)扶貧專項(xiàng)資金又多數(shù)傾向于貧困村和連片貧困區(qū)。面對(duì)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獨(dú)立的利益主體和經(jīng)營(yíng)者,也具有追逐自我利益的動(dòng)機(jī)〔6〕。因此,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執(zhí)行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改善當(dāng)?shù)孛裆摹爸鲃?dòng)性”也具有可變性。鄉(xiāng)鎮(zhèn)政府雙重角色的“被動(dòng)性”和“主動(dòng)性”,導(dǎo)致了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精準(zhǔn)扶貧實(shí)踐中呈現(xiàn)出不同的行為特征,進(jìn)而產(chǎn)生不同的扶貧效果。根據(jù)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雙重角色的主動(dòng)性與被動(dòng)性強(qiáng)度兩個(gè)變量,我們可以區(qū)分出四種不同的政策執(zhí)行模式(見圖1)。
1.服務(wù)型模式。當(dāng)政策接受者的角色強(qiáng)化且鄉(xiāng)村管理者的角色強(qiáng)化時(sh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執(zhí)行政策就會(huì)形成服務(wù)型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既要面對(duì)自上而下的績(jī)效考核,努力完成好各項(xiàng)工作任務(wù)并順利通過考核,又要積極回應(yīng)自下而上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各種貧困問題。這種模式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關(guān)注公共利益,還需要結(jié)合地方利益。鄉(xiāng)鎮(zhèn)政府更多的是為村莊提供公共服務(wù),協(xié)助貧困村、貧困戶發(fā)展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并構(gòu)建經(jīng)濟(jì)新主體與貧困戶間的利益聯(lián)系機(jī)制。
2.控制型模式。當(dāng)政策接受者的角色強(qiáng)化且鄉(xiāng)村管理者的角色弱化時(sh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執(zhí)行政策就會(huì)形成控制型模式。精準(zhǔn)扶貧是一項(xiàng)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wù),而產(chǎn)業(yè)扶貧是精準(zhǔn)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級(jí)級(jí)施壓、層層加碼的壓力型體制下,產(chǎn)業(yè)扶貧的各種任務(wù)責(zé)任最終落到鄉(xiāng)鎮(zhèn)政府。由于嚴(yán)格的政績(jī)考核機(jī)制〔7〕和縣級(jí)政府及相關(guān)部門所擁有的集中資金管理權(quán)和人事分配權(quán),鄉(xiāng)鎮(zhèn)政府更加趨向服從上級(jí)政府,為完成考核任務(wù)而追求“短期效應(yīng)”,以效率為追求目標(biāo),即僅僅考慮以最小的成本區(qū)完成既定目標(biāo),優(yōu)先對(duì)上級(jí)政府負(fù)責(zé)。與此同時(shí),基層自治組織村委會(huì)中也存在“半官僚”化現(xiàn)象〔8〕。鄉(xiāng)鎮(zhèn)政府通過壓力傳導(dǎo)來控制村兩委,以此來執(zhí)行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
3.懸浮型模式。當(dāng)政策接受者的角色弱化且鄉(xiāng)村管理者的角色弱化時(sh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執(zhí)行政策就會(huì)形成懸浮型模式。由于中央制定的政策大多較為寬泛,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具體行動(dòng)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地方政府在執(zhí)行過程中擁有著巨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當(dāng)上級(jí)政府對(duì)鄉(xiāng)鎮(zhèn)產(chǎn)業(yè)扶貧的指導(dǎo)或監(jiān)督弱化時(sh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容易選擇性執(zhí)行或敷衍執(zhí)行上級(jí)政策;同時(shí),容易忽視貧困群眾的實(shí)際需求,在發(fā)展經(jīng)濟(jì)過程中大搞政績(jī)工程和形象工程,脫離群眾。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對(duì)考核以外的工作則無暇顧及,消極應(yīng)對(duì)上級(jí)政府考核、消極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扶貧產(chǎn)業(yè)純粹只是應(yīng)付上級(jí)檢查需要,選擇性執(zhí)行,造成扶貧政策的扭曲。
4.理性型模式。當(dāng)政策接受者的角色弱化且鄉(xiāng)村管理者的角色強(qiáng)化時(sh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執(zhí)行政策就會(huì)形成理性型模式。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理性主體,能在客觀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利益的計(jì)算以實(shí)現(xiàn)自身利益最大化。為了獲取自己的利益,它表現(xiàn)出了相當(dāng)強(qiáng)的主動(dòng)性和靈活性,在貫徹執(zhí)行中央和它的上級(jí)政府的方針政策時(shí)帶著明顯的實(shí)用主義的色彩〔9〕。由于上級(jí)政府的政策模糊性,而鄉(xiāng)鎮(zhèn)政府比上級(jí)政府更加了解當(dāng)?shù)剜l(xiāng)村社會(huì)的情況和問題,當(dāng)上級(jí)政府對(duì)鄉(xiāng)鎮(zhèn)工作的監(jiān)督考核減少時(sh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就會(huì)利用信息優(yōu)勢(shì)來給自己留下更多的逐利空間,違背上級(jí)政府對(duì)其角色的期望,以期望獲得更多的權(quán)力衍生品。
三、G鎮(zhèn)產(chǎn)業(yè)扶貧的實(shí)踐
G鎮(zhèn)位于江西省西部,是城關(guān)鎮(zhèn)和工業(yè)園區(qū)所在鎮(zhèn),轄區(qū)有村委會(huì)16個(gè),自然村108個(gè),社區(qū)居委會(huì)7個(gè)。鎮(zhèn)北部為山區(qū),中、南部為丘陵,所屬的Y縣是非貧困縣。農(nóng)業(yè)以水稻為主,經(jīng)濟(jì)作物以黃瓜、花生著名,還生產(chǎn)木、竹、菜油、香菇。G鎮(zhèn)現(xiàn)有人口78617人,其中農(nóng)業(yè)人口19156人。2018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57戶291人,貧困發(fā)生率為1.5%。
(一)服務(wù)型模式:追求共同利益
由于精準(zhǔn)扶貧是一項(xiàng)系統(tǒng)性工程,涉及到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等方方面面。產(chǎn)業(yè)扶貧的開展呈現(xiàn)出運(yùn)動(dòng)式模式。比如,G鎮(zhèn)政府也緊緊圍繞著產(chǎn)業(yè)扶貧來開展脫貧攻堅(jiān)工作,并制定了《2018年G鎮(zhèn)產(chǎn)業(yè)扶貧規(guī)劃》、《G鎮(zhèn)“黨建+產(chǎn)業(yè)扶貧”實(shí)施方案》等。事實(shí)上,G鎮(zhèn)政府在2016年就已經(jīng)意識(shí)到產(chǎn)業(yè)扶貧的重要性,黨委書記X也認(rèn)為花了太多的時(shí)間和精力去整理貧困戶的檔案資料,尤其是“一證一冊(cè)”。到2017年,G鎮(zhèn)分管扶貧的Y鎮(zhèn)長(zhǎng)一直在籌劃著泥鰍養(yǎng)殖,但由于技術(shù)、資金和土地的缺失,最終也沒有弄起來。可見,在上級(jí)政府的相關(guān)政策下,尤其是自上而下的考核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政策的接受者,其角色的被動(dòng)性顯而易見,上級(jí)政府主導(dǎo)著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扶貧工作方向。
G鎮(zhèn)轄區(qū)的16個(gè)村,村集體經(jīng)濟(jì)差異很大,有些村沒有村集體收入,完全依靠政府的轉(zhuǎn)移支付維持運(yùn)作;而有的村通過發(fā)展村集體經(jīng)濟(jì),開發(fā)經(jīng)貿(mào)樓,村集體經(jīng)濟(jì)上千萬。因此,不同的村莊對(duì)于發(fā)展扶貧產(chǎn)業(yè)、帶動(dòng)村集體經(jīng)濟(jì)的需求不一。而且G鎮(zhèn)沒有貧困村,縣里撥付的很多扶貧項(xiàng)目都流向了其它鄉(xiāng)鎮(zhèn)的貧困村。貧困村每年撥付的扶貧資金高達(dá)500—600萬,而G鎮(zhèn)整個(gè)2017年才撥付8萬元,形成鮮明對(duì)比。G鎮(zhèn)黨委書記X一直想發(fā)展部分精準(zhǔn)扶貧產(chǎn)業(yè),但最終受限于資金和風(fēng)險(xiǎn),沒有發(fā)展態(tài)勢(shì)良好的產(chǎn)業(yè)。G鎮(zhèn)政府試圖在執(zhí)行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和回應(yīng)鄉(xiāng)村發(fā)展中找到平衡點(diǎn),為農(nóng)村合作社、鄉(xiāng)村致富能人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提供基本的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wù),并在資金、技術(shù)、稅收上給予一定支持和幫助,創(chuàng)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比如,Z村的村支部書記Y上任前,村里就背負(fù)著幾十萬的債款,屬于典型的村集體經(jīng)濟(jì)薄弱村。因此,發(fā)展村里的經(jīng)濟(jì)、償付完村里的債務(wù)成立Y村支部書記上任后最重要的責(zé)任。2017年,Z村支書Y多次主動(dòng)去其它鄉(xiāng)鎮(zhèn)考察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在考察中發(fā)現(xiàn)黃菊種植產(chǎn)業(yè)見效快、經(jīng)濟(jì)效益高、市場(chǎng)穩(wěn)定、技術(shù)有保障,因此積極與鎮(zhèn)扶貧辦推進(jìn)該項(xiàng)目落地。
(二)控制型模式:追求效率優(yōu)先
精準(zhǔn)扶貧是習(xí)近平總書記簽下“軍令狀”的政治任務(wù),因此也成為自上而下各級(jí)政府都十分重視的中心工作。中國(guó)是單一制國(guó)家,政策執(zhí)行存在級(jí)級(jí)施壓、層層加碼的路徑依賴。精準(zhǔn)扶貧過程中,各級(jí)政府都簽訂脫貧攻堅(jiān)責(zé)任書、立下軍令狀,比如G鎮(zhèn)政府簽下脫貧攻堅(jiān)“軍令狀”,到2018年年底完成貧困人口35人順利脫貧。而產(chǎn)業(yè)扶貧作為精準(zhǔn)扶貧中最重要的扶貧方式,更是成為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在官僚體制中,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國(guó)家權(quán)力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對(duì)上級(jí)政府負(fù)責(zé),特別是縣一級(jí)政府。對(duì)于基層政府而言就面臨著目標(biāo)責(zé)任考核的高壓態(tài)勢(shì)與時(shí)間緊、任務(wù)重的壓力型體制, 產(chǎn)業(yè)扶貧對(duì)基層政府的首要目標(biāo)就是要完成目標(biāo)任務(wù)考核中的客觀化指標(biāo)〔10〕。比如,在2018年每村建成1-2個(gè)5萬元以上的扶貧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每村建立一個(gè)扶貧產(chǎn)業(yè)專業(yè)合作社、所有貧困戶都要求加入合作社等。此外,精準(zhǔn)扶貧在基層政府采取“一票否決制”,凡是沒能順利通過國(guó)家第三方評(píng)估的,都取消鄉(xiāng)鎮(zhèn)年度評(píng)為綜合先進(jìn)的資格。
在控制模式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以效率為導(dǎo)向,以最經(jīng)濟(jì)的方式完成好體制內(nèi)上級(jí)政府的任務(wù),對(duì)上級(jí)負(fù)責(zé)。在執(zhí)行過程中,過于關(guān)注效率,并通過壓力控制來實(shí)現(xiàn)這種效率。無論是發(fā)展具體的扶貧產(chǎn)業(yè),還是成立新型經(jīng)濟(jì)主體,在控制模式下一味追求高效率而導(dǎo)致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執(zhí)行被扭曲,忽視了鄉(xiāng)村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真正需求,合作社淪為“空殼社”,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福利化。
(三)懸浮型模式:規(guī)避多重風(fēng)險(xiǎn)
鄉(xiāng)鎮(zhèn)政府是國(guó)家治理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一方面,鄉(xiāng)鎮(zhèn)政府扎根于鄉(xiāng)村社會(huì),為貧困村、貧困人口提供公共服務(wù),發(fā)展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帶動(dòng)貧困戶發(fā)展生產(chǎn)、脫貧致富,另一方面鄉(xiāng)鎮(zhèn)政府也受到上級(jí)政府的監(jiān)督與考核。盡管是政府主導(dǎo),但發(fā)展產(chǎn)業(yè)需要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相符需要足夠的啟動(dòng)資金來支持、發(fā)展產(chǎn)業(yè)。鄉(xiāng)鎮(zhèn)政府處于國(guó)家權(quán)力的末梢,其財(cái)政收入?yún)T乏,無法為發(fā)展村級(jí)產(chǎn)業(yè)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這就導(dǎo)致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發(fā)展需求得不到滿足,國(guó)家政權(quán)“懸浮”在鄉(xiāng)村社會(huì)之上〔11〕。鄉(xiāng)鎮(zhèn)政府“責(zé)大于權(quán)”且中心工作較多,沒有能力調(diào)動(dòng)資源和人力、物力、財(cái)力等扶貧資源時(shí),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就容易忽視農(nóng)村社會(huì)的利益訴求。比如,G鎮(zhèn)L村地處工業(yè)園區(qū),為了完成上級(jí)的考核指標(biāo),L村村委直接拿出村集體經(jīng)濟(jì)中的一個(gè)店鋪,作為一項(xiàng)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將每年店鋪的租金收益分發(fā)給村里的貧困戶。雖然G鎮(zhèn)完成了指標(biāo)上的考核,但是顯然違背了政府激發(fā)貧困戶的內(nèi)生動(dòng)力的初衷,又回到了“輸血”模式。
鄉(xiāng)鎮(zhèn)政府懸浮在上級(jí)政府與鄉(xiāng)村社會(huì)之間,既不能夠?yàn)猷l(xiāng)村提供好公共服務(wù)、發(fā)展好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也不能實(shí)質(zhì)上的完成好上級(jí)政府的扶貧工作。鄉(xiāng)鎮(zhèn)政府這種懸浮模式,一方面造成貧困群眾的真實(shí)發(fā)展訴求得不到有效回應(yīng),認(rèn)為政府只是在做表面文章、搞數(shù)字脫貧,進(jìn)而對(duì)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不滿,另一方面,人浮于事的工作作風(fēng),扶貧政策不能落到實(shí)處,又導(dǎo)致上級(jí)政府對(duì)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不信任。懸浮性行為背后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規(guī)避整治風(fēng)險(xiǎn)的邏輯。在基層政府,精準(zhǔn)扶貧是一項(xiàng)政治任務(wù),督察多、考核嚴(yán),采取一票否決制。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被動(dòng)性低,主動(dòng)性又低的情況下,就會(huì)衍生出規(guī)避政治風(fēng)險(xiǎn)的邏輯,即不求樹立典型,也不被約談問責(zé)。上級(jí)政府檢查什么,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就執(zhí)行什么。
(四)理性型模式:追求利益最優(yōu)
政府主導(dǎo)的產(chǎn)業(yè)扶貧主要采取“項(xiàng)目制”的運(yùn)作形式 。從微觀層面來說,鄉(xiāng)鎮(zhèn)也是農(nóng)村精準(zhǔn)扶貧的主戰(zhàn)場(chǎng)。而在稅費(fèi)改革制度后,以薪養(yǎng)廉下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自身也面臨著很大的生存壓力。沒有貧困村的鄉(xiāng)鎮(zhèn),既沒有足夠的國(guó)家扶貧資金支持,自身資金又匱乏。當(dāng)上級(jí)政府對(duì)產(chǎn)業(yè)扶貧的推動(dòng)和考核力度緩減時(shí),由于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模糊性與基層農(nóng)村問題的復(fù)雜性、國(guó)家政權(quán)的強(qiáng)制性與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自主性,這給鄉(xiāng)鎮(zhèn)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權(quán)來執(zhí)行政府政策。
鄉(xiāng)鎮(zhèn)政府是國(guó)家在農(nóng)村建立的最低層的政權(quán),是獨(dú)立的利益主體,也是名義上的法人機(jī)構(gòu)。盡管產(chǎn)業(yè)扶貧是由政府主導(dǎo),但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的發(fā)展效益更取決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這套機(jī)制。理性型模式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會(huì)在客觀事實(shí)的判斷的基礎(chǔ)上來執(zhí)行扶貧政策,利用自身對(duì)鄉(xiāng)村社會(huì)更加熟悉的這種信息優(yōu)勢(shì),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規(guī)避潛在的政治、經(jīng)濟(jì)風(fēng)險(xiǎn)。比如,G鎮(zhèn)黨委書記說,我們不去搞那些高大上的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我們就搞些實(shí)際的,有多大的能力辦多大的事。在扶貧資金不足和市場(chǎng)投資風(fēng)險(xiǎn)的分析上,鄉(xiāng)鎮(zhèn)政府采取了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的行為。G鎮(zhèn)政府投資3萬元采購各種果樹苗,分發(fā)給全鎮(zhèn)的貧困戶,由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duì)、幫扶干部在貧困戶的房前屋后空地、菜地及荒地上栽種,發(fā)展庭院經(jīng)濟(jì)。同時(shí),G鎮(zhèn)政府還在幾個(gè)村搞油茶林種植基地,該項(xiàng)目投資小、風(fēng)險(xiǎn)小,但收益又有保證。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的模式下,無論是搞庭院經(jīng)濟(jì),還是搞油茶林種植基地,關(guān)注維護(hù)自身利益而忽視貧困農(nóng)村、貧困人口的發(fā)展需求、解決當(dāng)前貧困的需求,違背了中央期望通過扶貧產(chǎn)業(yè)促進(jìn)貧困村、貧困群眾自力更生、自我能力提高來擺脫貧困的初衷,損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四、余論
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產(chǎn)業(yè)扶貧中表現(xiàn)出的多種行為模式的背后是雙重角色之間的張力。上級(jí)政策接受者的角色要求鄉(xiāng)鎮(zhèn)政府完成上級(jí)政府的績(jī)效考核指標(biāo);而基層農(nóng)村管理者的角色又要求鄉(xiāng)鎮(zhèn)政府回應(yīng)貧困村、貧困群眾的發(fā)展需求,提供貧困戶自我發(fā)展的能力所需的公共服務(wù)。產(chǎn)業(yè)扶貧是精準(zhǔn)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目的是激發(fā)貧困戶的內(nèi)生動(dòng)力,提高貧困戶自身發(fā)展的能力,從根本上幫助貧困村、貧困戶擺脫貧困。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執(zhí)行產(chǎn)業(yè)扶貧政策中成效比較好的是服務(wù)型模式:既貫徹好上級(jí)政府的政策、注重公共利益,又積極回應(yīng)鄉(xiāng)村社會(huì)發(fā)展的問題,統(tǒng)籌好地方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xiāng)鎮(zhèn)政府扮演的兩種角色間的對(duì)立,發(fā)揮出了鄉(xiāng)鎮(zhèn)政府作為國(guó)家政權(quán)治理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接點(diǎn)作用,同時(shí)調(diào)動(dòng)起中央政府和貧困戶的積極性,避免了“一頭冷一頭熱”現(xiàn)象。而其它三種行為模式:控制性模式、懸浮型模式和理性模式,事實(shí)上,在產(chǎn)業(yè)扶貧這個(gè)動(dòng)態(tài)過程中,可以通過構(gòu)建上級(jí)政府,尤其是縣級(jí)政府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合作治理模式,加大對(duì)貧困村、貧困人口發(fā)展問題的回應(yīng)性,及時(shí)糾正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產(chǎn)業(yè)扶貧中的偏差行為,使得控制模式、懸浮模式和理性模式都轉(zhuǎn)化為服務(wù)型模式。正如產(chǎn)業(yè)扶貧不是一個(gè)靜態(tài)的過程,它也不是一個(gè)獨(dú)立的過程,還以其它扶貧措施相關(guān)聯(lián)。鄉(xiāng)鎮(zhèn)政府需要發(fā)揮出接點(diǎn)治理的關(guān)鍵作用,既要縱向連接好國(guó)家權(quán)力與鄉(xiāng)村社會(huì),也要橫向連接好產(chǎn)業(yè)扶貧相關(guān)的各個(gè)職能部門,克服雙重角色間的張力,為貧困村、貧困群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wù)和公共產(chǎn)品。
〔參 考 文 獻(xiàn)〕
〔1〕 阿馬蒂亞·森著.任賾,于真譯.以自由看待發(fā)展〔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2.
〔2〕 何濤.突發(fā)性公共衛(wèi)生事件:政府與公眾的變與不變——從非典到新型冠狀病毒〔J〕.法制與社會(huì),2020,(07):118-120.
〔3〕 饒靜,葉敬忠.稅費(fèi)改革背景下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的“政權(quán)依附者”角色和行為分析〔J〕.中國(guó)農(nóng)村觀察,2007,(04):38-45+60.
〔4〕 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gu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35.
〔5〕 周雪光.運(yùn)動(dòng)型治理機(jī)制:中國(guó)國(guó)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再思考〔J〕.開放時(shí)代,2012,(09):105-125.
〔6〕 榮敬本,崔之元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zhuǎn)變:縣鄉(xiāng)兩級(jí)政治體制改革〔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28-35.
〔7〕 尹利民,項(xiàng)曉華.精準(zhǔn)扶貧中的半官僚化:基于Y縣扶貧實(shí)踐的組織學(xué)分析〔J〕.貴州社會(huì)科學(xué),2017,(09):132-137.
〔8〕 楊善華,蘇紅.從“代理型政權(quán)經(jīng)營(yíng)者”到“謀利型政權(quán)經(jīng)營(yíng)者”——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背景下的鄉(xiāng)鎮(zhèn)政權(quán)〔J〕.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2,(01):17-24.
〔9〕 袁明寶.壓力型體制、生計(jì)模式與產(chǎn)業(yè)扶貧中的目標(biāo)失靈——以黔西南L村為例〔J〕.北京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04):19-25.
〔10〕 朱光磊.當(dāng)代中國(guó)政府過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30-34.
〔11〕 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quán)到“懸浮型”政權(quán)——稅費(fèi)改革對(duì)國(guó)家與農(nóng)民關(guān)系之影響〔J〕.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6,(03):1-38+243.
〔責(zé)任編輯:孫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