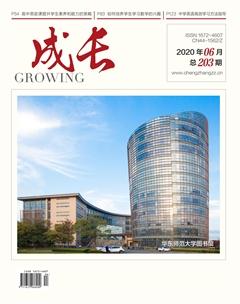魯迅的“吶喊”
趙夢陽
《吶喊》是魯迅先生的代表作,雖是只將那一篇篇《新青年》上發表過的文章集了下來,留到現在,但帶給我們的影響卻更比那時的更多了。而我的體會,也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在我十七年的生命中,《吶喊》已讀過多次。最早的“吶喊”,不過是感受母親談及“蘸人血饅頭”的恐懼;后來的“吶喊”,是我把自己浸入“魯迅體”半月后的一天,突然為其犀利所感染,在筆鋒里呼叫;如今的“吶喊”,則是感受著“迅哥兒”和他筆下的“我”、“祥林嫂”、“單四嫂”、“藍皮阿五”心中的悲憫與哀傷。
我記憶里最深的,仍是《吶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在最開頭就勾勒出這個“人吃人”世界的藍圖,而看這世界的——是“我”。
“我”踢過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我”看了字縫間滿是“吃人“的歷史,“我”發現了原來大家都是兇心、怯弱與狡猾的結合;所有人都在想著吃人,所有人又都怕被吃掉。“我”不愿無所為,那只會被吃;“我”更無意合其流,那終也被吃。于是大家都希望,希望別人勒死自己,再可將骨頭也嚼爛。那是個“道德”為王的世界,但可怕的是,這種“道德”卻是扭曲、變質的,那是個可怕的世界。“我”不禁問,為何吃人?!因為外面是一個只有“道德”的世界,而對“道德”滋養只能用活人的鮮血,因此,有如《藥》中用夏瑜“制作”的紅饅頭,有如《狂人日子》中被說成“瘋了”即可被“吃”的我,有如《祝福》中因寡婦和再嫁就被輪番精神踐踏以至形容枯槁的祥林嫂。一幕幕血腥淋漓的人間慘劇卻令“道德”腦滿腸肥,這何嘗不是恐怖之至,足以令人驚慌吶喊!
可魯迅僅是為此不平而吶喊嗎?
他在《朝花夕拾》中《父親的病》寫道“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我有時竟至于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或許這里的“父親”,并不止他的血肉生父,更包含著那個傳統的變革的中國。“我”在禮教中掙扎,卻也更盼望著這個世界的毀滅,盼望著這個世界真正新生的希望。或許父親真正的病不在身體,而在于錯誤的、騙人的藥方吧!或許中國真正的病不在傳統,而在于那些拯救中國的過程中繞的彎路吧!而這種中國文人獨有的自省與愛意,更是催生出了真正的“吶喊”。
他在反復吶喊著什么?我想,他在吶喊著父親,吶喊著中國人的國民性,吶喊著我們的民族自信!“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是中國的自信,更是中國的脊梁!魯迅的“吶喊”讓20世紀的中國重整旗鼓,誓死保衛河山,而這“吶喊”的余音讓21世紀的我們,鍥而不舍,實現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