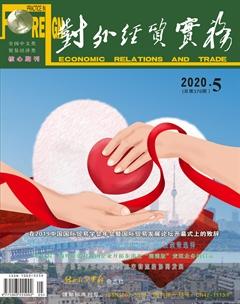歐美貿易救濟調查新動向 對我國3C企業對外經貿的影響
周原
摘 要:中國3C產品生產技術日漸精細,受到歐美國家消費者青睞,使得企業海外效益逐年提高。然而,近幾年歐美國家不斷調整貿易救濟調查方式,強化貿易救濟手段,擴充進口產品限制條款,加大我國3C企業對歐美市場貿易、投資的風險。為此,3C企業應該主動關注貿易救濟調查新動向,并做出相應防御策略。
關鍵詞:貿易救濟調查;新動向;3C企業;海外貿易
3C產品主要是指計算機類、通信類以及消費類電子產品三者的統稱,主要包括電腦、平板電腦,以及數字音頻或者視頻播放器等。近年來,我國3C企業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然而,隨著全球經濟下行趨勢日漸明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對自由貿易帶來嚴重挑戰,使得3C企業對外貿易面臨較大風險。同時,出于對中國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擔憂,歐美國家不斷調整貿易救濟政策,針對中國企業貿易、投資進行遏制與防范。2019年3月,歐盟出臺《歐洲戰略前景》,提出要對中國國有企業、高新技術等領域,采取更加嚴格的貿易救濟手段。美國更是通過實施“301”、“337”等貿易保護條款,加大對中國出口企業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我國3C企業出口歐美市場受到一定限制,不少合作項目被“流產”。因此,探究歐美貿易調查新動向對3C企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可為我國3C企業出口、投資歐美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一、歐美貿易救濟調查新動向
貿易救濟調查是指為保護本國產業發展,針對進口產品發起反傾銷案件、保障措施,以及特保案件統稱。近年來,中國企業出口歐美國家產品數量呈現出急劇增長趨勢,對目的地國家相關產業產生較大沖擊。因此,歐美國家為更好維護本國產業,不斷調整貿易救濟調查相關法律法規。在非市場經濟貿易救濟條款之外,積極構建針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市場扭曲條款,呈現出全新貿易救濟調查趨勢與動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啟用“市場扭曲”標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認定書》第十五條規定,WTO成員在2016年12月11日,終止對中國出口產品反傾銷調查中使用“替代國”數據做法。在此時間節點,歐美國家調整貿易救濟政策,正式啟用“市場扭曲”標準。截至2017年底,大部分WTO成員在反傾銷調查匯總中宣布放棄采用“替代國”做法,但是以歐美為代表的部分WTO成員,主觀將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與“替代國”做法混淆,將“市場扭曲”概念引入到貿易救濟中,加嚴貿易救濟調查審查。
美國依據《1962年貿易優惠拓展法》,對貿易救濟措施進行調整,規定非市場經濟不能適用替代國比價方法,假設進口產品原材料或者加工貿易不能反映生產成本,進口國則需要使用其他算法進行成本計算。因此,代替國比價方法不再局限于非市場經濟國家,而是更多向市場扭曲條款轉型。美國這一規定,在回避非市場經濟國家認定同時,主要針對中國制定新型反傾銷條款。
歐盟在貿易救濟相關法律的修訂中,制度形式與美國貿易救濟制度相似,都是將貿易救濟作為促進本國產業發展的工具,并不是防止外國進行產品傾銷、壟斷的保護性政策。歐盟在修改貿易救濟法時,為規避世貿組織“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將“替代國”做法轉變為“市場扭曲”,并進行國家主導干預貿易救濟政策。“市場扭曲”政策頒布,歐盟表面上強調該政策不針對任何國家地區,屬于正常性貿易救濟政策。但實質上是針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出口歐盟,而實施的貿易保護手段。
第二,增加貿易救濟裁定條款。自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后,為提振制造業、夯實經濟基礎、限制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的沖擊,鼓勵相關機構使用貿易救濟措施來保護本國產業發展。這一做法為美國相關機構主觀制定貿易救濟條款提供了依據。據新浪科技報道,2019年10月8日,美國商務部以“涉嫌侵犯中國部分少數民族人權問題”為由,將海康、大華、商湯、曠視、科大訊飛、依圖、美亞柏科、溢鑫科創,共8家中國3C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這八家企業涉及AI、人臉識別、安防行業,擁有著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尖端科技。此次制裁一出,八家企業股價相應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速度。
歐盟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之一,一直以來都沿用低稅規則進行對外貿易。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本土產業發展受到影響,導致歐盟貿易出口下滑。因此,歐盟各國為保護本國產業,在2018年6月7日,正式頒布以修改低稅規則為核心的2018/825號條例。該條例指出,為保證盟內產業正常發展,需要對低稅規則進行一定程度修改,以提高貿易救濟調查中的征稅水平。根據最新修訂法規,歐盟提出原材料扭曲現象、單一原材料占調查產品比例超過17%、符合歐盟利益等,來決定是否棄用低稅規則保護盟內產業發展。同時,歐盟增加新的產業損害計算法,規定歐盟進口產品需要考慮環保、政府政策實施等隱性成本,一定程度提高我國產品進入歐盟市場的難度。此外,歐盟裁定貿易救濟行為時,認定進口商品對歐盟內部產業造成損害時具有主觀性,會深化損害程度,從而制定較高關稅,影響我國出口企業的經濟效益。
第三,增多外資投資并購限制。2018年,美國政府發布《特殊301報告》中提出,美國本土在技術轉讓和技術當地化,以及私人商業活動中產生“市場扭曲”,使得美國企業向中國企業轉讓有價值商業信息。所以美國政府制定增加中資企業并購相關條款,限制向中資企業出讓技術。同時,2018年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制定《外資風險現代化審查法案》,對外資企業投資審查權限進行擴充,規定任何可能獲取美國關鍵技術、關鍵基礎設施,以及美國公民敏感信息的非控股投資,均需要通過嚴格審核,才能進行投資活動。并且,美國政府認為中國政府指示企業系統性收購美國公司,目的是獲取美國高端技術,所以美國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簽署《外資風險現代化審查法案》,提出投資并購主體需要主動披露信息。
歐盟也積極效仿美國制定新投資審查框架,收緊涉及關鍵技術與行業外資投資并購要求,保護盟內產業。2019年3月5日,歐理會正式通過并實施《外資審查框架法案》。該法案的實施,一方面擴大歐委會對外資并購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提高外資企業對歐盟投資審查風險。另外,盟內國家也積極調整貿易救濟政策。德國內閣通過一項外商監管政策,對歐盟以外投資者在德國投資,制定更嚴格審查制度。這項制度制定擴大跨行業審查適用范圍,首次對“威脅公共秩序及安全”作出界定,要求對于關鍵基礎設施外資并購,需要事先向德國經濟部申報,加大審查力度。
二、歐美貿易救濟調查新動向對我國3C企業的影響
(一)“被流產”合作項目增多
歐美國家為保護3C產業經濟平穩發展,頻繁使用貿易救濟措施,限制相關企業與中國企業開展合作。例如,美國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采取目標傾銷歸零違規做法,把本來沒有傾銷交易認定為傾銷,旨在限制中國3C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使之前很多已經簽署的合作,被迫流產。2018年1月初,美國第二大移動運營商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宣布,禁止銷售華為手機,終止了與華為的合作。1月30日,因美國政府壓力,電信運營商Verizon中斷與華為的合作,停止銷售華為手機。更為嚴重的是,2019年5月,美國政府將華為列入貿易管制“實體名單”之后,美國頂級科技企業,包括芯片制造商和軟件供應商,均中斷與華為合作,停止軟硬件供應。當前歐美國家頻繁發起貿易制裁,加大對中國3C企業限制力度,使“被流產”合作項目不斷增加。
(二)歧視性關稅措施的影響
歐美國家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協定》相關規定,拒絕給中國3C企業分別稅率,加大企業對外貿易成本。例如,美國不重視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定,對我國3C產品采用歧視性做法,計算出畸高傾銷幅度,征收高額反傾銷稅,稅率高達200%,極大地增加中國3C企業對外貿易成本。2018年5月,美國企業對中國耳機聽筒及組件提起337調查申請聲明。這一聲明還表示,美國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進口中國價值500億美元商品增征收25%關稅,其中就包括信息通信產品等3C產品。同時,2021年歐盟電子商務VAT政策進行變革,取消對從非歐盟國家最高價值為24.2美元免征增值稅。另外,歐盟明確規定大型電商平臺上非歐盟企業產品將會增收VAT增值稅。這便意味著我國3C產品,要想在歐洲市場銷售,就需要多付出24.2美元和VAT增值稅,成本大幅度提升。可以說,歐美不斷調整貿易救濟調查提升關稅,增大反傾銷調查力度,使中國3C企業不得不承擔高昂關稅,增大出口成本。
(三)出口額下降
近幾年,歐美國家加大對進口中國產品的審查力度,進而影響我國3C產品出口額。一方面,受中美貿易爭端影響,美國進口商正在積極與越南、泰國等國家進行合作,試圖擺脫關稅對進口中國商品約束,逐漸減少從中國進口3C產品,嚴重影響出口額。例如,2019年7月,深圳Telstar公司美國買家,將大量消費類電子產品訂單轉移到印度尼西亞。深圳iStar公司主要從事生產視頻游戲控制器,也因貿易戰爭引發關稅政策變動,使得美國合作者紛紛與東南亞國家企業進行合作,導致出口美國產品額由90%下降至40%,并呈現出逐年遞減趨勢。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中國3C企業采取“封殺”策略,進一步影響出口額。其中,2019年5月,美國政府動用緊急狀態封殺中國公司,將華為為首的中國3C企業列為“實體清單”,沖擊中國3C產品出口貿易。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1-8月中國高技術電子產品出口與同期相比下降2.1%,液晶顯示面板出口額下降6.6%。
(四)面臨的“雙反”風險增大
中國3C企業在與歐美國家開展貿易合作時,面臨著較大的反傾銷、反補貼風險。據中國國際商會統計,2019年上半年,中國收到的貿易救濟案件中,反傾銷28起,反補貼6起。其中,歐美國家發展“雙反”案件超過50%。可見,歐美國家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案件較為頻繁,加大3C企業的對外貿易風險。同時,歐美國家針對中國發起貿易調查事件時,往往會具有很強主觀色彩,進一步加大3C企業對外貿易面臨“雙反”風險。而我國3C產品在價格和質量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優勢,嚴重沖擊歐美本土產品,極易引起歐美國家發起“雙反”調查。據國別數據網統計,截至2018年底,我國3C類電子產品在美銷售額就超過1700億美元。規模龐大3C電子消費產品出口,嚴重沖擊美國本土耳機企業發展。因此,2018年5月24日,美國BoseCorporation公司依據《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規定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侵權申請,指控中國深圳三家公司在美銷售相關耳機產品涉嫌侵犯其專利權。導致我國相關企業耳機在亞馬遜、ebay、Wish等電商平臺資金賬號被凍結,嚴重影響3C企業貿易中的利益。
(五)迫使企業轉移貿易對象
近幾年,歐美國家逐漸增多對3C企業的限制,更為重要的是很多企業已經終止與我國3C企業的合作,迫使企業轉移貿易對象,將亞洲國家作為新型合作者。據騰訊網報道,美國為維護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動用行政權力禁止美國原材料供應商向華為提供零部件,致使華為5G產業鏈供應受到一定影響。因此,為降低美國禁令對華為經營帶來的風險,中國企業開始逐漸將產品供應鏈轉移到日韓等國。據搜狐網報道,2019年11月27日,華為董事長梁華在日本參會時表示,華為決定從日企供應商采購110億美元3C商品原材料,到2020年預計達140億美元。另據中國商務部報道,歐盟國家對中國企業不信任加劇,導致中國3C企業在歐洲國家的投資受挫。歐美國家不斷加強貿易制裁,迫使3C企業逐漸將合作目光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抵御歐美國家的貿易制裁。
三、我國3C企業應對歐美貿易救濟調查的策略
(一)根據市場扭曲條款本質,完善貿易救濟立法
對于3C企業來說,歐美國家不斷調整貿易救濟調查政策,成為發展對外貿易面臨主要挑戰之一。因此,完善貿易救濟立法,是保障我國3C企業享受公平海外貿易的重要舉措。首先,根據以往貿易救濟調查,預判與貿易伙伴之間可能發生沖突,并將其列入到貿易救濟法保護條款中。其次,我國應該根據國情,制定符合我國企業競爭規則,并借助于“不符合措施”清單,為我國企業改革預留空間和時間,助推我國3C企業“走出去”。再次,針對歐美國家加大投資并購企業審查力度的條款,我國在完善貿易救濟法律法規時,應該規定合約方政府不得隨意干預企業技術轉讓行為,保護3C企業合法權利。最后,針對歐美國家正在形成不利于中國的貿易條款,我國相關立法部門需要把握發展動向,評估可能對我國造成的影響,并制定應對策略,應對歐美國家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
(二)依托專利管理機構,加強企業內部貿易救濟制度建設
近幾年,3C企業開展貿易、投資時,面臨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調查事件逐漸增多,增大了對外貿易的風險。同時,企業進行內部貿易救濟制度建設,應訴能力較弱。所以3C企業應重視貿易救濟調查事件,依托專利管理機構,優化企業專利資產,提升知識產權價值創造力和獲取能力,協調專利糾紛,避免不必要海外訴訟。為能夠及時做好應訴工作,企業應成立專業的貿易救濟應訴部門,全面主動宣傳中國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利用專業的法律手段,增加應訴成功幾率。與此同時,3C企業還應重點警惕美國“337條款”、 “301條款”等損害較強的貿易保護手段,建立相應信息共享部門,利用合法貿易保護手段,做好應訴準備。
(三)積極利用貿易爭端小組,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2019年8月,世界貿易組織同意成立貿易爭端小組,裁定中美貿易之間的摩擦。所以,在應對歐美國家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時,3C企業和政府部門可積極利用貿易爭端小組,裁定歐美國家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事件是否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在發起過程中是否存在違規行為,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同時,為了更好地發揮貿易爭端小組的作用,中國政府、企業以及行業協會應該依據WTO相關規則,積極應對反傾銷、反補貼和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案件。并且針對歐美國家濫用貿易救濟規則,人為裁定較高額稅率措施,中國企業以及相應政府部門應該積極利用貿易爭端小組的作用,對歐美國家存在的違規行為進行裁定,減少我國企業應訴損失。
(四)充分發揮海外投資保險作用,提高企業風險應對能力
隨著歐美貿易救濟調查法律法規不斷調整,3C企業在歐美國家開展對外貿易面臨風險日益加大。因此,3C企業開展貿易時,可以充分發揮海外投資保險作用,將企業經營風險轉嫁給保險機構,增強投資者對企業海外經營信心。海外投資保險承擔貿易國與其他經營主體之間項目協議保險,幫助中國企業規避經營風險,提高貿易便利性。同時,企業可以通過了解貿易國海外貿易投資保險相關細節,根據自身資質結合審批流程,從而申請相應保險。企業還可以根據對外貿易預警和落實情況,進行實時監控,根據不同形勢申請不同屬性保險項目,提高企業風險應對能力。
(五)推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放寬市場準入條件
面對中國與歐美貿易救濟調查事件不斷增多,我國應大幅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吸引更多外資,回應歐美國家“對等開放”需求。具體來說,我國應全面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放寬金融、制造業、電信以及新能源領域的準入條件,進一步深化開放程度,倒逼歐美國家提高貿易自由化水平,減少3C企業合作項目被迫流產數量。同時,我國還應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可通過加快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建設,加強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積極發揮合作區資源聚集優勢,吸引更多外資流入國內。并且,利用外資提供巨大投資機會,優化3C產業鏈布局,推動產業升級換代。在這一過程中,吸引更多歐美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深化開放程度,反向倒逼歐美國家提升貿易自由化水平,為3C企業開展對外貿易營造良好商業環境。
參考文獻:
[1]張悅.全球貿易治理失衡與中國的路徑選擇——以“一帶一路”建設為背景[J].對外經貿實務,2019(8):8-11.
[2]陳清萍,鮑曉華.中國對外反傾銷:實施、測度及趨勢[J].上海經濟研究,2018(5):105-117.
[3]張寧.“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企業在歐亞經濟聯盟面臨的貿易制裁問題[J].歐亞經濟,2017(4):19-30.
[4]王海燕,焦知岳.如何緩解中歐班列“返空”尷尬[J].對外經貿實務,2018(1):38-41.
[5]武雅斌,王勇.樹立合作式國際貿易摩擦解決機制的中國理念[J].國際貿易,2017(3):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