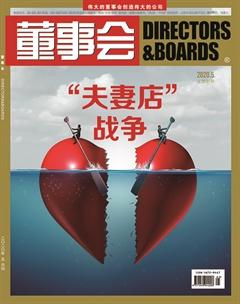董責險保險人有權參與上市公司治理
熊錦秋
自曝造假的瑞幸曾購買了總額2500萬美元保額的董責險,目前是否理賠尚未有定論。由于該案示范效應,4月以來公告擬投保董責險的A股上市公司有58家,超過去年全年。筆者認為,應引導董監高責任險發揮正面作用。
新《證券法》已于3月1日正式實施,第八十五條規定董監高對虛假陳述等需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除非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另外,新《證券法》對虛假陳述的行政處罰條款更為嚴厲,且規定了中國特色的集體訴訟制度,民事索賠金額可能巨大,且更容易落實。瑞幸案例提醒了A股上市公司董監高關注自身履職風險,由此董監高責任險開始有興起勢頭。
董監高責任險是由上市公司掏錢為其購買的保險,最終出資人其實是股東,若董監高上了責任險,放下思想包袱全心全意開拓經營,這無疑是股東愿意看到的結果;但若董監高以責任險為后盾,放膽參與財務造假等違法違規,欺詐股東,那么董監高責任險就會成為庇護違法違規的擋箭牌,可能抵消新《證券法》等對違法違規董監高的威懾效力,而這正是目前市場人士所擔心的。
美國保險法學界曾提出保險治理理論,認為保險能夠行使準政府職能,保險人可作為私人監管者。事實上,保險人是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如果被保險人不出險,保險人就沒有賠付壓力,基于這個原因,保險人有動力監管被保險人的行為。比如,美國安德魯颶風造成巨大損失,這使保險人認識到,為被保險人提供損失預防服務有助于自己獲得更好回報。
回到董監高責任險領域,如果保險人能引導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對董監高違法違規苗頭及時提醒、防微杜漸,就可以防止出現更為嚴重的違法違規,避免將來面對投資者的巨額民事索賠訴訟風險。因此,建議對A股上市公司董監高責任險保險人,應明確其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權利。事實上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被保險人應當維護保險標的安全,保險人可對保險標的的安全狀況進行檢查,及時向投保人、被保險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隱患的書面建議。
按該條精神,既然保險人承保上市公司董監高責任險,當然不能放任董監高造假等違法違規行為,坐等股東來索賠,而應防范于未然,以避免將來可能面臨的巨額民事索賠風險。保險人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權利,應在《證券法》等法律中予以明確,參與手段主要是善意提醒董監高,其自身存在哪些不足、或上市公司存在哪些治理缺陷,并提出對策建議,對于輕微違法違規還可向證監部門舉報,防微杜漸。
為防范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保險人還可采用風險定價,比如對高風險的被保險人收取高保費,反之則降低保費;另外,保險合同中可設計責任免除、免賠額和賠償限額等條款。事實上,目前對于發行人財務造假等故意違法行為,一般不屬于保險合同的承保范圍;但要確定是否屬于除外承保范圍,保險公司必須得到“最終且不可撤銷的判定其為故意行為”時才能啟動除外條款,而這往往需要以監管部門處罰決定書或司法部門的有罪判決書為準。

新《證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了對證券違法的行政和解程序,若當事人賠償有關投資者損失,證監部門可終止調查。行政和解由于沒有最終的行政認定程序,是否構成故意違法違規,沒有權威結果,這種情況下保險人只能承擔約定的賠償,而董監高則可逃避賠償。因此,對于已經上了董監高責任險的上市公司,若上市公司及有關當事人涉嫌違法違規,就不宜適用行政和解程序,證監部門對違法違規行為可作出行政認定,以厘清各方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
當然,要讓董監高責任險制度發揮作用,關鍵是要將董監高的民事責任落到實處。此前的一些虛假陳述案件,投資者一般只是把上市公司列為被告,很少將連帶責任人董監高也列為被告;另外《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條雖然規定董監高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但對勤勉義務的內容并未明確,投資者就很難以董監高違背勤勉義務來索賠。
因此,建議《公司法》應明確董監高勤勉義務的具體內容,另外投資者及律師也應逐漸改變維權習慣,對虛假陳述要更多追究相關董監高責任,真正實施侵權的是董監高而非上市公司,讓上市公司來賠償,也等于股東割肉給自己吃,意義不大。
——兼評《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42條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