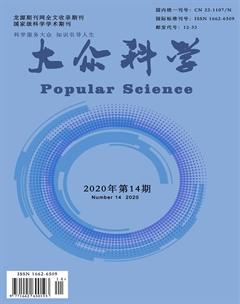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影響因素探析
鄭潔穎 何婉莊 黎淑芹
摘 要: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方面改革的熱點問題,是土地資源配置優化的重要途徑,可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促進經濟轉型,意義十分深遠。文章主要通過介紹佛山市南海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基本情況,然后根據南海建設用地入市的基本情況分析其入市的影響因素,并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政策的優化機制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建議或意見。
關鍵詞: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影響因素;優化機制
一、前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城鄉二者發展較好的同時,城鄉差距卻逐漸拉大。此外,土地市場的不斷發育,國有土地使用制度和農村用地的相關制度愈加完善,使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改革的必要性大大加強,以減少因城鎮化與建設用地間的矛盾、農村土地資源利用不合理、農村居民收入利益分配不當、農村產業及經濟發展緩慢等帶來的問題。為順應時代發展給土地帶來的改革潮流,國家制定并不斷改善土地制度并得到發展,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也使得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規范入市一步步得到實現。在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聯合印發關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試點工作的意見,宣布在全國范圍內挑選出 33 個縣市區進行探索實施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其中包括廣東南海、廣西北流等。廣東南海作為廣東唯一一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試點,具有極大的參考意義。本文將從廣東南海的整體概況,從政策、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推導和制約因素,深入分析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影響因素,并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相關建議。
二、南海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基本情況
(一)南海區概況
佛山南海區位于廣東省的中部,屬于粵港澳大灣區腹地,南接佛山順德區,環抱佛山禪城區,毗連廣州市,靠近香港、澳門、深圳等地區,地理區位優勢明顯,土地價值較高。全區總面積為1073.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91萬[10]。南海區共有 2031 個經濟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約 30 萬畝,占全區建設用地總面積 38%。2019年,南海區GPA達3176.62億元[11],連續6年位居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區排行榜第二名[12],綜合實力較強。
(二)南海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發展過程
土地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載體,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南海區作為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腹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流轉入市工作起步也比較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南海進行改革,逐步以經濟社制代替生產隊制;在90年代的“大搶建”后,南海的產業出現“量大、分散、低效”的情況,嚴重阻礙了其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建設[1]。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求開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2014年,南海區政府出臺了《佛山市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實施辦法》,該辦法的出臺使南海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入市流轉取得了較大的突破。2015年初,佛山南海區被授權為全國33個探索試點之一。
在一系列的背景下,南海區抓住契機,開展了一系列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探索。
在被確定為試點地區后,南海區政府積極探索,先后出臺了《入市管理試行辦法》、《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與稅費征收使用管理試行辦法》,逐步構建起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政策體系。隨后的幾年時間里,政府結合先前的土地制度改革實踐經驗,學習其他試點地區的先進辦法,從入市監管、抵押融資管理、產權登記管理、租賃住房管理等方面完善政策體系,為南海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入市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南海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現狀
(1)南海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面積考察。
據網絡數據調查和實地勘測,筆者對南海的用地面積進行摸查,結果顯示: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面積約達304平方公里,其中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面積約達171平方公里,約占集體建設用地總面積的56.25%[2]。
(2)南海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入市成果。
近幾年,南海區抓住試點契機,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進行了探索,并逐步構建起一套“1+N”的入市試點政策體系,全方位落實指導試點工作。
2016年初,南海首宗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政策執行的地塊交易成交入市,標志著南海的改革試點工作進入了實操階段。據統計,2016年12月止,南海區共完成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42宗,面積約1670畝,總成交金額約36億元。2017年8月止,共完成集體建設用地入市71宗,面積約2162畝,總成交金額超過58億。2018年8月止,共完成集體建設用地入市88宗,面積約2471.7畝,總成交金額達70億[13],交易的項目數量和成交金額位居33個試點地區的前列。由此可見,在試點政策體系的支持下,南海區集體性建設用地入市在穩步進行,項目數量不斷攀升,所覆蓋的集體土地面積也在逐漸擴大。
從實地訪問調查結果可知,南海區的村民們紛紛享受到試點改革帶來的紅利,股份分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極大的改善了生活質量。以大瀝鎮星港城項目為例,該地塊所屬經濟社成員每年的集體土地股份分紅已經超過40000元。
(3)南海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亂象。
早在2014年,南海區政府印發的相關文件中就規定:“通過流轉方式取得的集體建設用地不得用于建設住宅或類似住宅的居住用房,也不得將地上已有的其他用途用房改為居住用房”。但隨著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入市改革逐步深化,許多開發項目卻違反規定,出現“違規商改住”的亂市現象,即一些原本為商業服務性質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項目,在竣工驗收后,違規改建了公寓銷售,擾亂了市場秩序,造成了大量不知情業主們的損失。出現這一現象背后,反映出作為市場主體開發商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因為開發商會根據市場需求而選擇違規商改住,這是市場主體逐利行為,但是入市項目數量巨大,政府監管仍存在難處[14]。筆者認為,該現象反應出南海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中存在著監管的漏洞,若不加強監管,就會有更多無辜的業主為這種亂象買單,造成更大的損失與更多企業以此失信。
三、南海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對南海區的調查,本文主要將影響入市的因素分為誘導因素和約束因素進行分析。其中誘導因素的影響主要分析經濟發展以及所處區位等的因素影響,而約束因素影響主要分析法律定位模糊、產權主體不明晰以及入市收益分配存在分歧的影響。
(一)誘導因素的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的持續發展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交易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居民開始向經濟水平高、基礎設施配套較為完善的城鎮或城市地區聚集。人口的聚集為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必然會帶來勞動力成本降低,降低工業生產成本,并推動服務業的發展,[3]不斷促進企業的發展,從而增加對土地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在《人民日報》公布的2019年中國中小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數研究成果中,佛山市南海區再次強勢上榜2019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區,并連續第六年蟬聯全國第二名。南海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使這里形成了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與市場發育基礎,吸引了眾多投資、創業者,用地需求大大增加,而集體建設用地的靈活利用方式與相對較低出讓或租賃價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地者的前期成本,使其更樂于選擇使用集體建設用地。[4]
2、區位因素
首先,佛山市南海區位于廣東省中部,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其東部地區與廣州市中心城區相連,地理位置優越,而這優越的區位使其易于接受廣州市的輻射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基礎好,集體土地流轉的數量及其帶來的經濟效益更為明顯。[5]為了增強區域競爭力,2009年3月19日,廣州市和佛山市簽署了《廣州市佛山同城化建設合作框架協議》并頒布具體政策措施。而且南海區位于廣佛交界地帶,是廣佛同城化的核心區域,在同城化的背景下可以創造更多優良的經濟發展機遇,吸引更多的人才資源,促進該區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從而不斷推動南海的經濟快速發展,增加對土地市場的需求,促進土地的交易。
其次,由于南海區臨近廣州、香港、澳門等地,受到城市的輻射作用較強,產業發展速度較快,交通運輸十分便利,因此其建設用地需求量大。
(二)約束因素的分析
1、法律定位上的模糊
2019年 8 月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以下簡稱“新法”)頒布,在涉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法律制度中,刪除了原法第43條關于“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必須使用國有土地”的規定。雖然新法從法律層面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消除了法律障礙,結束了多年來集體建設用地不能與國有建設用地同權同價同等入市的二元體制,但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使用權在現行法律上依然定性模糊。《物權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客體是國有土地;新法的第六十三條與第六十六條都提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但這并不能代表可以將《物權法》中有關“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涵義應用于新法中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即使在中央關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文件中,多處可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用語,但至今也沒有現行法對其進行法律定性。
包志會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面臨的現實障礙”的分析中[6]提到入市主體呈現多樣化的原因在于農民集體在現行法律上定性模糊,農民集體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也沒有法律法規予以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法律定位模糊,一方面不能有效地優化配置農地資源,阻礙入市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會導致一系列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例如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使用權發生爭議時,法院在判決中不管是引用《物權法》中關于“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定,還是引用新法中有關“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規定,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現行的立法不僅沒有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有明確的法律定位,也沒有設計出較為明朗的法律規則。[6]因此這也導致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入市進程十分緩慢,不能達到明顯的效果,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力度還需加大。
2、產權主體不明晰
根據我國目前《土地管理法》的第十一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據此規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所有權屬于集體,而“集體”是一個由農民組成的社會團體,而這種社會團體由于不健全的產權制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加上權利的被限制,會導致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因其主權不明而具有較小的流動性。[3]
同時,現行法律也沒有明確具體指出“集體”所指誰,在 《憲法》和 《土地管理法》 法律層面和各試點地區的入市實踐中都不夠明晰,甚至有些地區存在直接混淆土地所有權人和使用權人的情況。因此產權主體不明晰會嚴重影響入市交易,農民的利益也難以得到保障。
3、收益分配存在分歧
自2015年南海被確定為33個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試點后,試點工作的開展給南海區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尤其是伴隨著農村集體經營性用地入市而帶來的大額土地增值收益,使得南海農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而農村集體(經濟社)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所有者,所以收益分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工作的順利開展。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收益分配,實質上就是對其增值收益[15]的利益分配。然而,通過調查可見,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實操過程中,由于涉及的利益分配主體較多,各方對于收益分配主體問題仍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社)和政府之間的收益分配矛盾問題。
農村集體(經濟社)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所有者,毋庸置疑要享有收益分配的權利。而作為政府主體,正如劉燕銦在“政府—農民集體—土地使用者”的博弈分析[7]中提到地方政府在土地入市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保證政府在市場中能發揮好管理者職能的均衡狀態,使得政府在管理工作中所耗費的成本得到經濟補償,所以政府參與到集體經營性用地入市的收益分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博弈分析中也提到,若政府參與收益分配的比例不合理,就會導致農民集體獲得的收益過少,從而容易出現土地隱形交易行為的發生,擾亂試點改革的秩序。
綜上,在土地收益分配的主體問題上,社會上仍存在著較大的分歧意見,如何在保證村民及村民集體的利益受到保障的同時處理好政府財政問題,制定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依舊是試點工作需要努力改進的方向。
四、南海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解決對策
(一)加強入市制度在法律上的建設
面對相關法律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之處,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應該加快完善入市制度的進度。國土資源部公開向公眾收集《土地管理法》修改意見,將《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修改為“國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采取出讓、租賃、作價出資或者入股等方式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并簽訂書面合同”,這也成功創立了屬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物權權能,強化了農民對于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權屬。然而農村集體組織依舊沒有完全具備獨立法人的資格,因此集體組織尚未享有的經營權利應該要有詳細的法規制定。[8]
同時,法規制度中的農民土地范圍應該進一步明確。農村閑置宅基地、廢棄地等整理節余出來的建設用地是否符合規劃前提,在入市經營性建設用地范圍之內,并無政策或法律界定相關概念。[9]因此,要使得入市過程中入市土地范圍的明確,解決因土地范圍帶來的農村征地的沖突,相關概念一定要足夠精確,才會使后續建設用地的開發、農民收益分配的合理帶來契機,減少紛爭。
(二)完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產權制度
《土地管理法》中提及到的所有權人為“農民集體”,關于此概念,國家應該更明確地表述出“集體”一詞的詳細意義,落實到每一個集體組織的每一類人身上,確保每個人的自身利益都受到制度保障,避免引發所有者、使用者、政府多方共同矛盾。所有權主體和使用權主體要分清,才能使雙方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減少紛爭。南海政府也需給予相關的補助和支持,使所有權主體和使用權主體兩者合作,在獲取自身利益的同時,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此外,應在試點地區首先實行一系列的推廣措施及管理條例,讓農民在建設用地入市過程中更加了解流程和相關法律,更加清楚地知道產權主體是何者,為農民能得到合適的、公平的收益打好基礎,使得入市整個進程更加順暢。
(三)健全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
收益分配制度的是否合理,決定農民收益是否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農村經濟是否能得到更好的發展。因害怕收益分配有分歧而不敢進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鄉村有不少,因此做好分配工作是重點,其核心在處理好國家財政、縣鄉鎮府、農民集體組織成員、農民個人的收益分配比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根據參與利益分配者可將其劃分為內部分配和外部分配。[3]
內部分配主要指農民集體內部成員之間的收益分配。其主要包括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重點是處理好雙方的收益分配比例,農民集體組織成員制度的完善也必不可少,這也是分配依據之一。
外部分配主要指國家財政、縣鄉政府與集體之間的利益分配。縣鄉政府在入市過程中的參與,包括部門介入走訪、多方面交談、基礎設施建設等,所以政府也是參與利益分配者之一。國家財政方面,可分配一部分收益,通過稅收體制來體現,保證國家財政的同時,也體現了公平性和均衡性。
五、結語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我國在土地制度建設升級過程中的一大舉措,它打破了我國原有的城鄉土地二元結構制度。其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支持,同時又是緩解城鎮壓力,使得城鎮發展走向新形式的新起點。盡管在發展中有出現過一些約束問題,如法律制度不完善、產權主體不明確、收益分配有分歧等,但是這會隨著我國不斷創新改革而逐漸得到解決,最終會提高我國農村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使人民過上美好生活。
參考文獻
[1]陳海素.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困境——以廣東省南海區為例[J].廣東土地科學,2017,16(02):9-11.
[2]李松杰.以重點示范項目帶動農村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以佛山市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改革為視角[J].廣東經濟,2017(05):20-23.
[3]劉冬鳳.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影響因素研究——以浙江湖州為例[D].浙江:財經大學.
[4]葉紅玲.探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新模式——廣東南海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觀察[J].中國土地,2018(07):4-9.
[5]李春江,賈莉.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問題研究——以佛山市南海區為例[J].鄉村科技,2019(24):41-43.
[6]包志會.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現實障礙和破解路徑[J].廣西質量監督導報,2019(09):78+69.
[7]劉燕銦. 南海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流轉收益分配研究[D].華南理工大學,2015.
[8]陳旻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困境及對策研究[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8,29(11):49
[9]李清華.我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問題研究[J].科技博覽,2018,13:197
[10]數據來源:http://www.nanhai.gov.cn 南海區人民政府官網
[11]數據來源:http://www.foshan.gov.cn/gzjg/stjj 佛山統計局官網
[12]數據來源:http://www.csmcity.com 中國中小城市網
[13]數據參考來源:搜狐新聞
[14]規范監管下暗生“灰色地帶”佛山南海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項目溯源,來源:中國經營報
[15]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增值收益是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后產生的入市總收入扣除原先土地的取得成本和土地開發成本后的凈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