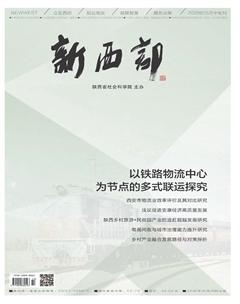美國西裔社會經濟生活問題研究
【摘 要】 本文從社會學、歷史學角度對西裔美國人三大主要群體包括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古巴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經濟生活情況進行了研究。
【關鍵詞】 美國;西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波多黎各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
西裔美國人亦被稱為拉美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或者西班牙語裔美國人。它是由來自西班牙或者其他西班牙語國家的人及其后裔組成的少數族裔群體。中國學界一般稱之為西班牙裔或者西裔美國人。按照美國普查局對西裔的定義,西裔是指“居住在美國,但在西班牙出生,或在講西班牙語的或其文化淵源于西班牙的拉美國家出生的人。”[1]根據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到2010年4月1日為止,美國總人口為3.08億,少數族裔的人口為1.11億,占全國總人口的36.3%。其中西裔人口為16.1%。”[2]西裔美國人在美國人口的快速增長促使了人們對于其在美國社會政治、經濟和學術上的關注。
一、西裔美國人整體社會經濟狀況
西裔美國人將在不久的將來在美國少數族裔中占主導地位,取代黑人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西裔人口的逐年增加不僅為美國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而且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但他們的生活水平卻一直落后于白人處于社會的底層。2003年美國普查局的調查顯示:“25歲以上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成年人口數量,白人為89%,亞裔為88%,非裔為80%,而西裔僅為57%。具有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的白人占30%,亞裔為50%,非裔為17%,而西裔則僅占11%。”[3]而且西裔學生的流失率也很高,2000年高中平均流失率為12.4%,西裔美國人高中流失率則達32.4%。這些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在增長,并且生活在貧困中。對于西裔人口的教育迫在眉睫,因為當前這一代的西裔美國人所獲得的教育的數量和質量將影響西裔美國人未來可從事的職業和所獲得的收入。對于大多數西裔美國人而言,受教育程度仍然是經濟和職業發展的核心與關鍵。“在1981年,年齡在18歲和19歲的西裔學生中有36%屬于高中輟學,而白人為16%,黑人為19%。同年,西裔16歲和7歲學生的入學率為83%,而黑人和白人約為91%。從1970年到1983年,完成了四年或四年以上高中教育的25-34歲的西裔美國人從45%增至58%,而非西裔美國人則從73%增至88%。”[4]因此,西裔美國人與非西裔美國人的教育程度之間的差距仍然存在。造成這一教育滯后的因素包括:貧窮;大城市學校的學生數量過多且設施不完善;對于深色皮膚的人的歧視。同樣,西班牙語的使用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從受教育程度低下到總體勞動力中的經濟地位低下只是一小步。西裔美國人的就業傾向于集中在低薪的藍領和半熟練工作中,這些領域包括建筑業或制造業,伴隨著季節性或周期性失業。在1981年,只有8%的墨西哥裔男子被錄為農場工人,是美國所有男性工人的4%的兩倍。未來的顯著改善將要求西裔美國人的教育程度迅速提高,以縮小差距。從總體上說,西裔人口的增長速度快,大多聚居在美國的西南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等方面都落后于非西裔。
二、墨西哥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生活
墨西哥裔美國人也稱為“奇卡諾人”,是當今美國最大的單一移民群體,也是西裔美國人集團中人數最多的民族群體。1846年美墨戰爭結束后,美國接管了墨西哥北部,其包括今加利福尼亞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猶他州,科羅拉多州的一部分,以及德克薩斯州。使原本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墨西哥居民,由墨西哥人轉變為墨西哥移民或者墨西哥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成為美國西南地區最早的定居者。由于缺乏其他資源,德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亞利桑那州的主要行業嚴重依賴墨西哥勞工。“墨西哥裔在鋪設鐵路線,修建道路和灌溉系統,清理刷子和灌木叢以準備耕種土地的方面,占據了大量的體力勞動。他們也是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銅礦以及德克薩斯州牛群的主要勞動力。”[5]墨西哥裔美國人由于語言不通、受教育程度低或者從事的勞動技術不熟練,所以美國西南部的墨西哥裔美國人在早期從事商業性農業、采礦和鐵路等勞動并受雇于水泥、鋼鐵、汽車生產以及食品加工和牲畜屠宰等行業。墨西哥裔美國人一直處于社會的底層,除了忍受雇主的歧視和工會的敵意之外,墨西哥裔美國人通常也成為最先被解雇的群體。墨西哥裔美國人對與自己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也在積極尋求改善這一局面的方法。不斷勝利的黑人民權運動也讓墨西哥裔美國人在1968年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奇卡諾運動”,開展了包括罷工游行,要求提高墨西哥勞工工資和待遇等一系列的運動。努力斗爭的結果讓墨西哥裔美國人的經濟狀況有了巨大的改善。
三、波多黎各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生活
其他主要西裔群體的歷史經歷沒有墨西哥裔美國人的經歷那樣五花八門,但又是不同于其他群體的。如果算上波多黎各裔美國人與美國東部間的積極移民活動,波多黎各裔美國人就有很長的歷史。這種模式往往是男性離家來到美國大陸尋找就業機會,并將錢寄回家里。1917年美西戰后,隨著波多黎各被美國合并,這種模式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因此,許多波多黎各裔美國人搬到城市中心來長期居住,如波士頓、紐約、邁阿密,在那里他們在工作和住房方面遇到了歧視,不得不在貧窮中掙扎生存。這些移民中許多是政治避難者,試圖逃避國內的政治迫害和武裝沖突。西裔美國人的貧困率是很高的,特別是波多黎各裔美國人等群體。這似乎與以下兩個因素有關或是部分有關。一方面,較高比重的波多黎各裔美國人住在城市,從事著低收入的全職工作,兼職工作,或根本沒有工作。比如在紐約,一開始,城市提供了大量幾乎不需要技術和教育的工作;但這些制造工業都已經離開了紐約。另一方面,相對于其他的西裔,更多的波多黎各裔美國人建立家庭時,并沒有從婚姻中獲益。結果就導致了較高比率的沒有丈夫、由女性維持的家庭的出現。這兩種因素,即父母工作模式和家庭結構婦女主導的家庭與貧困相關。有研究者以西裔孩子為例對此進行了考察。如果嚴格地以經濟幸福感為尺度,波多黎各裔美國人和黑人孩子為“家庭破裂”付出的代價很高。單是家庭結構的不同,就貢獻了波多黎各裔美國人和白人孩子的貧窮差異的55%,如果綜合考慮家庭結構與父母的工作模式,就可以解釋孩子貧窮差異的78%。父母沒有工作,波多黎各裔婦女較少外出工作,這都進一步加劇了兒童貧窮問題。不幸的是,工作不僅對波多黎各裔婦女是一個問題,對男性一樣。相對于非西裔白人和其他西裔美國人來說,波多黎各裔男性外出就業率較低,并有更高的失業率。“這種危險的經濟情況,對波多黎各裔男性的婚姻解體和非婚生育率偏高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6]此外,結果還強調了就業在父親撫養孩子的能力中的關鍵作用。父親并不愿意放棄對下一代的責任,而是沒有能力負起經濟責任和照顧孩子,特別是對居無定所的父親來說。
四、古巴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生活
古巴裔美國人北遷美國已經有悠久的歷史,但促使他們逃離古巴通常是政治原因。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古巴人為尋求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來到美國。1868—1878年的獨立戰爭和1895—1898年獨立戰爭,以及20世紀初期共和國的經濟窘境、激進的政府和政權的變化。使大量的古巴人離開自己的祖國,遷徙到美國。當時正處于冷戰對峙時期,在反蘇反共思想的指導下,美國把接受古巴移民作為對抗蘇聯的一種方式。由此,古巴人憑借“政治難民”的特殊身份在這一時期受到了美國大眾的關注、支持以及救援。例如:美國的“古巴難民計劃”,不僅為古巴移民在美國的就業和經營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而且還對古巴移民進行就業培訓和商務經營培訓。[7]這一寬松的社會環境為古巴移民在美國取得成功提供了前提條件。此外,早期的古巴移民多為古巴上層名流階級人士,他們在逃離古巴時攜帶了大量的資金,這些財產和資金就成為了他們的創業基金,確保了他們在“政治流亡”中沒有陷入經濟危機。早期古巴移民中的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或憑借較高的文化程度或憑借熟練的技能,都可以在激烈競爭中的美國爭取占有一席之地。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古巴的國內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從而使大批絕望的、貧困的古巴難民遷移到美國境內。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后,更導致了一場非法移民潮。這批新的古巴移民絕大多數來自社會的底層階級,都是處于貧困狀態的窮人,沒有受過什么教育,也沒有一項手藝或者專業技能。因此,他們移民到美國后同墨西哥裔美國人一樣,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行業和服務業,收入不高,生活處于困苦之中。
目前,西裔美國人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族裔群體,并且西裔人口快速增長的趨勢還在繼續,但西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遠不如其人口增長的速度,白人社會的種族偏見和歧視是導致西裔社會經濟狀況惡劣的關鍵因素。此外,西裔美國人低下的受教育程度和大量的非法移民也是造成他們社會經濟低下的重要原因。西裔社會經濟的低下與日益增長的移民和非法移民引發了一系列包括吸毒、暴力、犯罪等社會問題。但是,西裔美國人也為美國的經濟做出了貢獻并且會更大程度地影響未來美國經濟的發展。
【注 釋】
[1] 涂光楠.Hispanic [M]譯談[M].世界民族,1999.3.
[2] 姬虹.肯定性行動與美國少數族裔的教育[J].國際論壇,2004.4.
[3] U.S.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3,Education.
[4] Jaime Raigoza,U.S. Hispanics: A Demographic and Issue Profil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Vol. 10, No. 2 (Winter, 1988), pp. 95-106.
[5] Evelyn Nakano Glenn,Unequal Freedom How Race and Gender Shaped American Citizenship and Labo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4-151.
[6] Nancy S. Landale and R. S. Oropesa,Father Involvement in the Lives of Mainland Puerto Rican Children:Contributions of Nonresident.,CohabitinR and Married Fathers,Smial Forces 79(March 2001),pp.945-968.
[7] 錢皓.美國西裔移民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235.
【作者簡介】
孫曉宇(1994.02—)女,漢族,山東平陰人,哈爾濱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