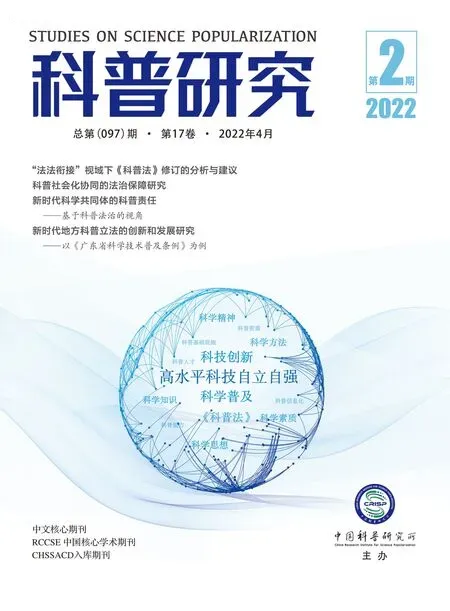突發公共事件中科普繪本的創作方法
吳欣欣
(青島出版社,青島 266061)
公共事件突然發生時,迅速向公眾進行科普、消除其疑慮和恐慌十分必要。當公共事件與兒童息息相關時,向3 ~ 6歲兒童進行及時有效的科普同樣不容忽視。與兒童相關的公共事件發生后,兒童的日常生活習慣往往會被打亂,容易在心理上產生困惑甚至自責,迅速向兒童科普所發生的公共事件,可以幫助兒童了解現狀,減少不安,促使兒童養成良好的習慣并增強社會責任感。
向3 ~ 6歲兒童進行科普,與向成人進行科普有所不同,因為二者的思維方式存在巨大差異。兒童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向他們進行科普時,圖片、視頻、音頻等視覺、聽覺載體比抽象化的純文字更加容易被接受。從圖書的角度而言,以兒童為主要對象、單純用圖畫或者用圖畫和文字相互映襯的方式來進行表達[1]的繪本(又稱圖畫書)顯然更加符合兒童的認知水平。
繪本,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的角度而言,繪本這一概念包容性很強,界限也非常模糊,只要采用圖文結合的表達方式,圖文比例上圖大于文,無論該書是否采用敘事結構,都屬于繪本,比如字母書、玩具書、圖畫故事書[2]。從狹義的角度而言,繪本指的是圖畫故事書,即圖畫和文字兩種表達媒介共同構成敘事載體,兩者有機結合,共同向讀者傳達一個完整的故事。本文所探討的科普繪本,采用繪本的狹義定義,即通過圖文有機結合的敘事結構進行科普的圖書。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全國上下積極應對,出版界也陸續推出了一批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科普圖書。第一本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科普圖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護》,由廣東科技出版社于2020年1月23日出版,48小時內完成,速度令人驚嘆。之后,諸多科普圖書相繼出版,比如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寫給孩子的病毒簡史(彩繪本)》、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寫給孩子的新型冠狀病毒科普繪本》、青島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護讀本》等,呈現方式各不相同,各有其側重和亮點,速度和質量并重,展示了出版業的擔當。但盡管相關主題的圖書已經出版了200余種,優質原創科普繪本卻相對缺位。
一方面,已出版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科普圖書中,有插圖的書出版數量眾多,但正如松居直在《我的圖畫書論》中提到的:“文+畫=有插畫的書,文×畫=圖畫書。”[3]有插圖的書不等同于繪本。比如,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寫給孩子的病毒簡史(彩繪本)》雖然圖片比重頗大,但實際上并不屬于繪本,而是屬于“有插畫的書”,因為書中的圖畫是對文字的簡單呈現,而且圖畫與圖畫之間不構成敘事邏輯。
另一方面,已出版的科普繪本距離優質科普繪本尚有一定的差距。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寫給孩子的新型冠狀病毒科普繪本》具有一以貫之的角色,圖畫自身具有一定的敘事邏輯,其從兒童埋怨不能出門,到爸爸媽媽向其解釋不能出門的原因,再到科研人員研究病毒、病毒的傳播途徑和七步洗手法,簡明親切,尤其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推出,不失為一部合格的科普繪本,但是與優質科普繪本相比,該書仍缺失一些重要的特征。
由此而言,與兒童相關的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后,原創科普繪本如何生動、精準、快速地向兒童進行科普,亟待探討和思索。本文擬對優秀科普繪本的共同特征進行剖析,為科普繪本創作提供參考,進而對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如何進行科普繪本創作提供幾點切實的建議。
1 優秀科普繪本的共同特征
優秀的科普繪本,首先必須是優秀的繪本。何為優秀繪本?可以從美國最權威的繪本大獎凱迪克獎的評選標準中窺見端倪:一是采用了優異的藝術手法;二是圖畫很好地表現了故事的主題和概念;三是圖畫的風格與故事、主題和概念契合;四是圖畫很好地傳達了主題、角色、環境、氛圍和信息;五是非常適合兒童閱讀[4]。該標準不遺余力地強調了優秀的繪本應當以故事為講述模型、畫面與故事應當高度契合。值得注意的是,優秀的科普繪本在具備以上兩個特征的同時,還肩負著平衡科學性與想象力的特殊使命。下面就優秀科普繪本需要具備的三點共同特征展開論述。
1.1 以故事為講述模型
從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到葫蘆娃、哪吒的風靡,無不體現出兒童對故事的喜愛程度。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通過觀察和研究兒童的活動世界,認為兒童與成人不同,他們尚且無法有效地滿足自己情感上甚至智慧上的需要,因此會有一個自己可以利用的活動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他們不是去適應現實,而是將現實同化[5]46。因此,兒童在閱讀繪本時,不是像成人一樣僅僅將其當作一本書、一個虛構的故事看,而是將繪本中的世界按照其自身的意愿進行塑造和演繹,這個過程,也就是皮亞杰所謂的“象征性游戲”。
從這一角度而言,科普繪本采用故事為講述模型,無疑便于兒童開展“象征性游戲”,使其在饒有趣味地構建故事的同時,不自覺地吸納故事中所滲透的科普知識,更有效率地實現科學普及的目的。而且,故事中日常生活場景和幻想場景配合出現,會更有利于兒童代入。一方面,日常生活場景對兒童而言熟悉而親切,可以讓兒童迅速與故事產生聯結;另一方面,幻想場景打破時空限制,可以將不同的科普元素組合發酵,也可以給予兒童充分的演繹空間。
以科普繪本《神奇校車(圖畫書版)》為例,該套繪本以兒童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的學校作為場景,以老師帶著學生乘坐神奇校車上天入地“歷險”為方式,向兒童科普海底、颶風、人體、月球等兒童感興趣的主題。在科普知識的同時,給了兒童充分的想象空間和代入空間,備受小讀者喜愛,常年居于當當網兒童科普圖書榜首。
可惜的是,目前國內的大多數原創科普繪本仍多以平鋪直敘的講述為主,生活場景用得多,幻想場景用得少,故事缺乏起承轉合的曲折性和豐富感。以《寫給孩子的新型冠狀病毒科普繪本》為例,其雖然努力挖掘孩子的視角,比如從孩子的視角出發,質疑不能出門是不是自己的錯,但是在介紹新型冠狀病毒時,仍然是以講述科研人員如何與病毒戰斗、病毒的傳播方式主要有哪些為講述方式,科普內容與整體故事存在很強的割裂感。整本書讀下來,仍是以成人的視角給兒童介紹新型冠狀病毒,而非設置具有想象力和代入空間的情境,讓兒童自發地產生興趣、主動地進行學習和探究。
相比之下,海豚傳媒4月剛剛推出的“病菌快走開”系列繪本,則將病毒擬人化,以“征程”的故事敘述模型,展示病毒如何經歷曲折的“旅程”,到體內“作亂”,最后被醫院及各種預防措施折騰得苦不堪言,最終無奈離開。詼諧生動的同時,足以讓兒童認識病毒的外形、破壞作用、傳播途徑和防護措施。而且,比起平鋪直敘的敘述,這種擬人化的故事敘述模型無疑會讓兒童更容易產生代入感,讓他們為自己穿上勇士的外衣,與擬人化的病毒產生互動、進行斗爭,完成科普知識從書本到實踐的遷移。
1.2 圖畫與故事高度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優秀的科普繪本,不僅文字需要故事化,圖畫亦需要故事化,其圖畫應具備內在的敘事邏輯,推進節奏與文字的推進節奏相呼應,兩者互動并有機結合,共同構筑完整的科普故事。也就是說,“一本圖畫書至少包含三種故事:文字講的故事,圖畫暗示的故事,以及兩者結合后產生的故事”[6]。
一部優秀的科普繪本,其文字不會過于追求面面俱到,擠壓圖畫的敘事空間,而是會充分發揮圖畫和文字不同的表達專長。文字可以用抽象化的字符,表達出豐富的內涵,啟發人們的想象力又不局限于某一具體畫面,構建出差異化理解和解讀的空間;圖畫與文字相比,則更加具體可感,無論是色彩的對比、構圖的多變還是細節的展現,全都是圖畫視覺語言的一部分。也正是因為圖畫和文字各自傳達不同種類的信息,兩者共同作用,彼此限制意義,又利用各自不同的特質互相補充完整,兩者才達到相輔相成的狀態[7]。也唯有如此,繪本的圖畫才能不再是文字的附庸,不再是單純將文字所描述的內容進行直觀的展示,而是對繪本的整個敘事產生指數級的影響,真正適配文藝復興時期建立起的新兒童觀,遵從兒童的自然本性,契合兒童的思維習慣和認知水平,尊重兒童的創造性和發展潛能。
3 ~ 6歲兒童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其在認知事物和思考問題的時候,往往會訴諸具體事物及其外在形象,而非借助抽象的概念和名稱。對于兒童而言,一只熊的圖畫,遠比“哺乳動物”這個概念容易理解和記憶。因此,在創作科普繪本時,作者應充分考慮繪本中圖畫比重大、圖文關系密切的特點,充分發揮想象力,將抽象化的概念加以具象,以契合兒童具體形象的思維習慣。以繪本《我的情緒小怪獸》為例,其將抽象的、看不見的情緒用小怪獸的萌趣形象以及紅色、黃色、藍色等不同的色彩表達出來,非常利于兒童直觀地認識和感知不同的情緒,并且可以幫助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恰當地描述和表達自己的情緒。
1.3 兼顧科學性與想象力
繪本由于其獨特的圖文關系,表現方法十分豐富,而且具有飛躍性。但目前國內的許多原創科普繪本容易過于追求寫實,即便是加入了生活化的情境,也趨向于寫實和嚴謹,這不僅體現在故事曲折程度的欠缺上,也體現在圖畫的想象力匱乏上。科普繪本的圖畫,誠然需要一定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也應符合故事的主題、氛圍等方方面面,在保證科學性的基礎上,增添想象力。
對于科普繪本而言,增添想象力并非等同于天馬行空、脫離現實,而是指在保證科學性的基礎上,將想象力滲透到圖畫的細節中。根據皮亞杰的研究,兒童在閱讀圖畫的時候,其知覺具有混合主義的特征。也就是說,同樣是觀察一幅圖畫,成人往往出于生活中業已形成的系統和策略,會力求以最小的損耗獲取最大的信息量,因而會積極主動地尋找圖畫的主體,過濾掉相對不那么重要的細節;而兒童尚未形成這種系統和策略,因而會不加分析地觀察所有能觀察到的東西[5]33。
從這一角度而言,繪本的細節變得異常重要,需要創作者充分發揮想象力,在保證圖畫整體敘事邏輯完整、具體形象科學嚴謹的基礎上,對畫面的整體架構和細枝末節都予以考量和斟酌。以“病菌快走開”系列繪本中的《當心!有毒的腸道細菌》為例,其將圖畫和文字有機結合,展示了大腸桿菌如何從牛的體內排出后,好不容易趴到生牛肉上,如何在被烤得“半生不熟”的時候,被兒童恰巧夾起,歡天喜地地進入兒童口中。進入胃部之前,大腸桿菌憂心忡忡地閱讀“危險警示”,順利進入大腸后,趾高氣揚地聚集起一支大軍,開始在腸道里大肆搞破壞,與免疫細胞打仗,最終引發腸道里的“火山噴發”。兒童去醫院后,聽從醫生的建議,吃了藥,勤洗手,勤洗澡,不吃生肉。大腸桿菌最后只得背著一個小包袱,落寞地離開,繼續尋找下一個落腳點。這段內容簡介中對大腸桿菌情緒和狀態的描述,皆源自圖畫中大腸桿菌生動的表情和肢體語言。這些圖畫中的細節,既為這個科普故事增添了親切感和代入感,也構成了科普故事敘事邏輯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如果僅將病毒以臉譜化的、千篇一律的面目呈現,對兒童而言,互動性差,距離感強,吸引力自然較弱。
2 科普繪本創作建議
突發公共事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事態緊急、影響范圍廣等。因而,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科普繪本創作,既需要遵循優秀科普繪本的共同特征,又需要滿足突發公共事件所觸發的時效性要求高、科學知識與人文關懷并重等特殊訴求。以下僅從圖書出版和創作角度,對突發公共事件中科普繪本的創作提供幾點切實可行的建議,供探討和參考。
2.1 迅速反應
公共事件影響范圍廣,但由于其突發性,相關信息暫時處于空白或無序狀態。此時,迅速反應是重中之重。
一是要迅速鎖定選題,無論是泛化的概念還是具體的科普,創作者和出版方都要迅速選定角度。雙方一開始便進行對接,并由出版方結合其自身、其所在出版社的圖書結構進行思索,不失為一種高效的方法。
二是要迅速完成內容創作。公共事件發生后,出版方可以第一時間組織有關專家或部門撰寫文稿,并組織繪者進行繪制,文稿、圖稿的創作同時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出版方需要全程參與。由于公共事件的突發性,許多專家往往不具備繪本創作經驗,此時需要出版方與專家和畫手充分溝通,并引導文稿作者及繪者盡快磨合,充分溝通。采納微信公眾號等平臺的熱點科普文章也是迅速完成內容創作的一大途徑。許多新型冠狀病毒科普繪本,其前身便是“10萬+”爆款文章。需要注意的是,與研究者不同,此類作者擅長寫作或者繪畫,但是知識往往不夠系統和嚴謹,因而,需要出版方邀請相關的專家和學者作為顧問,進行知識審核。
三是要迅速推進出版流程。出版過程正常來講十分煩瑣,既涉及選題上報和批復、書號申請、CIP申請等行政性流程,又涉及排版設計、三審三校、印制質量把控、發行營銷溝通等實務流程,涉及環節和人員眾多,需要非常強的團隊協作和管控調度能力。這一過程往往需要出版社予以政策和資源支持,以節約行政審批時間,確保各部門高效配合。
四是推廣要迅速。公共事件往往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將科普繪本送到有需要的孩子手中,需要編輯與營銷人員通力合作,與各渠道及各媒體充分協作,迅速推廣。
2.2 精準定位
一是選題要精準。一個公共事件,有著多種角度的科普可能性。以新型冠狀病毒為例,科普的角度可以是關于病毒自身,可以是關于病毒對身體的損害,可以是病毒與人類的斗爭史,等等。這就需要創作者及出版方找準角度后,再創作科普繪本;要勇于舍棄,不一味追求全面、囫圇吞棗。
二是對讀者的年齡層定位要精準。對于3 ~ 6歲的兒童而言,科普內容不宜過于深奧,只要形象生動地將一個科普知識點講透,就已然是很精彩的科普繪本。以經典繪本艾瑞·卡爾所著的《好餓的毛毛蟲》為例,其主題很簡單,講述了毛毛蟲如何從蟲卵孵化為毛毛蟲,然后蛻變成蝴蝶。但盡管主題如此簡單又耳熟能詳,該繪本還是憑借有趣的故事線、豐富的細節和色彩成為一部經典之作。它通過豐富的色彩,洞洞、階梯切圖的巧思,展示出毛毛蟲的進食過程,并通過周一、周二、周三……一個蘋果、兩個梨、三個李子……進行遞進,在展示數量關系的同時,讓兒童了解一個星期的構成,認識各種各樣的食物,并與毛毛蟲產生共情。最后,毛毛蟲不覺得肚子餓了,變成了一條又肥又大的毛毛蟲。看到這里,兒童一定忍俊不禁。而下一頁,接著展示了毛毛蟲如何造了一間叫作“繭”的小房子,把自己包在里頭,并在里面住了兩個多星期。然后,它把繭咬破一個洞,鉆了出來……變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兒童看到這里,自然會驚嘆蝴蝶之美麗,贊嘆毛毛蟲的發育過程之神奇,并將這一過程內化于心。
2.3 滲透人文關懷
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容易引發兒童心理上的焦慮甚至自責,因而在創作以突發公共事件為題的科普繪本時,需要在進行知識科普的同時,加入一定的人文關懷,向兒童傳達勇于面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觀念的傳達,一定是通過情節設置,而不是通過說教,才能真正引發孩子的共鳴。
以廣受兒童喜愛的《可愛的鼠小弟》為例,其雖非科普繪本,卻以鼠小弟和它的朋友為主角,將大小、重量等概念進行了生動的呈現,將不同動物的習性和特長滲透在故事中,并涵蓋了多種精神層面的啟示,如合作精神、分享精神等。想吃蘋果的鼠小弟,努力地去摘樹上的蘋果,但是怎么都夠不著。接著,它發現,小鳥可以直接飛到樹上,猴子可以爬到樹上,大象有長長的鼻子,長頸鹿有長長的脖子,袋鼠可以跳很高,犀牛可以撞樹……它十分羨慕,正在沮喪的時候,海獅過來,幫忙把鼠小弟拋到了樹上,鼠小弟終于吃到了蘋果。整本書完全沒有任何說教的語言和意味,而且畫風和語言極其簡明,卻呈現出不同動物的外觀及其習性,并滲透著堅持不懈、互相幫助、團結合作的精神;這種“潤物細無聲”式的方式,非常值得在科普繪本創作時借鑒。
2.4 拓寬傳播維度
拓寬傳播維度,一方面,可以采納新技術,使紙質繪本的互動方式更加多樣。比如,將逐漸成熟的增強現實(AR)技術運用到科普繪本中,無疑會增加繪本的趣味性,調動兒童互動的積極性。不過,在植入AR等新技術的時候,應避免炫技式植入,而應當對技術的交互方式加以把握,使其充分調動兒童的感官,并且緊緊圍繞故事場景展開,對敘事主線不形成干擾,真正讓技術服務于科普繪本自身,并通過人物引導法、音頻串聯法等,制造主體參與的情景,將科普繪本與新技術緊密結合[8]。
另一方面,可以將內容的呈現方式多樣化。在如今的數字時代,獲取信息和知識的載體百花齊放,無論是短視頻、直播,還是音頻,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傳播速度。而在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社會秩序往往會遭受一定的擾動,常規的倉儲、物流等方面都會受到一些影響,紙質圖書在這方面容易受限。電子書、音頻、視頻等載體則不受時空限制,也不存在物流和倉儲限制,不失為公共事件發生時迅速反應的高效渠道。比如,青島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護讀本》,電子書、有聲書同步上線。截至2月26日晚,其有聲書在喜馬拉雅平臺的點擊量已突破62.3萬次,便是拓寬傳播維度的一次好的嘗試。
3 結語
3 ~ 6歲的兒童正處在好奇心旺盛、對外界感知敏感的人生階段。當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兒童會產生好奇、焦慮、不安等復雜情緒,因而,向其進行迅速、有效的科普十分迫切和必要。繪本以其故事化的呈現方式、緊密的圖文關系、充滿想象力的畫面成為向兒童進行科普的理想圖書形式。
與單純的故事類繪本相比,科普圖書具有科學性要求高的獨特特質;而突發公共事件也為創作提出了及時高效、兼顧人文關懷等特殊要求,這就需要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科普繪本創作對繪本的趣味性、科學性和時效性進行平衡。本文雖然提出了迅速反應、精準定位、拓寬傳播維度等具體建議,但如何真正將建議付諸實施,如何真正啟發兒童的科學思維,仍然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在理論上進一步系統化。
畢竟,科普繪本的目標,絕不僅僅局限于告訴兒童是什么,更多的是為了培養兒童的科學思維,真正拉近兒童與科學的距離,讓他們看到世界的復雜和美妙,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為創造力的生發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