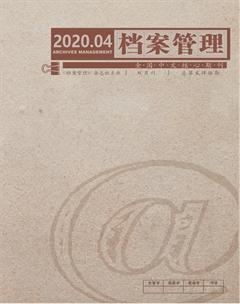也談檔案利用與“黑天鵝事件”
梁艷麗
摘? 要:《檔案利用與“黑天鵝事件”——論檔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預測》與《再論檔案利用與“黑天鵝事件”——兼與劉東斌、吳雁平二位作者商榷》兩篇文章對“黑天鵝事件”特征的描述不同,對檔案利用的個體性與整體性、特殊性與一般性側重點不同,對檔案隱性價值和顯性價值的關注點不同,對案例選擇的范圍不同導致了結論的不同。作為一篇單獨的文章,后者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從商榷和探討的角度看,后者的漏洞是顯而易見的。
關鍵詞:檔案利用;黑天鵝事件;劉東斌;利用內容不可預測性
《檔案管理》雜志2019年第3期、2020年第1期先后刊登了劉東斌、吳雁平撰寫的《檔案利用與“黑天鵝事件”——論檔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預測》(以下簡稱《劉文》),邢變變、王坤撰寫的《再論檔案利用與“黑天鵝事件”——兼與劉東斌、吳雁平二位作者商榷》(以下簡稱《邢文》)。針對《劉文》認為的檔案利用具備“黑天鵝事件”小概率和不可預測性特征,《邢文》指出,“檔案利用的小概率”不等于“黑天鵝事件”的“罕見”,檔案利用的“不可預測性”與“黑天鵝事件”的“事后可預測性”不相符合,《劉文》所列舉的檔案利用案例不具備極端影響力特征,檔案價值具有客觀相對可知性、主觀相對可知性、相對確定性。[1]
筆者認為,兩篇文章對“黑天鵝事件”特征的描述不同;對檔案利用的個體性與整體性、特殊性與一般性側重點不同;對檔案隱性價值和顯性價值的關注點不同;對案例選擇的范圍不同。這些不同點導致了結論的不同。
1 對“黑天鵝事件”定義特征的不同描述
《劉文》認為,“黑天鵝事件”有兩個主要特征:其一,罕見;其二,無法預測。[2]《邢文》認為,“黑天鵝事件”有三個主要特征:第一,稀有性;第二,沖擊性;第三,事后可預測性。[3]
1.1 “罕見”“稀有”“小概率”。《邢文》認為,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對“罕見”“稀有”的解釋,兩者意思接近,都可以用來解釋事件出現的頻次低、極少發生。而“小概率”指的是某事件出現的頻率較低,但出現的絕對次數并不一定低。接著,《邢文》以2015年至2017年,全國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的利用率雖然僅為3.1%左右,館藏檔案的提供利用平均每年都在2000萬卷、件以上來印證檔案利用屬于“小概率”,但并非“罕見”。[4]
筆者認為,對“罕見”“稀有”的理解要與一定時期、一定地域的社會情況相結合,與某事件在某時期某范圍發生的概率相結合,與特定時期人的認知相結合。《劉文》列舉了一個案例:1988年建平縣統戰部應臺胞李樹春查找其家鄉住址及家人的請求,在縣檔案館查閱原熱河省地圖后,實地查訪,找到了李的家。[5]案例發生的時間為1988年,臺胞通過縣統戰部查找家鄉住址,對縣檔案館來說,這個年代、這種人群、這種事由、這種內容、這種意義的查找是不是既“罕見”“稀有”又“小概率”呢?
《劉文》所列舉的個人層面的利用檔案解決林場權屬問題的細節不是很清楚。筆者所在的河南省新鄉市檔案館有一個與此類似的案例。2009年,河南省焦作市修武縣糧食局應縣委、縣政府招商引資號召,尋找合作伙伴開發原方莊糧管所閑置的場地、庫房,服務云臺山旅游發展,以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項目實施過程中,當地村民說,土地不是征用的,是“友好”地借給糧食部門的,一旦不作糧倉使用,他們有權收回。經多方查閱,最終在修武縣檔案館查到了糧管所1965年、1967年、1976年的三次征地文件,在新鄉市檔案館查到了1970年的土地征用文件。從1965年的第一次征地到1976年的最后一次征地,從糧管所場地、庫房的使用到閑置,幾十年來,當地村民沒有人對土地的權屬提出異議,糧管所乃至修武縣糧食局更不會懷疑土地的權屬。2009年,土地開發過程中當地村民突然要求收回土地,對于方莊糧管所乃至修武縣糧食局而言,村民的行為及要求是不是既“罕見”“稀有”,又“小概率”呢?
1.2 “無法預測”與“事后可預測”
1.2.1 《邢文》“事后可預測”的出處。《劉文》認為,“黑天鵝事件”具有不可預測的特征,《邢文》認為,“黑天鵝事件”具有事后可預測特征。《邢文》對于“黑天鵝事件”內涵及特征的描述源自參考的一篇文獻《黑天鵝事件定義及分類的探討》(以下簡稱《佟文》)。原文為:Taleb認為黑天鵝事件需滿足三個特征:第一,稀有性,它在通常的預期之外,過去沒有任何能夠確定它發生可能性的證據;第二,沖擊性,產生極端的影響;第三,事后預測性,盡管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會促使我們在事后為它的發生編制理由,似乎它是可以解釋和預測的。[6]有趣的是,《邢文》將第三個特征改為了:事后可預測性,即盡管它突然發生具有意外性,但對整個事件進行回顧后就會找到其發生的征兆,使事件看起來可解釋、可預測。兩相對比,不難發現,《邢文》將所引文獻中的原意“人出于對未知事物的探索,為超出預期發生的事件編制理由,使完全無法解釋和根本無法預測的事件因此顯得具有了因果、推理關系,似乎可解釋和推測”改成了“對事件的回顧,從中找到征兆,使事件看起來可解釋、可預測”。即便如此,可解釋、可預測也只是“看起來”如此,不代表就是如此,更不意味著找到的征兆一定朝著特定的方向發展,最終導致事件的發生。由此看來,可預測本身就是經不起推敲的,是值得懷疑的,是站不住腳的。
1.2.2 對《佟文》“黑天鵝事件”定義要素的分析。《佟文》以表格形式從定義來源、定義內容、定義要點列舉了9種類型黑天鵝事件的定義。[7]從定義要點數量來看,要點僅1個的數量為4,占比44.44%;要點有2個的數量為3,占比33.33%;要點有3個的數量為2,占比22.22%。從“不可預測”與“事后可預測”在不同定義中的占比上看,可以說人的認知范圍內事件不可能發生的有3種;事件發生了,但超出了人的認知,因而不可預測的定義有2種。定義要點中含“不可能”的有3種,含“不可預測”的占2種,這5種類型的定義表達的共同意思為:不可預測,占比為55.56%。與此相對,定義要素中明確含有“事后可預測性”的僅1種,占比11.11%。
3.1 《劉文》所謂的檔案價值不可知基于檔案顯性價值的實現不可知。《劉文》指出:檔案價值的客觀需要,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技術發展形勢的制約,什么時候社會需求什么樣的檔案,什么時候什么樣的檔案可以實現其價值都是不清楚的。[21]
毋庸置疑,這種判斷是符合唯物觀、歷史觀和辯證觀的。檔案是社會的產物,其載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其內容更是特定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反映。檔案的管理具有時代特點,人們對檔案的認識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檔案法律法規的完善,檔案的價值逐漸凸顯,檔案的開放利用水平也越來越高。
只要檔案何時被利用、被何人利用、被用于解決何種事項、對于解決的事項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等因素不確定,檔案的顯性價值就是未知的。
3.2 《邢文》所謂的檔案價值可知基于檔案的隱性價值的相對可知。以會計檔案鑒定為例,高齡會計檔案應受尊重是對檔案隱性價值在不同時代不盡相同的一種注解。會計檔案的鑒定既要考慮會計檔案形成者的社會地位及其承擔職能的重要性,也要考慮所記錄內容的重要性、準確性;既要考慮會計檔案所形成的年代、時期,也要考慮其形式;既要考慮是否完整,也要考慮其形成環境及依附系統的生命周期;既要考慮本單位的使用情況,也要考慮審計、公檢法等部門的調查需要;既要考慮當前的利用需求,也要考慮歷史研究的需要。[22]由此可見,檔案的隱性價值在不同的時代不盡相同,在同一時代不同的人眼里也不盡相同;同樣的人,從事檔案工作的時間不同、經驗不同,對檔案隱性價值的判斷也不盡相同。
《邢文》先后論證了檔案價值的客觀相對可知性、檔案價值的主觀相對可知性、檔案價值的相對確定性。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也是基本正確的,但以此反駁《劉文》檔案價值不可知的論點軟弱無力。檔案的隱性價值不代表也不等于檔案的顯性價值,更不能用來論證檔案的顯性價值是否可知。一件檔案,無論其隱性價值有多大,如果從未利用過,其顯性價值就是零;一個檔案館,館藏資源再豐富,如果利用者在這里沒有找到需要的檔案,對利用者而言,這里的檔案是沒有價值的。
總之,《邢文》雖名為對《劉文》的商榷文章,但由于兩篇文章對“黑天鵝事件”的定義特征判斷不一致,論述的關注點不同,所以,基本處于各說各話的境地。從單獨的一篇文章看,《邢文》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從商榷和探討的角度看,《邢文》的漏洞是顯而易見的。
參考文獻:
[1] [3] [4] [8] [11][12][19]邢變變,王坤.再論檔案利用與“黑天鵝事件”——兼與劉東斌、吳雁平二位作者商榷[J].檔案管理,2020(1):63-65.
[2] [5] [9][10][13][14][21]劉東斌,吳雁平.檔案利用與“黑天鵝事件”——論檔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預測[J].檔案管理,2019(3):55-57.
[6] [7]佟瑞鵬,謝貝貝,安宇.黑天鵝事件定義及分類的探討[J].中國公共安全(學術版),2017(2):44-48.
[15]閆俊麗,何惠光.漯河市檔案館近10年檔案利用情況調查[J].檔案管理,2014(5):54-55.
[16]周應朝.新鄉市檔案館(一庫)檔案利用統計分析[J].檔案管理,2003(5):23-24.
[17]程相山,王玉.南陽市檔案館1995年—2004年檔案利用情況調查與分析[J].檔案管理,2005(4):53.
[18]吳雁平,張金娜,劉衛華.開封市檔案館1990—1999年檔案查詢利用情況個案統計分析[J].檔案管理,2003(4):21-23.
[20]張苗苗.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及相關概念辨析[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7(03):28-30.
[22]段東升主編.會計檔案整理[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59-60.
(作者單位:河南省新鄉市檔案館? ?來稿日期:20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