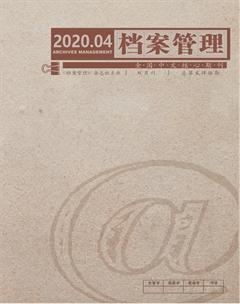出版物檔案概念及其理論實踐
郭東升
摘? 要:出版物、出版物檔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謂出版物檔案,就是出版物編輯出版過程中形成的有保存價值的歷史記錄。相同點在于出版物與其相對應的出版物檔案是同一事物。不同點在于出版物檔案的外延小于出版物。出版物檔案的內涵大于出版物。二者的聯系,一是出版物與出版物檔案兩個概念屬于相容關系;二是一般出版物個體,即非出版物檔案個體,與出版物檔案個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檔案行政部門應該注重出版物文件材料歸檔、出版物檔案收集保管利用的規范化。
關鍵詞:出版物;出版物檔案;概念;本質;聯系
《檔案管理》2019年第5期發表了桑晟先生的文章《出版物作為檔案保管的機理闡釋》,文章主要從文件結構體系角度闡釋出版物作為檔案保管的合理性,關注出版物檔案并從理論上闡述論證,是非常值得稱道的。這對出版物檔案收集保管實踐大有裨益。拜讀之余,又覺得其對出版物檔案的論述尚不到位,似有從出版物檔案概念本質上作更進一步討論之必要。
1 關于出版物、出版物檔案概念
要厘清出版物檔案保管機理問題,首先應該明確出版物、出版物檔案的概念、本質及其聯系。筆者以為,出版物、出版物檔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什么是出版物?2016年2月6日國務院修訂的《出版物管理條例》說:“本條例所稱出版物,是指報紙、期刊、圖書、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等。”這是以列舉法為出版物下的定義,概念簡單明了。雖其末尾“電子出版物”之表述,略有同語反復之嫌,怕也是無奈之舉。什么是出版物檔案呢?該條例并無涉及。新聞出版署、國家檔案局1992年9月13日發布的《出版社書稿檔案管理辦法》第二條稱:“書稿檔案是圖書編輯出版過程的歷史記錄,是國家檔案的組成部分。”這里的書稿檔案,應是把出版物檔案包括在內的。其第三章“書稿檔案立卷范圍”的第五條“立卷歸檔的文件、材料范圍”之第七款是“圖書出版通知單、清樣、樣書”。這里的樣書明顯就是出版物檔案。以上兩個法規沒有給出版物檔案專下定義,根據其思想內涵和檔案本質屬性規定,我們不妨給它下一個定義。所謂出版物檔案,就是出版物編輯出版過程中形成的有保存價值的歷史記錄。這里,出版物檔案的外延也就包括了報紙、期刊、圖書、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等,只是其概念內涵與出版物有所不同。
2 出版物與出版物檔案概念的相同、不同及聯系
出版物與出版物檔案有哪些相同點呢?從實體角度看,出版物與其相對應的出版物檔案是同一事物,這是它們的相同點。所謂相對應,就是二者是同一出版實體。都是同一出版活動形成的最終成果。例如2019年第5期《檔案管理》,作為《檔案管理》雜志社本期雜志的最終編輯出版成果,它既是出版發行物,屬于出版物,又是作為本期雜志最終編輯出版過程的記錄物,也就是出版物檔案。二者是同一事物。二者不同點是什么呢?從概念角度看,出版物檔案的外延小于出版物外延。出版物檔案的內涵大于出版物。二者的聯系有兩點,第一點是:出版物與出版物檔案兩個概念屬于相容關系,是屬種關系。出版物為屬,出版物檔案為種,出版物檔案包含于出版物。第二點是:一般出版物個體,即非出版物檔案個體,與出版物檔案個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即一般出版物個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出版物檔案個體,同樣,出版物檔案個體也可以轉化為一般出版物個體。一般出版物個體轉化為出版物檔案的條件是歸檔,出版物歸其出版物形成者管理。也就是說,歸檔主體必須是其出版物的形成者或形成者之一。
3 關于出版物檔案與出版物文件機體結構關系
桑晟先生文章說:“一本圖書問世要經過選題、論證、立項、向行政主管單位報批、編輯、設計、打印、校對、印刷等諸多環節最后出版。在每一個環節都要求形成與之相關的文件,這些文件與最后面世的圖書形成一個有機的文件整體,記錄此次出版活動的全過程。圖書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它處于記錄此次出版活動所形成的文件鏈條的末端,它記錄的是出版活動的結果。當它作為檔案保存的時候,它只是這個文件有機體的一個因子,它與此次出版活動的其他文件具有關聯關系,具有結構特征。”這論述,站在出版活動過程角度把握文件材料收集歸檔的完整性來看問題,是正確的,筆者沒有異議。但桑晟先生接著說:“它與其他文件之間的結構關系是它作為檔案保存的先決條件,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它僅僅是圖書而已。”這種把一檔案個體認定與其檔案形成過程文件整體掛鉤,以整體性與非整體性鑒定檔案個體性質的是與否,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筆者無意否定檔案個體和與它有密切聯系的檔案群體間的密切關系,也不反對一組檔案個體在其形成中的“系統”或“結構”意義。但這里的“系統”或“結構”含義,應是強調的檔案各個體之間的相互聯系性,檔案保管單元整體與檔案個體之間的保管形式存在狀態,并不存在檔案整體可以決定或否定其中某一檔案個體性質問題。如,案卷是一組在其形成過程中具有有機聯系的檔案整體保管單元,全宗是立檔單位形成的檔案個體之全部。這種檔案個體與檔案單元的結構性、系統性,其意義在于檔案的整理、保管、利用,在于便于揭示彰顯檔案單元的整體信息和各檔案個體間的關聯信息,而絕不是以檔案單元的系統性、結構性去決定或否定其中任何一個加入或脫離、游離其檔案保管單元者的個體性質。檔案個體的性質只能由其自身存在的具有保管價值的原始記錄性質來決定,決不會還有什么其他的“先決條件”在里面。事實上,同一出版物檔案,并不一定屬于同一全宗。這一點,桑晟先生文章也是有所認可的。桑晟先生文章把出版物作為檔案保管的主體列舉為“出版社、作者、編輯、封面設計人員”,那么,相關出版物檔案就可以分屬其所述各個主體形成的不同的全宗。比如,同是2019年第5期《檔案管理》,有的歸檔于《檔案管理》雜志社全宗,組在2019年第5期《檔案管理》出版過程形成的案卷中。有些則要分別歸檔于文章作者、編輯、封面設計人員等各個人全宗之中。將其歸檔作者全宗者,當然應該與作者的該文寫作提綱、初稿、修改稿、定稿及編輯部提出的修改意見等整理在一個或若干形成該文的文件案卷中。桑晟先生說:“檔案是具有‘系統(不是‘集合,集合不具有結構特征)屬性的。”這里,他把“系統”“結構”兩個概念表述得比較含糊。但排除了二者的集合意義。雖然排除了其集合涵義,其對出版物檔案“系統”與文件“個體”性質的表達卻很有集合概念意味。比如,他認為,圖書個體在出版社內部不是檔案。“在名人全宗中作為檔案存在的名人作品也是如此,不是因為作品自身,而是因為在名人全宗中它與其他檔案成分的結構關系才作為檔案保存。名人全宗中的檔案成分都屬于一個人,共同記錄和再現名人的人生軌跡。將作品從名人全宗中剝離出來,其作品就失去了檔案的性質,僅僅是作品而已。作為檔案保管的出版物與其他文件具有了這種結構關系,它才能作為檔案保存。”把個體的性質捆綁在全宗“系統”上,脫離這“系統”,這檔案個體就不具有檔案性質了。這不是認為一個集合體具有的屬性,必定不為組成該集合體的每一個個別事物所具有的意義了嗎?這實質上不還是在檔案本質把握上,把檔案整體與文件個體關系等同于集合概念特征了嗎?如此,無論是在常理上,還是在邏輯上,它都是說不通的。之于檔案,一個案卷,它是檔案,其案卷中的每一文件,也是檔案。從“系統”角度說,也只能說,文件整體稱之為案卷,單個文件只能稱一份檔案,而不能稱案卷。這是案卷與檔案個體兩個概念的區別聯系關系,不是檔案與非檔案間的區別與聯系,決不能把它們說成,案卷是檔案,其中的一份文件不是檔案。檔案個體與全宗關系也是如此。只能說,一立檔單位歸檔文件整體稱之為全宗,其中單個文件只能稱一份檔案,而不能稱全宗。但決不能把其說成只有全宗是檔案,其中的一份文件不是檔案。事實上,文件也有個系統屬性,比如某文件包括了正件和若干附件。這正件與附件之間就顯示了它的系統性。檔案本來是有自己的個體性的。檔案個體之于全宗,不是完全一一對應的。同一檔案實體,可以歸入不同的全宗。比如2019年第5期《檔案管理》,有的歸入《檔案管理》雜志社全宗,有的歸入桑晟全宗。桑晟先生說:“出版物是否作為檔案保管,受其主體和客體制約。”是的,但應該加一句:出版物是否檔案,要看其主體是否是客體出版物的形成者,客體出版物是不是檔案,看其收集保管者是不是出版物的形成者。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4 關于出版物、出版物檔案的文化屬性
桑晟先生文章以圖書為例對作為檔案保存的出版物屬性進行分析。他認為:作為檔案保存的圖書已經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屬性,它的知識性。他說:“此時此刻的圖書,相當于出版社,它不以在出版社內部傳遞圖書承載的信息和知識為己任,已經失去了自身的精神,退去了該有的品質,附加了檔案(文件)的性質,作為出版社的原始記錄而存在,相對于出版活動,圖書中記載的知識內容是無關緊要的。它記錄的是出版活動的過程,并且相對于此次出版活動具有了憑證價值。”這段論述多有不妥。從概念角度看,出版物的最重要的屬性,固然是它的知識性與知識傳播性。但這一屬性也是出版物檔案的重要屬性。如筆者前文所述,出版物檔案概念的屬概念是出版物,所以知識、知識傳播性是出版物、出版物檔案兩個概念所共有的。出版物檔案概念與出版物概念在代表質的內涵上,差別在于出版物檔案內涵比出版物多。多什么呢?多出了一個原始記錄性。應該說,知識、知識傳播性不能把出版物與出版物檔案二者區分開來。而原始記錄性才能把出版物與出版物檔案區別開來。二者中凡是具有原始記錄性屬性者,它就是出版物檔案。這樣,從概念角度說,桑晟先生關于出版物作為出版物檔案保存的提法也是不準確、不科學的。出版物檔案就是出版物檔案。不必加一個“作為”來當限制詞,而把出版物檔案概念表達得那么勉強。出版物檔案的知識、知識傳播性價值存在與利用,在立檔單位表現發揮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比如其再版發行的例子,復印復制摘錄摘編的例子,出版社內部借閱的例子,都是有的。怎么可以說它不以在出版社內部傳遞圖書承載的信息和知識為己任,已經失去了自身的精神,退去了該有的品質了呢?不僅僅是出版社,凡是立檔單位保管的出版物檔案,它們都不會失去其出版物價值的。不僅僅是出版社與其他出版物檔案形成者各全宗,就是我們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保存的本地名人出版物檔案也多有本館人員研究借閱。比如筆者就閱讀研究過臨清名人、明代大詩人謝榛的出版物檔案《四溟詩話》。桑晟先生論述說:圖書“作為出版社的原始記錄而存在,相對于出版活動,圖書中記載的知識內容是無關緊要的。它記錄的是出版活動的過程,并且相對于此次出版活動具有了憑證價值”。這就更不妥當。且不說圖書出版物檔案的利用,就是對它的鑒定,也是必須看它的內容價值的。其內容價值、形式價值高,它會被定為長期永久甚至珍貴檔案;其價值低,會被定為定期檔案;沒有了價值,就要被作銷毀或移出全宗處理了。檔案不僅僅有憑證價值,而且有參考價值。出版物檔案也是如此。參考價值,內容為重,怎么可以輕視出版物檔案的參考價值,特別是它的文化價值呢?
5 出版物檔案概念的指導意義
出版物與出版物檔案概念認識上的理論滯后,使得檔案館室人員對出版物檔案歸檔與收集進館缺乏應有的意識自覺,使得出版物檔案收集工作大受影響。一些出版物形成者忽視甚至不知道將其出版物記錄最終成果的文件材料歸檔,而只是將其看成出版物。一些出版物立檔單位及其域內國家綜合檔案館,也如此的把出版物檔案當出版物來看待。這是令人十分揪心的事。把出版物檔案作為出版物來收集保管,其安全風險是非常大的。就是在國家綜合檔案館,也是如此。比如臨清市1948年10月創刊的《臨清日報》,連續兩任市委書記兼任主編,到頭來一張報紙也沒有留下。比較其他檔案,臨清市自1945年9月1日建市起,市長就安排建立起檔案工作來,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門單位的文件材料收集歸檔比較齊全完整。如果那時有一個出版物檔案意識,臨清市檔案館應該還能看到那時的《臨清日報》。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在臨清市黨史辦工作時,去北京訪問時任臨清市委書記兼《臨清日報》主編的丹彤。他說:“臨清市檔案館檔案齊全,就是沒有《臨清日報》。那時我當主編,也親自寫了不少稿件,有好些的東西是檔案里沒有的。應該尋找尋找,看還能不能找到。”一晃四十年,哪里尋得到《臨清日報》的影子,當年滿市亂飛的一張報紙,因為沒有被認識到是出版物檔案,隨著星移斗轉,消聲滅跡了,給臨清的一段歷史研究帶來多大的遺憾哪!筆者以為,重視出版物檔案的歸檔與收集,就必須在理論上大張旗鼓地為出版物檔案正名分。不為出版物檔案正名,館室及個人的歸檔范圍、檔案收集范圍文件,就不把出版物檔案列入其中,從收集范圍開始,就把其拒之門外了。檔案行政部門應該建立本行政區域出版物文件材料歸檔檔案規章,有出版物檔案收集保管利用規范。如此,我們的出版物檔案歸檔進館工作必然更上一層樓。
(作者單位:山東省臨清市檔案館 來稿日期:2020-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