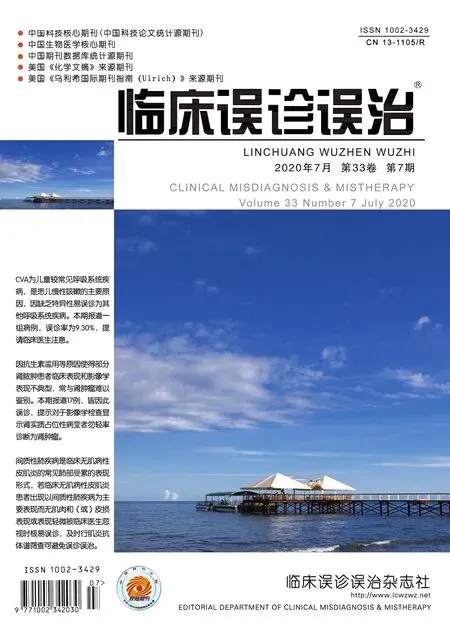輕型、普通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高分辨率CT影像學特征及短期演變
張欲翔,王 琳,宋彥芳,張澤坤,桑 輝,劉 明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是由2019新型冠狀病毒致病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1-3]。COVID-19傳染性強,病情短期變化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印發的試行第六版COVID-19診療方案中提出影像學特征在COVID-19診斷中占十分重要的作用[4-5]。高分辨率CT(high resolution CT,HRCT)方便快捷,不僅可以準確判斷肺內病變的影像學特征,而且可以對同一患者進行及時的定期復查,動態觀察肺內病變的演變過程。除湖北地區外,我國其他地區也有COVID-19患者,筆者現回顧分析非湖北地區12例確診的輕型、普通型COVID-19患者首次及短期(3~5 d)復查的HRCT圖像,旨在探討輕型、普通型COVID-19的影像學特征及短期影像學變化,為臨床診治提供影像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搜集2020年1月24日—2月17日確診的12例非湖北地區COVID-19患者,納入標準:①有流行病史或密切接觸史;②兩次COVID-19實時熒光定量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檢測陽性;③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試行第六版COVID-19診療指南[6]臨床診斷為COVID-19輕型或普通型患者;④具有首次檢查和3~5 d后復查兩次胸部HRCT檢查資料。排查標準:①1次COVID-19實時熒光定量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檢測陽性;②僅行1次胸部HRCT檢查;③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試行第6版COVID-19診療指南[6]臨床診斷為COVID-19重型、危重型患者。12例中男8例,女4例;年齡13~67歲;輕型2例,普通型10例。
1.2HRCT檢查方法 采用Philips Brilliace 64 CT掃描儀。患者取仰臥位,頭先進,掃描范圍上自胸廓入口、下至肺底,屏氣行連續螺旋掃描。掃描參數:管電壓120 kV,管電流200 mAs,視野350 mm×350 mm,矩陣512×512,層厚5 mm,行冠狀位及橫軸位骨算法重建,重建層厚0.625 mm。
1.3HRCT圖像分析 由2名經驗豐富的從事放射診斷工作的副主任醫師進行盲法目視評價,肺窗下觀察病變分布(左右肺、肺葉、肺段),形態(斑片狀、片狀、條狀、圓形),密度(淡薄、磨玻璃、實性、混合型),位置(胸膜下、支氣管血管束周圍、二者同時受累),最大病變長徑,邊界(清楚、模糊);縱隔窗下觀察是否伴有胸腔積液、是否伴有肺門及縱隔淋巴結增大、是否累及胸膜。當2名副主任醫師診斷結果不一致時由主任醫師進行判讀。
1.4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3.0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是否符合正態分布,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表示,比較采用秩和檢驗。以α=0.05為檢驗水準。
2 結果
2.1首次胸部HRCT檢查病變分布 12例COVID-19患者中,2例(16.67%)胸部HRCT無異常;6例(50.00%)雙側肺葉受累;4例(33.33%)單側肺葉受累,其中左側肺葉受累1例、右側肺葉受累3例。12例中以左肺下葉、右肺下葉受累為主[各7例(58.33%)],右肺上葉及中葉受累各6例(50.00%),左肺上葉受累5例(41.67%)。12例中以右肺下葉背段、左肺下葉前內基底段受累為主[分別為7例(58.33%)、6例(50.00%)],右肺下葉后基底段、左肺下葉外基底段及右肺中葉外側段受累各5例(41.67%),左肺下葉背段、左肺下葉后基底段、右肺下葉內基底段、右肺下葉外基底段、右肺上葉尖段及右肺上葉后段受累各4例(33.33%),左肺上葉尖后段、左肺上葉上舌段、右肺上葉前段、右肺中葉內側段及右肺下葉前基底段受累各2例(16.67%),左肺上葉前段、左肺上葉下舌段受累各1例(8.33%)。
2.2短期(3~5 d)復查與首次胸部HRCT檢查病變分布比較 12例短期復查胸部HRCT后,2例首次胸部HRCT無異常患者仍無異常,2例單側肺葉受累患者進展為雙側肺葉受累;短期復查胸部HRCT肺葉、肺段受累數較首次檢查均有增加,但肺葉受累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肺段受累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12例輕型、普通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兩次高分辨率CT檢查病變累及肺葉、肺段數比較(中位數)
2.3短期(3~5 d)復查與首次胸部HRCT檢查病變影像學特征比較 12例首次胸部HRCT檢查中,除2例無異常外,其他病例均有異常影像學改變,病變僅位于胸膜下3例、僅位于支氣管血管束周圍2例、同時位于胸膜下及支氣管血管束周圍5例;病變僅表現為磨玻璃影3例(圖1a)、僅表現為實變影2例,病變呈磨玻璃影、鋪路石征、實變、纖維化、結節等多種影像特征,部分病變磨玻璃影可伴發血管穿行征,部分病變鋪路石征可伴發空氣支氣管征(圖1b),伴發胸膜病變7例,伴發胸腔積液1例。短期復查胸部HRCT示:病變明顯進展2例,表現為病變分布范圍顯著增大、數目增多(圖2);1例由單側肺葉受累進展為雙側肺葉受累,表現為多發磨玻璃影、空氣支氣管征、結節影;1例右肺下葉實變影明顯吸收好轉;3例較前磨玻璃影數目減少、范圍縮小;部分病變在原病灶基礎上出現纖維索條影;1例新見少量胸腔積液。
3 討論
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性強、致病率高,并且具有較高的突變率[7],同時更應高度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傳播[8-9]。COVID-19患者臨床表現各不相同,根據臨床特點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輕型患者癥狀較輕,重型及危重型患者癥狀重,多伴有呼吸困難、低氧血癥,甚者出現呼吸窘迫綜合征、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導致死亡[10]。對于非湖北地區COVID-19患者擁有自身的一些特點,本研究患者為輕型、普通型。胸部HRCT不僅方便快捷,而且敏感性高,可以檢出毫米級病灶,更重要的是其可動態觀察肺部病變的演變過程[11]。本研究發現2例核酸檢測陽性,但是臨床癥狀輕,兩次胸部HRCT檢查無異常。故臨床需注意部分COVID-19患者,臨床癥狀輕,CT檢查陰性,但是本身具有傳染性,一定要結合核酸檢測,以防漏診的發生,這可能和宿主的免疫狀態有關[12]。本研究中COVID-19患者以兩肺葉同時受累多見,2例單側肺葉受累病變短期復查HRCT進展成雙側肺葉受累;同時發現COVID-19患者以兩肺下葉受累多見,尤其是左肺下葉前內基底段、右肺下葉背段,推測可能是由于COVID-19的目標細胞位于下呼吸道[13-15];短期復查與首次胸部HRCT對比發現大部病例均有變化,以肺段受累數增多為主,說明對于大部COVID-19患者短期內病灶受累呈增多趨勢。對于同一患者短期內肺內病變演變的過程,不僅表現在累及肺段、肺葉的增加,而且表現在原病灶本身的變化,如范圍的擴大或縮小、邊界的清楚或模糊、密度的改變、形態的改變等,此外還需注意是否繼發胸膜病變、胸腔積液以及肺門、縱隔淋巴結增大等,本研究除無淋巴結增大外均有涉及。這些演變過程,可能和炎性細胞因子有相關性[16],肺泡損失后,肺泡內滲出和水腫的程度不同[17],支氣管及血管邊緣增厚、間質受累[18],導致影像學特征不同;當炎癥引起胸膜受累時,會引起胸膜反應(胸膜炎或反應性炎癥),導致胸腔積液的發生[19]。
總體而言,COVID-19的胸部HRCT影像學特征為多形態并存,主要以間質性病變為主,特征性磨玻璃影分布以兩肺下葉、胸膜下多見。短期復查胸部HRCT可及時觀察肺內病變的演變情況,從而判定肺組織損傷程度,同時需結合臨床及相應的實驗室檢查指標進行綜合判定。由于時間倉促,非湖北地區COVID-19患者相對較少,病例有限,仍需進行多中心、大樣本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