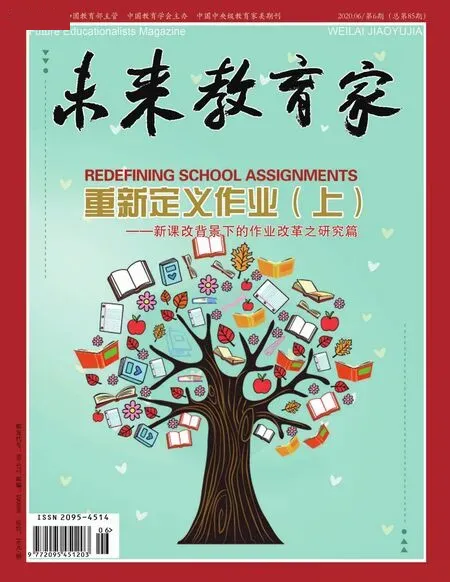讀書心得三十則(下)
孫立權/東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編者按:學習當以自學為主,而自學又以讀書為主。讀書多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學習的成果和學問的積淀。這里選錄東北師大附中語文特級教師孫立權平時讀書后寫的心得體會三十則,繼上期刊發十六則后,本期再刊發十四則,雖片言只語,于讀書而言則啟人智慧,發人深省。
(十七)“懵讀”之重要
少年時代懵懵懂懂、似懂非懂、懂一些還有許多不懂的,甚至帶有誤讀的閱讀,我稱之為“懵讀”,這是影響一生的揮之不去的閱讀。
(十八)學習書面語言的正途
看影視戲劇,固然能學語言,但非學語言的正途。通過讀作品學語言,直擊文字本身,才是學習書面語言的正途。影視戲劇的語言是演員表演出來的,它直觀、具體,而文字作品中的語言是指代符號,讀者先要在心里“還原”它。這“還原”的過程對讀者思維的發展、語言的發展至關重要。
(十九)讀完去干什么
我在農村長大,小時候能見到的圖書極其有限。正因為書少,讀到一本自認為很好的書,總想一口氣讀完,連吃飯甚至天色暗了伸手去開燈都認為耽誤時間(我的眼睛就是這樣近視的)。但當這本書讀得沒剩幾頁的時候,又會產生恐懼:讀完去干什么——現在想來,那情景歷歷在目,仍使我感到意味無窮。
(二十)讀文學作品當能感同身受
宋人嚴羽讀《離騷》,“歌之抑揚,涕淚滿襟”。清人盧世潅讀杜甫的詩,“肝腸如火,涕淚橫流”。我當年讀雨果的《悲慘世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數次淚流滿面。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把心交給我們,我們焉能無動于衷?作者敞開心扉向我們細訴衷腸,我們當和他們一同喜怒哀樂。
(二十一)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來讀
閱讀別人的作品要和閱讀自己的生命相結合。在一定意義上,閱讀追求的是讀者個體的自我理解,是從閱讀對象那里找到自己,即通過理解他者來理解自己。讀者是在尋求理解的基礎上使自身體驗與文本意義同化,參與文本意義的建構,從而化文本的意義為自我的意義,化文本的世界為自我的世界,從“他人的世界”(文本)中發現“自己的世界”,在“你”中發現“我”,這就是古人說的“我與文化,文與我化”的境界。所以,老師須引導學生在閱讀中發現和創造自我。教別人的作品要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來教,學別人的作品要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來學。閱讀教學不能像“新寫實主義”那種文藝思潮所主張的,拒絕主觀情感,反激情,對敘述對象不做任何價值判斷,即所謂“零度寫作”“冷面敘述”。這種主張絕不能引入閱讀教學,不能進行“零度閱讀”“冷面閱讀”。恰恰相反,閱讀教學中最需要師生的主觀激情、人生體驗和價值判斷。《紅樓夢》第四十八回“濫情人情誤思游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中說到香菱向黛玉學詩的事,其文曰: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里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要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和‘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才形容的盡;念在嘴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似的。還有:‘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這‘余’字和‘上’字,難為他怎么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做晚飯,那個煙竟是青碧連天。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香菱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會閱讀的典范。她讀王維的詩歌,初讀時覺得無理,用字也俗,但結合自己的人生經驗去讀后,才體會到字里行間的妙處。
(二十二)允許“誤讀”
應該允許閱讀教學中學生對課文的“誤讀”。每個人只能按照自身的認識程度、思維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人們原有的“視域”決定了他的“不見”和“所見”。所以“誤讀”是客觀存在的。“誤讀”不一定就是“不懂”“歪曲”,它常常是一種新的理解、新的發現。茅盾先生當年讀尼采時就產生過“誤讀”。例如尼采提出“權力意志”,即人類生活中最強的意志是向往權力,而不只是求生。從德國人的角度看,這就意味著:“我愿成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權力的人對于較低級的、無權力的人們可以像“對待蚊蟲一樣,擊斃它,并無任何良心的悲憫”。茅盾卻是這樣解讀的:“惟其人類有這‘向權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隸來茍活,要不怕強權去奮斗。要求解放,要求自決都是從這里出發。倘然只是求生,則豬和狗的生活一樣也是求生的生活。”茅盾的解讀和尼采的原意相差甚遠,屬于“誤讀”,但這種“誤讀”是有價值的。如果學生閱讀課文時產生這種有價值的“誤讀”,我們應給以肯定。
(二十三)課下自由閱讀是更重要的語文學習
擺脫了師長父母管束的課下自由閱讀,能讓孩子們在書中尋找完全屬于他們自己的答案。這是人生啟蒙期中的精神漫游。這是課內讀書生活所無法比擬的。為人師長父母者務必要認識到課下自由閱讀也是語文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語文學習。
(二十四)經典課文的三種讀法
經典課文有三種讀法。一種是站在前人的立場上讀,謂之“歷史讀法”;一種是站在今人的立場上讀,謂之“時代讀法”;還有一種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讀,謂之“個人讀法”。任何閱讀,都離不開這三種讀法。而目前語文教學中最缺乏的是“個人讀法”。
(二十五)同是詠蟬,比興不同
虞世南、駱賓王、李商隱都是唐代詩人,他們都寫過“蟬”詩。
蟬
虞世南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注釋】垂緌:緌是古人結在頷下帽帶的下垂部分。蟬的頭部伸出的觸須,形狀如下垂的冠纓,故稱“垂緌”。流響:不停地鳴叫。藉:依賴。
在獄詠蟬
駱賓王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注釋】西陸:借指秋天。《隋書·天文志》中說,太陽周天而行,“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南冠:借指囚犯。《左傳·成公九年》載: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鐘儀:南方楚人,著楚冠,故曰南冠。后世遂以之代囚犯。玄鬢影:本指黑色的鬢發,這里指黑色的蟬。獄中的駱賓王看到黑色的蟬自然想到自己的白頭。
蟬
李商隱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注釋】以:因。費聲:指蟬聲頻頻。“徒勞”句是說,蟬悲鳴不已,卻不受理睬,因而寄恨無窮。疏:指蟬聲稀疏。薄宦:俸祿微薄的官職。梗:樹木枝條。泛:漂流。“梗泛”常用來比喻漂泊無定的生涯。警:警醒,觸動。舉家清:舉家蕩然,一世清苦。
三人同詠蟬,即是說選擇了相同的審美對象,也都以蟬自況,但表達的思想感情卻很不相同。虞世南強調立身品格高潔的人,并不需要某種外在的憑借,自能聲名遠播。駱賓王在表明自己高潔的同時,更是哀嘆自己含冤莫辯的艱難處境。李商隱實是抒發位卑寄人籬下的感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不同?清代學者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說得好:“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就是說,因為這三個人的人生境遇不同,人生體驗有別,所以面對同一審美對象,會賦予不同的審美情感。
(二十六)不同文化背景影響文章解讀
美國學生聽中國老師在課堂上講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他們對把三仙姑打扮的行為(“已經四十五歲,卻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腿上仍要鑲邊”)極力丑化和辛辣諷刺表示無法認同。他們認為三仙姑大膽追求幸福的行為無可非議。這種解讀態度,在中國學生中很難找到。可見,不同文化背景帶來的不同審美心理會使其對作品做出不同的解讀。這也啟示我們在教學中不應只重視“上下文語境”,也要重視“歷史文化語境”。英國的學者瑞恰茲在《論述的目的和語境的種類》中對傳統的語境的概念進行了有效擴展,認為語境可以擴大到包括與所要詮釋對象有關的一切事情,包括社會環境、語言習慣、民風民俗等。這就從“上下文語境”擴大到“歷史文化語境”。
(二十七)劉邦與項羽
劉邦活在政治里,項羽活在文學里。劉邦有政治價值,項羽有審美價值。生前,劉邦戰勝了項羽;死后,項羽戰勝了劉邦。項羽是“鬼雄”,項羽廟遠多于劉邦廟。
(二十八)高俅父子“貢獻”很大
因要給學生講《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昨晚翻開《水滸》,把林沖的故事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看著看著,我忽然覺得高俅父子“貢獻”很大,他們居然把一個安分守己、規規矩矩、忍氣吞聲、委曲求全的人“改造”成了合格的造反派,鐵桿的梁山好漢,讓一個無敵忍者變成了怒目金剛。正是像高俅父子這樣的居上位者源源不斷地為梁山輸送優秀人才。
(二十九)說“回也不改其樂”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這里的“樂”不是樂于身處陋巷、簞食瓢飲,不是以苦為樂。痛苦就是痛苦,不是快樂,苦本身不是快樂。誰都希望改善物質生活。注意原文是“不改其樂”,就是說,貧窮困苦的生活不能改變顏回原來就有的“樂”。這原來就有的“樂”是什么呢?當然是“樂道”。堅守純粹的學術品格,保持獨立的人格操守,即使在苦中也不改其某種精神追求的快樂。這才是中國“樂感文化”的要義。
(三十)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兩句話中的“學”和“思”,我是教書多年才忽有所悟的:“學”說的是“是什么”和“如何做”,即“what”和“how”,而“思”說的是“為什么”,即“why”。這兩句話是說:整天在那里死記硬背這是什么,那是什么,人家怎么說,你就盲目地跟著做,不用長在自己肩上的屬于自己的頭腦思考,孔子認為這樣會“罔”,即被欺騙;而整天苦苦思索“為什么”,卻不去記“是什么”,不去跟別人學,不去行動,孔子認為這樣會“殆”,即有危險,走火入魔。只有把“學”和“思”結合,把客觀考察與主觀冥想結合,把實踐與理論結合,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才能真正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