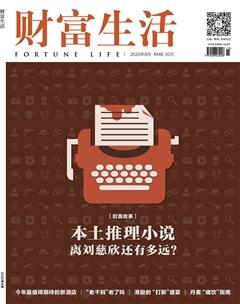稻米安全說“糧倉”

仲富蘭
當前全球抗疫,糧食安全一直是人們最關心的話題。幾千年以來,導致人類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直沒有變過,它們分別是饑荒、瘟疫和戰爭,而且,瘟疫常常與饑荒與戰爭相關聯。一千年前的一場大疫后,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寫道:“門薪饋無米,廚灶炊無煙”“未敢扣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那場面令人心痛!大疫之后必有災荒,糧食安全始終是歷朝歷代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中國人的歲時節令,每年正月廿五有“填倉節”,有的地方農歷二月二是“天倉節”,二月二是龍抬頭的日子,這個日子離春耕播種的季節很近,所以農家在這天“填倉”,是祈愿新一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作為魚米之鄉的江南,自古以來,就流傳著“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太湖流域的稻作文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讓太湖岸邊成了天下的糧倉。很多地名都跟糧食有直接關系,比如蘇州的太倉,其本意就是帝王的糧倉,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在今太倉位置設倉囤糧,當地故得名“太倉”。在江南各地的地名中,以稻米和糧倉作為地名的,不計其數。
地方志書上稱糧倉為“倉庾”?其實,“倉庾”就是古人對“糧倉”的別稱。《史記·孝文本紀》記載:“發倉庾以振貧民。”唐代大詩人杜甫《暫往白帝復還東屯》:“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唐代居住在江南的詩人陸龜蒙《祝牛宮辭》說:“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宋代政治家又是文學家王安石《感事》:“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清代昭蓮《嘯亭雜錄·理足國帑》說:“每令直省將天下正供糴米隨漕以入,故倉庾亦皆充實。”可見,古人對于糧食儲備、建好糧倉都極為重視。
明代上海曾有兩座水次倉,一座在唐行鎮,明萬歷元年(1573年),析上海和華亭縣部分置青浦縣,這個“唐行鎮”就成了青浦縣治,所以《上海縣志》中講:“唐行鎮,今隸青浦。”另一座在上海縣小南門外靠近黃浦江的地方,這里有兩條黃浦的支流,一條是陸家浜,另一條是薛家浜,可以從黃浦直達南水次倉,如今這里尚有南倉街、外倉街、多稼路、府谷街,均為這個南水次倉留下的地名。清末人秦榮光著《上海縣竹枝詞·渡橋》中說:“浦闊無梁阻旅行,沿灘渡口有船橫。民捐官設都稱義,普濟東西往返程。”
明清時期,由于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歷代的漕運,皆依托蘇州綿密的水運網絡運到蘇州城內糧倉儲存,而后由蘇州發運北上。那個時候,蘇州是國家漕糧的重要征集地和起運地。明代,巡撫周忱和知府況鐘,為加強對漕糧的管理,把原本分散在各縣農村的糧倉,分別移建到蘇州城內婁門和閶門一帶。這些糧倉不僅靠近城門,而且糧倉前后都開有門,每個門都臨水。蘇州城內的河道可通漕船,這就為漕糧的收集、存儲和運輸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