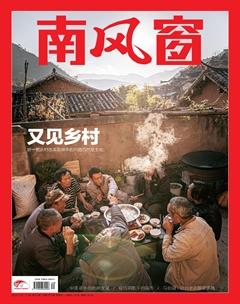流量時代的公眾號學術
趙英男

互聯網時代,往往顏值即正義,流量是真理。伴隨著微信逐漸成為我國頂級流量入口,可以評論、可以分享、可以“在看”的公眾號文章,成為日益走入“三天可見”狀態的朋友圈的唯一亮色。眾多學術期刊、研究機構以及學者個人,自然也愿意抓住這個風口。微信中的學術公眾號和學術文章,成為了這個充滿小哥哥小姐姐、風景美食與勵志雞湯場域中的一道獨特風景。今年由于疫情,大量講座、會議、課程都轉戰線上,學術與流量,更成為了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
用作流量的方法來推廣學術,其實好處蠻大。比如,絕大部分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章,其實并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般艱深。一些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經典作品,甚至可以說妙趣橫生。雪藏在嚴肅呆板的期刊中,可能即便專業研究者也懶得去翻看。但經過公眾號節選或全文轉載,再加上好玩兒的標題、有趣的圖片以及精心排版過的頁面,火到成功“破圈”還真不算難事。這算是無形當中通過互聯網實現了知識普及。十多年前的“百家講壇”節目曾說“學者讓電視深刻,電視讓學者有為”,這個關系用在學術與公眾號上,同樣成立。還有,學者基于自己的背景知識與身份,往往可以觸碰一些記者或自媒體運營者不愿說或無法說的現象或觀點,使得一些原本受到遮蔽的問題得到了應有關注。
不過,從學術角度來看,公眾號與學術的結合未必沒有問題,甚至弊端多多。這大概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流量并不生產學術甚至與學術的生產邏輯相反。流量追求的是轟動爆炸,是黑白分明,是從“腰部”發力直達“頭部”,是今晚發出帖子明早就能“10萬+”。但學術并非如此,觀點一定要鮮明,但最忌非黑即白的簡單粗暴,最忌愛憎分明的情緒表達。兩者擰成一股繩,勢必會導致一方不得不服從于另一方的邏輯。因此流量與學術的結合,很多時候可能既沒有引來流量,也沒有傳播好學術。
其實大多數學術公眾號運營者或許已經發覺了這個問題。他們的應對之道就是兩個方案:找大佬和追名校。學界耄耋自然“人高言重”,莫說論文,單是一篇講話、訪談乃至致辭,都不乏一波流量收割;名校更是如此,著名學府的西紅柿炒雞蛋漲了一毛錢都有上熱搜的潛質,著名學府的著名教授囑咐學生好好讀書也可以成為“今日主推”。但這其實加劇了學術場域內的馬太效應,固化了學術圈內既有的差序格局。在公眾號中高曝光的教授和院校,能夠或多或少地享受到流量變現的紅利,但普通學者和普通院校卻并沒有這般幸運。這是公眾號興起的八年來對于學術場域最大的改變:網絡聲量的大小,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現實中資源的多少。當然,我們可以說在這樣一個平民化的時代,有多大本事吃多大口飯。但問題在于學術資源的分配,應當取決于學術本身,而非其他因素,盡管學術因素本身也未必多么純粹。
學術公眾號的本質不是生產學術,而是利用學術生產來為自己增值。比如,一些知名公眾號不時會推出高校科研排行榜、知名學者引用率、核心期刊發表數等統計。這些數字對于學術進步缺乏意義,對于知識普及沒有作用,除了增加公眾號關注外,就是制造學者和院校的焦慮,將教育部一再批評的“論文至上論”改頭換面的偷渡進來。又比如,學術公眾號也給年輕學生一種錯覺,以為學術等同于寫一本好賣的書、去知識付費平臺講幾次課、通過網絡說一些悲天憫人且勸人坐冷板凳的話等。這讓學術不再是學者和院校的學術,而是網絡公眾平臺背后資本頭腦中理解的學術。面對此情此景,我們就不要再問:洶涌的流量時代,這一切還會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