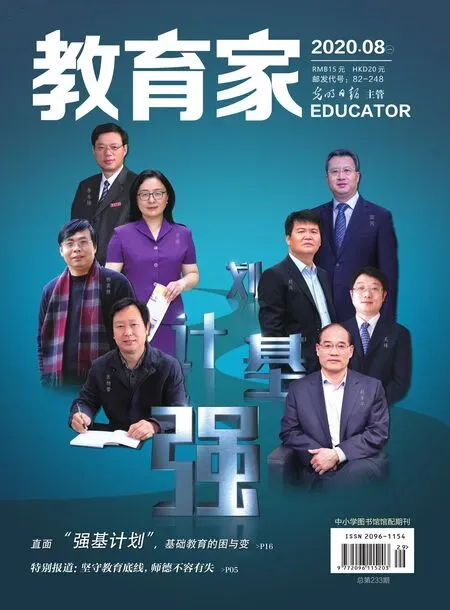“野性”的日本學校體育
近年來,每當有日本學者榮獲諾貝爾獎,日本媒體和公眾會更關注獲獎者的生活經歷和業余愛好,對他們的運動偏好和中小學時參加的體育社團尤其好奇,這反映了日本崇尚體育的社會風氣。例如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京都大學教授山中伸彌,學生時期參加過柔道、橄欖球、長跑等運動社團,2011年,曾以4小時29分53秒的成績跑完大阪馬拉松;2020年(57歲),參加京都馬拉松,又將成績提高到3小時22分34秒。
日本的《體育基本法》表達了“通過體育運動,過上幸福而富裕的生活是每個人的權利”的觀點,體育與讀書、創作、旅游、交友等一樣,成為日本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是生活的重要部分。日本崇尚體育已成為一種社會文化,這與學校體育的蓬勃發展密不可分。
學校,日本現代體育的傳播地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體育運動,在武士文化的影響下,學習武術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武士文化追求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等內在品格,重視外在美感。這一傳統對日本現代學校體育影響頗深,不僅劍道、弓道、柔道等傳統項目仍在學校體育中占據重要位置,其他的現代體育項目也重視儀式感、注重精神品質的培養和文化的熏陶、講求一絲不茍、倡導“干什么像什么”。即使在裝備、服裝等物質層面的體育文化方面,日本學校也要求嚴格。
明治維新以后,學校成為傳播包括體育在內的現代文明的主要場所,西方很多體育項目通過學校傳到日本,進而普及整個社會。廣受日本人喜歡的棒球運動,是1871年由一位到日本教英語的美國人霍勒斯·威爾遜傳入的;日本孩子最喜歡的運動之一閃避球,是1909年可兒德和坪井玄道這兩位日本人通過《小學校運動游戲》一書介紹到日本的。
直到現在,學校仍是現代體育的重要傳播地。學校能發揮這樣重要的作用,既因為它配備操場、體育館、游泳池等體育設施和相對專業的體育器械,也由于學校的體育課、運動會、體育社團等課程活動眾多,這些不僅是青少年學習體育技能與文化的主要途徑,也是他們通過體育發展個性、習得社會性的主要渠道。
保持體育課的“野性”
體育在日本幼兒園屬于“健康”課程的組成部分,沙堆游戲、水中游戲、攀爬游戲、跳躍游戲等都屬于孩子們進行身體運動的方式。筆者在日本歷史最悠久的幼兒園——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幼兒園交流時,曾旁聽過孩子們的運動課,至今印象深刻。一部分孩子把積木箱壘到1.6米左右的高度,拖了一些墊子鋪在周圍,然后排著隊爬上積木箱再跳下去,教師則在一個角落默默地做觀察記錄;另一部分孩子則在戶外的淺水池玩水,他們一會兒跳進水里,一會兒跑到沙堆上,個個滿身泥濘。我問幼兒園教師:這樣孩子會不會感冒?弄得這么臟家長會不會有意見?老師回答:開始的時候總有孩子會感冒,但慢慢就適應了;游戲總會弄臟的,這也是一種鍛煉,孩子們帶了換洗衣服,家長們也都理解。
小學階段,“體育”學科出現,旨在培養學生基本的運動習慣和體育技能。日本小學的體育課會組織一些在我們看來風險較高的運動項目,如一年級的小學生可通過水中游戲進行游泳基本技能的訓練,此外,他們還有跳箱課程,每個小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跳箱(三到七層箱子)自主練習,一堂課下來,約一半的孩子可以輕松跳過七層箱子。教師只是從旁觀察,并未安排特別的保護措施。有的學生因為技術不熟練從箱上跌落,會默默爬起重新挑戰,在場觀課的家長并未對此提出異議。
初中和高中階段,學科名稱改為“保健體育”。由此可知,這一學科內容分為兩大部分,除了體育技能外,還有保健知識、體育理論、社會衛生政策等。
學校體育與社會人的休閑體育不同,其主要目標是培養人,因此總會有意識地讓兒童和青少年接受不同程度的磨煉。毛澤東同志在103年前所著的《體育之研究》中提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現在,雖然需要格外重視學生在校的安全問題,但盡量保持“野性”,仍應是學校體育本來的面貌。
團體主義運動會與“部活”
運動會是日本學校不可或缺的重大活動,往往需要準備一兩個月的時間。一般小學稱為“運動會”,初中及以上稱為“體育祭”或“體育大會”等。在小學運動會中,全體學生要參與幾乎所有的項目,除了接力賽等少數項目由選手參加。所有家長要全程觀戰助威并參與部分項目。學校運動會的意義已超越體育本身,成為促進社區團結和家庭和諧的重要途徑。還有日本學者認為,學校運動會在促進日本現代國民意識形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運動會注重團隊精神,運動會的項目以集體項目為主,個人項目被壓縮在很小的范圍。學段越低,這一傾向就越明顯。很多諸如二人三腳、疊羅漢、拔河等集體項目并不是競技體育賽事的項目,卻在學校運動會上“唱主角”,只因它們是有利于培養團體合作精神的傳統項目。實際上,疊羅漢風險很大,參賽者摔傷、壓傷的情況屢見不鮮,項目廣遭詬病,不少地方已經廢止,但仍有很多學校“我行我素”、堅持至今,這些學校大多是出于培養個人意志品質和團隊精神的考慮。
日本中小學的社團活動被稱為“俱樂部活動”,簡稱“部活”。運動部在學校社團中分量很重,不同學校的俱樂部有自己的傳統和特色,高中社團尤其活躍,優勢部活甚至會成為學生報考學校的重要吸引力。很多學校出于鍛煉教師、人員不足等原因,讓沒有體育專長的教師管理體育社團、指導部活,占用了教師大量的課余和周末時間,給他們帶來了負擔,卻也從側面說明了日本學校中體育社團之繁盛。社團和部活普遍跨年級,成為不同年級學生建立縱向聯系的紐帶。有研究者認為,學校社團是日本形成“前輩”“后輩”觀念的主要原因之一。
學校體育對日本社會影響最大的賽事非“甲子園”莫屬。“甲子園”是指每年在阪神甲子園棒球場進行的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日文直譯為“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是震動全日本的重大活動。從1915年到2019年,“甲子園”已經舉辦了101屆,每年全日本共4000多所高中參與競賽,只有49支隊伍進入甲子園參加決賽。萬眾矚目的“甲子園”大賽為正值青春的高中生提供了揮灑汗水和熱血的逐夢機會,很多有天賦的運動員在此嶄露頭角,讓整個社會看到年輕人的力量,也為專業運動團隊提供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
日本的經驗再次說明,要把以“保命”為目的的被迫養生變為以提高個人生活質量為目的的終身鍛煉、讓體育運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要從兒童和青少年抓起,扎扎實實地發展學校體育。在今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人大代表、中國國家女子排球隊員朱婷和張常寧的提案獲得了廣泛關注——朱婷提出體育的“關口”應前移到學齡前兒童,張常寧則提出要重視普通高校高水平運動隊建設,她們的側重點雖有不同,卻都在呼吁關注校園體育。毫無疑問,這也符合新時期教育改革和學生綜合素質培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