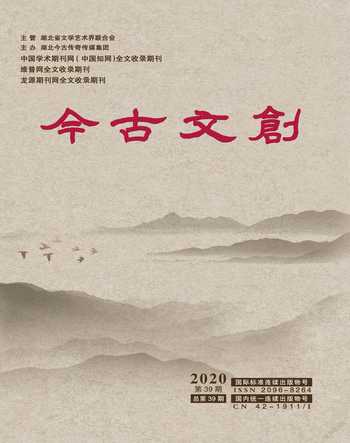淺談延安時期陜北秧歌劇的藝術特征
【摘要】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文藝工作者們走出“小魯藝”,走進“大魯藝”,開創(chuàng)了全新的文藝創(chuàng)作模式,在陜北傳統(tǒng)秧歌的基礎上改造創(chuàng)新,為宣傳抗戰(zhàn)起到了積極作用。通過追溯秧歌劇由來、舉例分析秧歌劇內(nèi)容,總結(jié)出秧歌劇具有政治性、民間性、群眾性、時代性、大眾化的藝術特征,這些藝術思路均深刻影響著此后中國文藝研究工作的發(fā)展。
【關鍵詞】 陜北秧歌劇;創(chuàng)作題材;藝術特征
【中圖分類號】J72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39-0060-03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為廣大文藝工作者們指明了一條全新的文藝創(chuàng)作道路,在傳統(tǒng)秧歌的基礎上改造創(chuàng)新,發(fā)展出了一條讓大眾喜愛的文藝路線。延安秧歌劇是特定時代環(huán)境中的產(chǎn)物,其藝術特征深刻影響著此后中國文藝研究工作的發(fā)展。文章通過對秧歌劇的由來、秧歌劇的表現(xiàn)內(nèi)容進行梳理,從而總結(jié)秧歌劇政治性、民間性、群眾性、時代性、大眾化的藝術特征。
一、秧歌劇的由來
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之所以改造秧歌,是因為這種民間藝術形式在陜北有著悠久的歷史,并深受廣大老百姓的喜愛,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秧歌在我國北方流傳較廣 ,多見于各地廣大農(nóng)村,它是慶祝民間喜慶節(jié)日時的一種歌舞形式,人們俗稱“鬧秧歌”。人們熟悉的秧歌有“大場”“小場”“過街”這幾種形式。大場秧歌是秧歌隊員們在開場表演和落幕時表演的一種集體歌舞形式。小場秧歌是表演者在大場秧歌開場的基礎上,進行一系列帶有故事情節(jié)的歌舞表演,類似演戲的戲曲形式。過街秧歌是秧歌隊在熱鬧的大街上流動演出,通常是伴有一些隊形變化,他們會根據(jù)音樂的起伏變化擺出一些簡單的舞蹈動作。這種樸素而又直接的藝術方式,是秧歌劇發(fā)展的基礎。
(一)秧歌的歷史演變
對秧歌的起源問題學術界各持己見。其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到南宋時期。據(jù)史料記載:“秧歌,南宋燈宵之村田樂也。所扮有耍和尚、耍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漁婦、雜沓燈術,以得觀者之笑。”宋金時期,在陜西省甘泉縣出土的文物中發(fā)現(xiàn)很多浮雕磚刻,其中有部分畫是關于秧歌的畫像。畫像中人物的穿衣風格、面部表情神態(tài)以及舞蹈的造型,都與今天陜北群眾的整體形象很相似,其舞蹈造型與陜北秧歌的表演形式相吻合。由此可推論:秧歌最早出現(xiàn)在民間可以追溯到800年前的南宋時期。秧歌漸漸成為一種群體性的歌舞活動,不但對表演動作和演出所需道具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對于伴奏樂器也有一定專業(yè)性的要求。表演動作形式多樣,其步法包括二進二退、十字扭步等多種步法。演出道具一般以彩扇、彩綢、彩花為主,伴奏樂器通常是吹奏嗩吶和敲打鑼鼓等。
關于秧歌的歷史演變有幾個發(fā)展階段,一是傳統(tǒng)陜北秧歌,始于古代祭祀活動,驅(qū)邪除惡或是祭祀死者。傳統(tǒng)秧歌多出現(xiàn)在傳統(tǒng)節(jié)慶風俗活動中,陜北人民把這種秧歌表演形式稱為“鬧秧歌”。二是陜北新秧歌,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文藝工作者不斷改造傳統(tǒng)秧歌,深入生活,廣泛挖掘民間素材,積極宣傳革命政治內(nèi)容,使之賦予了時代的新內(nèi)涵,以此促成了新秧歌的發(fā)展。
(二)秧歌劇的形成
秧歌劇于20世紀40年代產(chǎn)生,是盛行于解放區(qū)的一種戲劇形式,周揚的《表現(xiàn)新的群眾的時代》一文中所提到的:“它是一種熔戲劇、音樂、舞蹈于一爐的綜合的藝術形式,它是一種新型的廣場歌舞劇。”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解放區(qū)掀起了一場如火如荼的群眾性秧歌運動,其規(guī)模龐大,歷史影響深遠持久。特別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舉行文藝座談會后,延安文藝工作者開始重視民間文藝,結(jié)合人民群眾的現(xiàn)實生活,貼近政治內(nèi)容,使秧歌運動有了更全面的提高和發(fā)展。
1943年,一場盛大的“新秧歌”演出活動在延安舉行,參與其演出的主要是延安“魯藝”的知識青年。該活動在舊秧歌基礎上融入了許多具體的人物形象,如:秧歌劇《兄妹開荒》,該劇以大生產(chǎn)運動作為背景,對人物進行了大膽的革新,并與革命政治內(nèi)容相呼應,這部劇成為了延安秧歌運動的典范,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并且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和支持,這是一首新的“秧歌劇”,彰顯著新時代特點和內(nèi)容。“秧歌劇”內(nèi)容短小簡潔,主題明確,音樂風格純樸有力,民族特色顯著。因為它表達的內(nèi)容貼近人民的現(xiàn)實生活,能把人民的真實生活狀態(tài)體現(xiàn)出來,因此受到了廣大群眾的喜愛和歡迎,此主題內(nèi)容也正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①中所指出:“文藝工作者必須與群眾相結(jié)合”的文藝方針相適應。這些重要特征對中國新歌劇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以《白毛女》為代表的歌劇作品。在這一時期,新秧歌劇劇目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送公糧》《鐘萬財起家》等,這些秧歌劇的誕生,正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的體現(xiàn),也是延安文藝界“整風運動”的成果。
二、陜北秧歌劇的創(chuàng)作題材
新秧歌運動后,秧歌劇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劇增,創(chuàng)作內(nèi)容形式多樣,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從1942年至1945年間創(chuàng)作的秧歌劇達到169篇,按內(nèi)容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鼓勵開展勞動的秧歌劇。1941年,由于延安糧食、物資嚴重缺乏,經(jīng)濟十分困難,因此著手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放在首位,鼓勵人民自力更生,開展生產(chǎn)自救,并對勞動英雄進行獎勵。勞動生產(chǎn)秧歌劇大多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所以深受人民的歡迎。代表作有《兄妹開荒》《鐘萬財起家》《動員起來》等;二是歌頌軍民魚水情的秧歌劇。在這類劇作中,歌詞內(nèi)容豐富,主題鮮明,有對上前線打仗的軍人進行歌頌的、鼓勵參軍者立功殺敵的;有宣傳慰勞部隊、關心軍屬的;也有表現(xiàn)軍民情意深重的、歌頌軍民團結(jié)一家親的主題。如《志愿當紅軍》《送郎參軍》《送公糧》《軍愛民,民擁軍》等;三是頌揚新生活的秧歌劇。它是表現(xiàn)新中國成立后農(nóng)民翻身做主,歌頌我們的共產(chǎn)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功勞為主題的秧歌劇,體現(xiàn)新中國成立后美好的新生活場景,這類劇作反映人民當家做主,反映人民真實生活水平,在秧歌劇中占有較大比重。如《爭年畫》《翻身年》《夫妻識字》《栽樹》等;四是反映階級斗爭的秧歌劇。這類秧歌劇主要是為了鼓勵群眾大膽進行階級斗爭運動,是群眾真實生活的反映。如《挖壞根》《自衛(wèi)隊捉胡子》《徐海水鋤奸》等,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階級敵人丑陋的一面,他們想方設法暗地搞破壞,最終還是沒能躲過群眾雪亮的雙眼,被揭穿真面目并對其進行斗爭的事實,體現(xiàn)出了地主階級虛偽的嘴臉和狼狽不堪的下場;五是描寫軍旅生活的秧歌劇。此類劇作劇情短小精悍,多表現(xiàn)部隊生活,描寫部隊精神等方面內(nèi)容。從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階級對立的本質(zhì),時刻不忘初心、教育和呼吁戰(zhàn)士團結(jié)一心,要勇于同壓迫自己的階級敵人進行英勇的斗爭。這類題材的代表作有《一個解放戰(zhàn)士》《劉順清》《爭取勇猛班》《慣匪周子山》等。
根據(jù)對秧歌劇簡單的整理分類,我們可以看出秧歌劇的內(nèi)容題材都是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正是因為其內(nèi)容貼近解放區(qū)的人民生活,引起了人民群眾思想感情上的強烈共鳴。這些作品在以藝術的形式向人民傳送愉悅、憤怒、悲壯、勇氣等思想的同時,也發(fā)揮著動員群眾、堅持抗戰(zhàn)、鼓勵發(fā)展生產(chǎn)、實現(xiàn)人民民主以及擁軍愛民的社會功能,是革命宣傳的有力媒介,在當時延安革命運動的推動下蓬勃有力地發(fā)展起來。
三、陜北秧歌劇的藝術特征
(一)秧歌劇中的政治性
延安時期的秧歌劇無論是創(chuàng)作上還是表演上均具有強烈的政治話語表述,其宣傳內(nèi)容與當時的政治主題結(jié)合緊密。如《兄妹開荒》,它是透過兄妹之間在拓荒勞作過程中幽默的談吐對話,成功地塑造了根據(jù)地青年們踴躍勞動的形象,在大生產(chǎn)運動中人民群眾高漲的勞動熱情和布滿朝氣的革命精神,形象地還原了在毛主席的率領下,根據(jù)地人民積極開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的大生產(chǎn)運動;《鐘萬財起家》向人們描述了一個吊兒郎當、好吃懶做的二流子鐘萬才,經(jīng)由村主任的屢次耐心疏導,從一個懶漢逐步轉(zhuǎn)變?yōu)樯线M、吃苦、勤懇的好青年。該劇讓有此行此舉的二流子們心中感到萬分羞恥和慚愧,從而讓他們意識到改邪歸正的重要性。該劇目把黨的領導方針、政策及立場形象地表現(xiàn)了出來;《夫妻識字》這個劇目以夫妻二人互教互學的形式,向人們傳輸學習文化的重要性,向人們展示了根據(jù)地廣大勞動人民積極學習文化知識,追求進步的新面貌。其政治意義旨在宣傳學習文化知識的必要性,及掃除文盲的文化工作等。
(二)秧歌劇中的民間性
陜北秧歌劇其故事原型都是傳統(tǒng)的民間傳說或是革命實踐中的真人真事改編而成,采用民間化的語言,通俗易懂,而且內(nèi)容大都是與民眾的實際生活緊密相連的,甚至都是大眾親身經(jīng)歷過的,很能引起受眾的共鳴,所以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如: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這類近似詩歌的秧歌劇,借鑒了陜北信天游的模式,乃至詩歌中有直接援用當時的信天游作為樂句, 所以,《王貴與李香香》不但以陜北方言作為基礎,并且大部分句子構造都是陜北方言的結(jié)構,劇目比較大眾化,簡潔明了。
(三)秧歌劇中的群眾性
在秧歌劇中,不論是反映哪種題材,比如:生產(chǎn)勞動、家庭生活、軍民關系、階級斗爭等,工農(nóng)兵大眾始終是劇中的主人公,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大多是群眾的日常生活狀況和革命斗爭形態(tài),都在群眾中成為膾炙人口的藝術形式。與舊秧歌相比,新秧歌劇不僅僅保留了原有的基本風格,還從形式,甚至內(nèi)容上都有了飛躍性的發(fā)展,為人民大眾所接受。秧歌劇的蓬勃發(fā)展,對于解放區(qū)來說是一場戰(zhàn)時的革命任務,且完成質(zhì)量特別好。不僅喚醒群眾的政治意識、也調(diào)動了群眾的生產(chǎn)生活、革命、斗爭的積極性,實現(xiàn)了文藝與群眾的真正結(jié)合,實踐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思想。如:《擁軍花鼓》中,當廣場中央的演員高聲喊道“豬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這句歌詞時,旁聽的觀眾就會很自然地齊聲回應道:“送給咱親人八呀路軍。”在這種環(huán)境之下,通過如此簡短的即興唱和就能給人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那是觀眾們愛戴擁護、歌頌八路軍,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的情懷。這也恰好是秧歌劇的魅力,它的群眾性力量就表現(xiàn)在這里。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廣為流傳,歷久彌新,正是因為它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代人民發(fā)聲,在人民中間有著龐大的群眾基礎。
(四)秧歌劇中的時代性
陜北秧歌劇在敘述策略與故事原型上大多采用傳統(tǒng)的大團圓敘事、夫妻逗趣、申冤報仇等模式與原型。但是,這些模式與原型被冠以全新的內(nèi)容,即“舊瓶裝新酒”,如:《擁軍花鼓》,它是一首新民歌,運用民間曲調(diào),在此基礎上填入新的歌詞。學界一般把這個曲調(diào)來源當成是陜北民歌《打黃羊》,此中鑒戒融會了民間秧歌“小場”的一些演出形式,再填上軍民革命題材的歌詞,用“舊瓶裝新酒”的方法,與廣大群眾的審美需求達成統(tǒng)一。正是因為文藝工作者們領悟到音樂是面向大眾的,具有時代性的藝術,所以才會有更明確的創(chuàng)作方向,創(chuàng)作出更多與時俱進的作品。
(五)秧歌劇中的大眾性
“大眾化”是現(xiàn)代文學思潮上非常重要的一條脈絡,隨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fā)表后,“大眾化”才從話語方面成功轉(zhuǎn)換到實踐上,從如何構建大眾化文藝的具體方法、步驟等細節(jié)問題,展開進一步的探討和具體實踐。延安秧歌劇在大眾化上的實踐和對大眾化的重建,無疑是秧歌劇成熟的標志性成果之一。這不但是對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或權力的認可,更是群眾認可信息的直接反饋。在眾多創(chuàng)作的秧歌劇當中,有眾多優(yōu)秀的作品得到人民的廣泛傳播,對于大型民族新歌劇和新話劇的發(fā)展,它是一個奠基石,又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民族新歌劇《白毛女》的問世,正是大眾化成功的例證。
四、結(jié)語
秧歌劇是在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當中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其適應了時代和人民群眾對藝術的要求與渴望。通過對陜北秧歌劇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梳理、回顧,發(fā)現(xiàn)其深具政治性、民間性、群眾性、時代性與大眾化的藝術特征。這些藝術特征與當時的政治語境密不可分,其藝術精神內(nèi)核與大眾文藝緊密聯(lián)系,對于當下的文藝創(chuàng)作具有深刻的指導作用。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發(fā)展,大眾文藝的創(chuàng)作根基始終來源于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與情感。在新時代文化影響下,文藝工作者更要踐行既有“陽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這一創(chuàng)作精神,創(chuàng)作群眾性與藝術性并存的優(yōu)秀作品。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diào)整期間,當代中國也正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新時期階段,正面臨一個難能可貴的歷史機遇,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順應時代要求,以人民為中心,主動為人民抒寫,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用濃墨重彩為民族立言、為時代立傳、為人民放歌。
注釋:
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參考文獻:
[1]汪毓和.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346-351.
[2]陳晨.延安時期的新秧歌運動[J].文史精華,2003.
[3]計曉華.延安魯藝時期秧歌劇的創(chuàng)作與啟示[J].樂府新聲,2012.
[4]張庚.《秧歌劇選》后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5]任秀蕾.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鑒賞[M].北京: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出版社,2013:221-225.
[6]楊琳.重構民間性與大眾化:延安時期秧歌劇的革新與傳播[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7]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32-251.
[8]冉思堯.延安時期的日常社會生活[J].文史精華,2012.
[9]王培元.抗戰(zhàn)時期的延安魯藝[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276-301.
作者簡介:
周超男,女,漢族,重慶合川人,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音樂)課程與教學論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