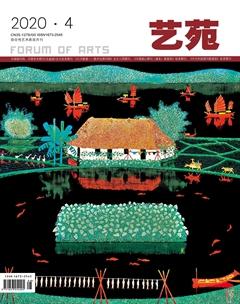《古田軍號》: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突圍與文化創新
賴寧娜 蘇文健

【摘要】 《古田軍號》作為新時代主旋律電影之一,打破了傳統主旋律電影注重說教的固有模式,立足于“講好故事”這一電影藝術的本質,在還原歷史真實性的同時,又結合了戲劇矛盾、立體人物形象刻畫、美學構圖布景等藝術性表達手法,創新了紅色歷史敘事的表達方式。《古田軍號》成功地將“古田會議”的歷史價值與傳承紅色地域文化相融合,為紅色記憶注入了當代活力,使這段蘊載紅色地域文化的歷史更加具體真實可感。影片對福建電影產業發展、傳播福建形象意義重大,為福建紅色文化旅游產業的跨界融合發展及福建文化軟實力的提升都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關鍵詞】 《古田軍號》;主旋律電影;歷史敘事;藝術表達;文化創新
[中圖分類號]J90? ?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我國電影產業化、商業化模式的發展轉型升級,主旋律電影已逐漸呈現出多元化風格。近年來,致力于探索敘事技巧與藝術表達、藝術審美與商業運營兼顧的類型化主旋律電影不斷涌現,如《戰狼2》將愛國主義與動作戲相結合,贏得廣大觀眾的喜愛;以“湄公河慘案”為原型的《湄公河行動》的公安影視作品,較好地影像化當時的慘案真相;由“也門撤僑”事件改編的《紅海行動》打破個人英雄主義,將軍事題材影片推向新高度。這些主旋律電影在強大的主創團隊運作下,取得了政治、藝術與商業的多重成功,成為近些年電影產業發展的重要文化現象。其中,紅色題材電影《古田軍號》也在“古田會議”召開90周年及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獻禮上映。該片的敘述視角一改慣用的宏觀敘事手法,采用以小見大的微觀敘事,引發了觀眾強烈的情感共鳴[1],以其建立在真實歷史基礎之上的藝術創新與審美表達[2]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贊賞。影片也先后榮獲“五個一工程”獎“特別獎”、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配角”“最佳音樂獎”等獎項。
值得關注的是,《古田軍號》對紅色地域文化的藝術渲染頗具文化創新性意義。影片以“古田會議”為史實基礎,將宏大歷史題材與古田當地的生活常態相結合,實現在宏大與微觀之間的轉換與平衡,既講好紅色故事,又兼顧地域性。“福建土樓”“板凳龍”被賦予了新的紅色文化內涵,成為象征“共產黨團結人民群眾”“心齊方可成龍”的地域性符號,對于促進福建紅色文化傳播,及推動福建電影、文旅產業的發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將從敘事模式、人物塑造、文化創新三個方面對《古田軍號》的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進行歸納總結,分析其在歷史敘述與藝術表達方面的雙重突破,并由此思考電影產業對旅游跨界融合而催生新興業態的文化創新之路。
一、顛覆成規的敘事創新
傳統主旋律電影講求宏觀敘事,通過宏偉壯烈的影像場面將紅色主題進行升華。與之相較,《古田軍號》的敘事策略有著明顯不同。《古田軍號》響應時代號召,致力于“講好福建故事”,從小軍號手池有田的視角回憶歷史,由小軍號手之孫來講述這段歷史,將人物的塑造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巧妙運用蒙太奇手法進行層次化敘事、多線敘事,廣泛使用物品和場景的象征意義,讓歷史故事從細節鋪展開來。影片將歷史與現代的發展內嵌互現,營造出強大的視覺震撼,讓觀眾能從今昔對比中感受中國共產黨經歷的艱難曲折與堅守初心的不易。
首先,《古田軍號》一改傳統主旋律電影的宏觀敘事風格,將鏡頭聚焦在宏大歷史背景下的鮮活個體上,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歷史規律的“宏大敘事”,增強了歷史敘事的現實感與真實感。小軍號手跟隨毛主席,親歷了“古田會議”召開前后的過程,影片以故事外的小軍號手之孫作為旁白來敘述歷史,打破了以往歷史題材單一的時間敘事,運用蒙太奇手法將敘述者“我”的現實與親歷者“爺爺”的歷史拼貼在一起,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呼應。土樓、板凳龍等場景符號的多次切換比對,將革命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生活物品的對舉,暗喻著兩個時代生活的不同與新變,從側面體現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與當年黨團結人民群眾的艱苦斗爭密不可分;舞龍場景的前后呼應,很大程度上能增強觀眾的代入感,讓之深切感受到“古田會議”以來的山鄉巨變。過去和現在自由切換,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相互交錯,無形中建構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
自新中國電影“獻禮展映”的電影文化模式開展以來,一直都在向度不一的電影敘事實踐中探尋政治與電影表現平衡點之上的新的敘事范式。[3]從秋收起義毛澤東帶領起義部隊前往井岡山與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會師,到“三灣改編”整頓軍隊、加強軍隊由黨領導的思想建設,再到之后朱毛井岡山會師整編隊伍為“紅四軍”,構成了電影的宏觀敘事背景。而作為軍長的朱德和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在軍民關系、軍隊內部肅整等問題上未能達成共識,爭論時有發生,劉安恭的加入更使矛盾激化,毛澤東只好前往上杭。毛澤東離開后,錯誤的指導思想導致軍隊管理混亂,在戰爭中人員損失慘重,元氣大傷。直到1929年“古田會議”召開,確立了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黨和軍隊建設的中心思想,紅四軍才重新回到正軌。電影以此歷史背景展開微觀敘事,將“朱毛之爭”融入生活細節之處,通過層層矛盾帶來的藝術張力營造了緊張感。讓觀眾在復雜的內外矛盾與危機中認識到會議勝利召開的不易,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紅色故事影視化的創新突破。
其次,《古田軍號》以矛盾沖突推動多線敘事。影片從小軍號手和魏金奎的沖突開始分化為三線敘事,即以整治軍風紀律為主線,小軍號手家族的吹號使命與個人成長為第一條輔線,毛澤東前往上杭開展群眾工作和啟蒙教育為第二條輔線。影片最初以軍隊出現“軍閥作風”問題為切入,代表著舊軍閥作風陋習的士兵魏金奎因被小軍號手撞見抽大煙而對其大打出手,通過個人沖突展現了軍隊存在的不良風氣。紅四軍隊伍中有不少參加過秋收起義的士兵,但他們加入部隊的目的并不單純,只為吃喝不愁,沒有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而斗爭的紅色革命理想,反而做出強取百姓錢財、調戲良家婦女、對戰俘使用暴力等不恥之事。由此展開朱德和毛澤東在軍隊管理上的分歧,這條敘事線在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到來之后,更是愈演愈烈,從小團體內部急劇上升為中央和前委的矛盾,領導人內部內部劍拔弩張。深受蘇聯革命影響的劉安恭,認為中國紅軍應該照搬蘇聯紅軍的理論來實踐,堅持以攻打城市為首要任務,反對毛澤東發動群眾勢力、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主張。這條敘事線,為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而被迫離開埋下伏筆,直到毛澤東回來召開“古田會議”才扭轉了此前軍隊由錯誤指導而造成的慘烈局面。
小軍號手是劇中毛澤東行為活動的主要旁觀者,以第三視角見證了前面兩條敘事線的發展。他見證了毛澤東與朱德、劉安恭二人在軍隊管理和作戰策略上的分歧,以及軍隊管理在毛澤東離開前后的變化對比,也親歷了毛澤東前往上杭辦教育開展群眾活動所取得的成就。同時,小軍號手又不僅僅是一位旁觀者,他肩負著繼承革命事業的責任。小軍號手的哥哥和父親也是吹號手,父兄二人在戰火中壯烈犧牲后,小軍號手接過哥哥手中的軍號,延續著為軍隊吹號的使命,期望吹響一次次沖鋒的號角來換取革命的勝利。
影片注重內部矛盾的敘述,這是導演的勇氣,亦是主旋律電影的突破。雖然故事情節一波三折,但最終多線敘事合一,矛盾在加反對令章加黑邊與最后加黑邊的鏡頭下化解,黑邊的意義也由紀念列寧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變成紀念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中犧牲的同志,銘記軍隊指揮思想錯誤的教訓。故事在中鋪墊的脈絡收束,推動了觀眾的情感升華。電影在紅軍動身遠征中結尾,頗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一敘事內涵。
二、真實可感的人物塑造
在人物塑造上,《古田軍號》將宏大的歷史進行語境化、細節化,通過合情合理的想象與虛構,彰顯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溫情的一面。相對于以往空洞的偉大形象刻畫,影片將歷史的真實融入到鮮活的個體中活動中,并展開符合邏輯的細節補充,使人物塑造變得立體、真實、可感,創新了主旋律電影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這部電影顛覆了觀眾此前對于紅色革命電影、偉人英雄形象的認知,讓觀眾意識到是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其一,細節制勝,以小見大。陳力導演的《湘江北去》《血戰湘江》等主旋律電影均關照宏大歷史背景下的社會現實與人物關系,卻又始終保持著對細節的觀察與捕捉:《湘江北去》中,在圖書館打零工的毛澤東深受陳獨秀的情緒感染,竟不自覺地為其革命信念奔走呼喊,不顧管理員的阻攔沖進館內高聲叫好,彰顯出毛澤東熱血激情、昂揚向上的斗志,這從細微小事入手暗示了毛澤東革命思想的轉折;《血戰湘江》亦是如此,在描繪毛澤東與博古、李德等人激烈爭論的場景時,既通過激烈言辭體現其直率的性格和堅定的革命態度,又以嘆息和沉默的動作反映其內心的糾結無奈。但是,以更加鮮明的姿態運用細節來塑造人物形象,陳力導演的新作《古田軍號》則更進上層樓。影片借助生活場景來展現人物性格及人物關系,將大矛盾體現在微小之處,突顯出毛澤東和朱德作為普通人的一面,煙火氣十足。特別是通過床板隔斷一拉一合等小動作的妙用,展現了朱毛關系的緊張與舒緩。電影還塑造了多位形象鮮明的古田人,在毛澤東離開上杭后,張素娥接過粉筆,終生致力于當地的教育事業,意味著毛澤東在群眾中播下的啟蒙種子得以薪火相傳,黨的事業生生不息,后繼有人;“軍號”這一符號背后的意義也借由傳遞這一動作得到延伸,獨特的傳承精神也寓于其中——“古田會議”精神代有傳人,紅色革命精神薪火不斷。
同時,影片也因對細節的高度關注而突破了主旋律電影中常見的“臉譜化”問題。在《湘江北去》中,陳力著重表現青年的救國熱情與昂揚斗志,正面贊揚敢為人先、奮發有為的精神,但仍不可避免地對毛澤東、蕭子升等正面青年形象進行了過于理想化的刻畫。如影片對毛澤東、陶斯詠、蕭子升之間不同救國理念的沖突展現不足,以無波瀾的狀態走向“正確的革命道路”,諸多富有深度的內容在影片中被淡化,使觀眾難以從影片中理解時代背景下領袖人物的抉擇。但在《古田軍號》中,可以明顯看到陳力的改變,其中的領導人物不再僅僅只是單一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輸出,而是在豐富細節的呈現下更加鮮活立體。如毛澤東和朱德因矛盾而爭吵不休,陳毅夾在兩人關系之間斡旋周轉的刻畫,不回避偉人之間的個人矛盾和治理軍隊理念上的分歧;但是又通過朱德給小軍號手安排做衣服,毛澤東便即刻掏出寫有小軍號手尺寸的紙條遞給裁縫的細節,來凸顯二人相互配合的默契,說明了矛盾也不是絕不可調和。又如在毛澤東和朱德爭論中語言的使用,毛澤東的對白設計注重針對實際情況的分析,而朱德這一角色的語言使用則暗含對蘇聯模式的親睞,以此展現出不同的人物形象。
此外,對劉安恭形象的刻畫也是《古田軍號》的一大突破。影片并未對劉安恭進行以偏概全的評價,而是站在中立立場上對劉安恭的思想堅持和犧牲進行陳述,既沒有猛烈批判,也沒有過度渲染。中國共產黨當時正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轉折期,人在歷史洪荒中前行憑的是堅定的信仰與滿腔的熱血。劉安恭這一人物形象總體上是偏正面的,影片對人物進行了立體多元的審視,形象刻畫不偏不倚,讓歷史鮮活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其二,人物青春浪漫化呼應時代審美。《古田軍號》能吸引大批的年輕觀影群體,得益于其對人物形象的青春浪漫化構建。如何將紅色基因的傳承熔鑄于時代語境之中,打造一部可以“讓歷史照進現實”的年輕化主旋律電影?導演陳力說道:“在新時代如何表現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問題上,我們一直在力求創新和突破,力求宏大敘事與個性表達的融合。”為了和當代的青年人保持同樣的語境,營造代入感,《古田軍號》在故事構架、藝術表達、背景音樂選取、鏡頭拍攝狀態、畫面剪輯等方面都選擇了青年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影片對人物塑造一改傳統紅色人物形象的成熟穩健,將36歲的毛澤東、28歲的陳毅、22歲的林彪,這些青年時代青年人該有的青春、浪漫、血性展現得淋漓盡致。如電影中毛澤東在造紙勞作中提到婦女解放時的意氣風發,拿起毛筆蘸墨揮毫,是符合其年齡性格的到位表現。人物氣質與革命氣質水乳交融,可見電影制作團隊對革命歷史的深入考究與性格藝術化的深入分析。
綜上,《古田軍號》試圖與年輕化的市場流量體系達成有機融合,在主流意識形態與市場商業化之間達到了較好的平衡。影片選用“小鮮肉”來扮演領袖毛澤東,可謂是一次大膽的嘗試。毛澤東的扮演者王仁君也被年輕觀眾稱為銀幕史上最俊美的毛澤東形象。“演員陣容上的明星化,題材與敘事上的類型化,視聽效果上的奇觀化,是主旋律電影最近幾年來在商業化道路上所主要做出的幾項嘗試。”[4]這一次年輕化嘗試有效打破觀眾對領袖特型化扮演者的審美疲勞,使之在藝術上追求神似高于形似。風華正茂的青年毛澤東激情澎湃、血氣陽剛,既有年輕人的急躁沖動,也有革命者的英勇無畏,讓熒幕前的觀眾一賞偉人青春浪漫的真性情,并為年輕群體重新定義“青春”帶來了正面深刻的影響。
三、文化創新中的符號化生產
電影影像是一種符號化的語言表達。導演往往借助符號載體來進行藝術生產,彰顯文化創新的自覺訴求。符號的構建各有不同,包括色彩符號、物質符號、地域符號等。而符號標識的差異性邏輯,導致了景觀社會的視覺認知,符號通過形象生產而生產自身。在影像中,符號消解了自身的抽象,并將自身再生產為一種符號,從而賦予符號特有的魅力。特定文化空間中表意符號的編碼,可以形成一條能引起情感共鳴的紐帶,將時代、作品、觀眾關聯在一起,正是電影藝術的魅力所在。影片《古田軍號》對符號運用十分成熟,引領觀眾通過具有特殊象征的符號編碼體味意義深遠的關鍵點。
首先,紅色主旋律的視覺化運用。紅色作為革命的象征,紅色在我國的意識形態環境里往往被賦予了神圣等意義,為避免在影像化世界里刻意表述,《古田軍號》采取了類似于美術構圖的取景角度與色彩選擇,將色彩的明暗度與革命事業的發展階段相呼應。起初電影主體色調是陳暗的,這與故事所處的歷史背景相一致,紅四軍正處于內憂外患的歷史轉折關鍵期,革命道路正在“大霧”中一步步摸索。但在電影中能經常看到一抹亮眼的紅色點綴畫面,如毛澤觀看舞龍時發出“心齊方可成龍”感慨時,連接板凳的紅色布條鮮艷明亮;又如小軍號手掛在腰間的軍號在不同的場景顏色也不同,在戰爭中是染滿鮮血的,而在“古田會議”現場則是鮮紅且干凈的——紅色在電影場景中隨著人物情節的變換切換不同的色調,它的顏色變化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
《古田軍號》專注“紅色”意象的藝術化表達,沒有在宏觀敘事上展現革命道路的曲折和軍隊的越戰越勇,而是通過紅軍戰士流血犧牲時那一抹紅色體現悲壯與英勇。如椿娃子的死,毛澤東將他抱在懷中,如古典浪漫主義油畫般的構圖,讓那血的鮮紅莊嚴肅穆、意義非凡。還有軍號上的紅穗,象征無數革命先輩用鮮血點亮前方的光明之路、叫醒世人勇于反抗,震撼人心。不經意間露出的紅旗,長鏡頭中忽明忽暗的紅色背景,不刻意不突出地表現著紅色,但在潛意識中影響著觀眾,讓紅色成為特殊的意象又不失宏大的意義,與電影敘事相輔相成,使觀眾能有更強的情感共鳴。
其次,物質符號的隱喻性營構。影片對物質符號所指涉的象征寓意也匠心獨具。故事以小軍號手的視角展開,軍號在故事開篇就被賦予重要意義,即革命啟航的象征。小軍號手的父親和哥哥都作為吹號人戰死沙場,軍號作為一種遺志的繼承從個人上升為集體,活著的人繼承烈士的斗志,聽到號角齊心協力,不畏犧牲,浴血奮戰。同時,軍號也成為了連接歷史時空的符號,其現實意義也被升華,象征紅色精神生生不息。此外,板凳的運用也頗為巧妙,舞龍的由板凳連接而成,象征著人民群眾團結凝聚在一起,也暗示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關系的變化。在影片結尾開會的場景上,剛開始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坐在各自的板凳上,到后來三人坐在了同一條凳子上,象征著革命領袖矛盾化解,思想統一。板凳作為一種象征符號生動展現了毛朱陳三人關系的變化,從一開始的分歧、爭執和分離,到最后坐在一起探索尋找黨和國家的事業和出路,確立建立黨和軍隊的正確思想,展現了他們團結一心完成時代使命的信念,體現了他們在革命摸索道路上的不易,也是軍隊團結、軍民一心,革命必將取得勝利的緣由所在。
最后,地方性形象的符號化編碼。《古田軍號》中,與“紅色”緊密相連的是福建的地域化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福建土樓,其反復出現也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福建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地域化特色。土樓是古田獨具特色的地域性建筑,是當年客家人團結起來抵御外部危險的遺產。福建土樓已然成為福建的一張燙金名片。《古田軍號》將青年毛澤東站在過去與現代的土樓前觀看舞板凳龍的鏡頭拼貼在一起,并通過毛澤東“心齊方可成龍”感慨賦予舞板凳龍新的內涵:無數板凳連接成的舞龍,象征著中國共產黨團結人民群眾心連心,也暗示著黨的強大與成就皆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中國共產黨的強大來自群眾的支持,黨的艱苦奮斗和成就也是為了人民;人民因支持黨而翻身做主人,獲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事實上,影片中呈現的舞板凳龍是福建的傳統民間文藝活動,更深層次地表明了紅軍與老百姓之間的關系是親密無間的,也象征著人民的幸福生活離不開黨的艱苦探索和不懈努力,美好生活終將會來臨,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影片的開頭和結尾都出現了新時代人民生活的鏡頭,民眾舞板凳龍,寓意真正的繁榮祥和、國泰民安已經到來,革命的付出是值得的。
《古田軍號》善于對福建地方性文化特色的符號化編碼、生產與再生產是絕非偶然的。此影片的導演陳力是福建人,她在處理革命歷史題材上具有豐富的經驗,并且致力于傳承弘揚紅色文化和傳播正能量。此次《古田軍號》的明顯突破在于對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紅色符號的守正創新,成功地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與古田人民、福建名片的土樓文化結合起來,賦予了紅色新的精神內涵和文化價值,引起了人們對“文化強旅”“科技強旅”的新思考。就在此時,第28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于2019年11月19日至23日在廈門舉辦,此后永久落戶于福建廈門,這對福建電影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因此,《古田軍號》的成功,為福建影視產業的發展探索提供了可資借鑒的重要經驗。紅色歷史成功的影像化、符號化,不僅對于講好福建故事、傳播福建形象,提升福建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促進意義,而且由此推動文化旅游新業態的形成,促成產業鏈重構,電影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都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重要路徑。
結 語
《古田軍號》作為當今我國主旋律電影的優秀作品,不僅在紅色地域化表達方面堪稱典范,而且在歷史敘事與藝術表達上取得了雙重的突破,打破了過去主旋律電影普遍存在的“與主流意識形態過于緊密的結合,連影評的形式只有一種單一的政治評判”[5]現象。影片既有歷史人物的抉擇,也有普通人物的奉獻和犧牲,偉大源于平凡,通過豐富細膩的主體情感營造和可感真實的細節把握,較好地消解了那種“因為這是一部主旋律‘紅色電影就心生抵觸”的負面觀影現象。《古田軍號》為主旋律電影樹立了時代的新標桿,在主流意識形態、文本創作、歷史考究、藝術理想、市場需求等方面達到了一種近乎完美的平衡,讓我們看到了一部求真、融合的紅色歷史題材影片。傳統的福建土樓在其中被賦予的紅色意義煥發出了新活力,舞板凳龍這一民俗活動在影片中得到了新的詮釋,成為象征地域性特色的紅色符號,也是特色鮮明的福建文化名片。作為紅色福建符號化的視覺影像藝術,《古田軍號》背后潛藏的對福建形象、對中國電影產業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具有重要的文化創新意義。在當下的產業、科技背景下,這種文化創新實踐更能讓人意識到,主旋律電影與地域性結合,可以催生出文化創新發展的新業態和新模式,昭示出不可限量的新動能,值得人們重視。
參考文獻:
[1]王一川.《古田軍號》:今昔對視中的微宏敘事[J].電影藝術,2019(5).
[2]胡智鋒,陳寅.《古田軍號》:歷史真實的藝術創新與審美表達[J].當代電影,2019(8).
[3]虞吉.“國營電影廠新片展覽月”:新中國電影文化模式與敘事范式的創生[J].文藝研究,2014(3).
[4]路春艷,王占利.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與商業電影的主旋律化[J].當代電影,2013(8).
[5]章柏青.中國電影批評:反思中前進[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1).
作者簡介:賴寧娜,華僑大學文學院本科生;蘇文健,華僑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電影批評、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