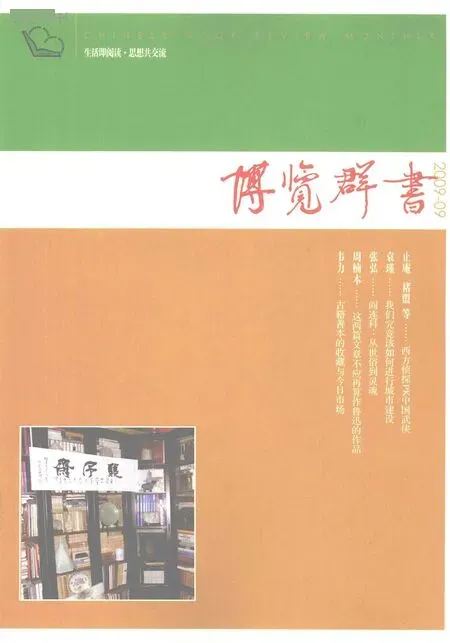詩教與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
馬奔騰
中國詩教傳統源遠流長,它至少肇始于西周時期,歷經周公、孔子、孟子及后世政府和士人的提倡、發展,內蘊日益豐富,相關理念存在于《尚書》《左傳》《論語》《孟子》《周禮》《禮記》《毛傳》《鄭箋》以至后來的《文心雕龍》《詩集傳》《滄浪詩話》等大量的著作之中。詩教思想滲透到社會文化的每一個方面,它在文藝創作和批評,以及大眾教育、倫理建構、人才選拔等諸多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而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基本風貌。中國文學藝術體式、內容與表現的特色,為詩教所決定,如章學誠《文史通義》中言:“后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其源多出于《詩》教。”認識中國的文藝問題,就必須了解和研究詩教傳統。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思想來看,中華民族文明史所孕育的文學藝術、詩教傳統自然也是其重要源頭。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以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毛澤東《講話》)中說:“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他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也說:“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毛澤東《講話》和2014年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習近平《講話》)是體現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我們可以這兩個《講話》為例,初步認識詩教傳統對共產黨文藝思想的深刻影響。
強調文藝的社會功能
重視文藝的社會功能是中國傳統詩教的核心理念。自先秦時起,人們即已明確認識到文藝的社會價值,《尚書》中即記載了上古時期中國社會重視詩教、樂教、禮教的情況,而《周禮》記錄了周代與詩教相關的官職有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等超過20種。在《論語》中,孔子對詩的作用作了全面的概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至傳為子夏所作的《詩大序》又提出詩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早期以詩歌為代表的創作,并非以審美為主要追求,其目的首先在于社會生活。如《詩經》中的絕大多數篇章,皆有明確的現實指向,毛公解詩說《行露》篇言“召伯聽訟”、《綢繆》篇言“刺晉亂也”等,都可以找到現實的印證;屈原的《離騷》等作品,綺麗瑰奇的表象之下,主要為抒發報國無門的悲憤情懷,其內在精神與《詩經》仍然相通。自西漢,《詩經》作為五經之一上升到國家政治的層面立于學官,自此詩教成為傳統文藝的價值依托。詩教影響所及,并不僅限于詩歌,而是囊括了廣義的文學藝術。浸潤于傳統詩教之中,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精神成為文學藝術持久的特色。文藝發展至近現代依然如此,如梁啟超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魯迅為改變國民精神而棄醫從文。因為文藝重視發揮社會功能的這一傳統,中國文化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常和文藝的內容與形式問題緊密相關,如唐代中期韓愈、柳宗元等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導的“新樂府運動”,均針對當時文藝創作中存在的偏于形式技巧而背離了補察時政詩教傳統的傾向而發。毛澤東、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烈的現實關切,與傳統詩教思想一脈相承。
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文藝的社會作用,重視文藝在教育大眾、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等方面的價值。毛澤東《講話》中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他的目的在于“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他認為“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澤東的詩詞均為反映革命斗爭或社會事件的作品,有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現實意義,是發揮文藝社會功能的典型。
習近平在《講話》中認為文藝和文藝工作者可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可以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強大精神支撐。他闡述了文學藝術在國際交往、國民教育等諸多方面的積極意義。他說“中華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響,不是靠窮兵黷武,不是靠對外擴張,而是靠中華文化的強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一方面,不重武力,而重德性、重感召,這正體現了詩教傳統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品格。《尚書·舜典》中記載了先民詩樂舞一體化的教育所要達到的效果就是“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重視對人德行的培養;《禮記》中也記有孔子的話:“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另一方面,以帶有傳統詩教精神的文藝作品作為交往的手段,往往可以達到以文化人的效果,如習近平《講話》引《論語》中的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習近平《講話》認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其中還引用了劉勰《文心雕龍》里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來加以說明。文藝反映時代的變化,這是傳統詩教的一個基本觀念。早在《詩大序》中就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劉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之語,理論源頭正在于此。因此文藝對社會風氣的引領、對民族精神的建設,歷來都起著巨大作用。當前我們的文藝領域出現了許多問題,如習近平《講話》中所列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等,嚴重扭曲了文藝的特性與功用,此類文藝作品既不能反映時代的風貌,更不是時代前進的號角。面對這些問題,傳統詩教文化無疑是可以利用的有力武器。習近平《講話》引用了白居易《與元九書》中的名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的一個主要內容即在于反對“嘲風雪、弄花草”之作,要求作品能“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白居易《新樂府序》中“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傳達的也是同樣的創作思想。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對普通民眾的深切關懷,是傳統詩教的又一個重要理念,從兩篇《講話》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對這一詩教理念的繼承。
為人民而創作,是我們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一以貫之的根本原則。毛澤東在《講話》中引用了列寧的話:“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他還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習近平《講話》所談的第三個問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他還引用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歷任領導人的相關話語加以強調,并引用從遠古的《彈歌》《詩經》中的《采薇》《關雎》、屈原的《天問》到北朝民歌《木蘭詩》以及杜甫、李紳、鄭板橋諸人的詩句,有力地闡明:那些久傳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滿著對人民命運的悲憫、對人民悲歡的關切,都是在人民生活中產生的。中國文藝發展史上也曾多次出現遠離大眾、偏于技巧或狹隘私情的創作傾向,如六朝時的艷體詩、中唐時大歷十才子的創作、明代前后七子的擬古作品,但在內蘊深厚的詩教傳統中,這些傾向均得到反撥、未成主流。至于歷史上有些奸佞之徒背棄人民和國家,如秦檜、蔡京之屬,即使頗有才華,其作品也為大眾所唾棄,甚而徹底湮沒于無情的時光之流。傳統詩教為生民立命的情懷,使中華民族的無數文藝作品厚重、深刻、充滿活力,也使文藝成為反映人民心聲的有效途徑。
與此問題相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還要正確處理歌頌光明與揭露丑惡之間的關系問題。社會向前發展,不斷面臨新的挑戰,出現丑惡現象在所難免,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是如此。文藝要立足大眾、關注民生,就必然需要面對這些現象,問題的實質在于以什么樣的態度去面對。毛澤東《講話》中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習近平《講話》說:“對這些現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決好如何反映的問題”,因為“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那么要以怎樣的方式來創作呢?首先要解決立場的問題。毛澤東《講話》中說:“在為工農兵和怎樣為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后,其他的問題,例如,寫光明和寫黑暗的問題,團結問題等,便都一齊解決了。”習近平《講話》中也要求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同在”。其次要解決表現方式問題。習近平《講話》引用了《論語》中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大序》中的“發乎情,止乎禮義”來加以說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乎情,止乎禮義”是《詩經》中詩篇的表現特點,它們也是傳統詩教所極力倡導的,為中國歷代文藝反映社會問題的基本方式。傳統文藝作品擅長以“美刺”“諷喻”的方法,以“溫柔敦厚”的情懷展現民生疾苦和政治陰暗面,讓讀者既感受到人民的呼聲,又能在審美的陶冶中思考問題的實質。這也是古代文藝創作中比、興手法興盛的原因之一。以史鑒今,文藝創作不應極端化地打擊人的精神,使人遁入黑暗之中,更不應激化社會矛盾帶來民生的災難,所以習近平《講話》中主張文藝“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
重視文藝在核心價值觀建設中的作用
自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刪訂六經、漢武帝獨尊儒術,中華民族漸漸形成具有強大感化力和融合力的價值觀念,這觀念以儒家思想為根本,立仁尊禮,倡忠孝節義,締造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創造力。所以習近平《講話》中說,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而詩教是傳統價值觀念得以傳承和發展的基石。《詩經》長期為社會文化教育的基本經典,甚至如白居易言:“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詩教以詩性文化為直接對象,注重以情感人、化理入情,并且詩教與六經以至后來的十三經中其他經典的教育相融相生、并行不悖,因而歷來在價值觀的塑造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
傳統的文藝創作受到詩教文化的深刻浸染。對于古代士人來說,這種詩教的影響,早在童蒙時期即已開始,后經血緣親族的教化、人才薦舉和科舉考試內容的強化,以及國家宣傳與獎懲的引導,遂滲透入靈魂之中,與血肉之軀和諧為一個整體。古代的文藝作品,縱然也會受佛、道等不同思想的影響,但總體而言其核心價值是清晰的、明確的。正如魏國曹丕《典論》言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南朝劉勰《文心雕龍》以《原道》《征圣》《宗經》開篇,明初高明在《琵琶記》中說“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這種普遍的社會責任感和家國情懷實乃相近價值觀引領下水到渠成的事情。因而中國傳統文藝中充滿高尚情操與昂揚精神的作品層出不窮。至如在國家危難之際,文人在創作與行為中所表現的勇猛和氣節,又注入了民族的血液與骨骼,成為民族永續的至深動力。而相關作品,自然成為不朽的經典。所以習近平《講話》中稱許了范仲淹、陸游、文天祥、林則徐等人的詩文,并引用了清代李漁的話:“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
有鑒于文藝在價值觀養成方面的巨大作用,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利用文藝來培育價值觀、形成凝聚力。毛澤東《講話》指出工農兵“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于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斗爭”。習近平《講話》中說“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
另外,在對文藝創作規律的重視上,兩篇《講話》都體現著與傳統詩教精神的相通。毛澤東《講話》中說:“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指出:“要堅守文藝的審美理想、保持文藝的獨立價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所以中國共產黨絕不是簡單地要求文藝成為政治的傳聲筒和社會任務的工具,而是尊重文藝作為一種精神創造的特殊規律。傳統的詩教觀念,也是既強調文藝的現實功用,又強調其審美的獨立性,如古以風、雅、頌、賦、比、興為《詩經》“六義”,其“賦、比、興”即為表現手法,明確有重視作品的藝術性之意。尊重文藝創作規律是文藝作品品格形成的前提。中國古代產生了很多研究文藝創作規律的著作,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皎然《詩式》、歐陽修《六一詩話》、嚴羽《滄浪詩話》、王夫之《薑齋詩話》等。這種對文藝自身規律的重視,使無數文藝作品既有豐厚的內涵,又富有意境、充滿神韻。
總的來說,兩篇《講話》都對中國詩教的優秀成分進行了繼承和發揚,只是在具體的態度上,二者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毛澤東發表《講話》的1942年正值抗日戰爭處于關鍵時刻,敵我矛盾尖銳,因此《講話》的目標指向非常清晰,要求文藝服務于現實的斗爭需要,其中對傳統詩教觀念的體現,更多地是潛移默化于行文之中,體現為一種內容上的邏輯。這種對待傳統文藝的態度,可以從毛澤東自身的文藝修養以及其他許多關于傳統文化的論述中得到佐證,他還提出了著名的“古為今用”原則。而現在中國共產黨早已由革命的階段進入到建設國家的階段,面臨的形勢與任務與前比已有較大不同,所以對文藝的認知也在與時俱進。正如吳良鏞先生所言:“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都是從總結自己的遺產開始的。”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在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偉大復興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強化對傳統文化、傳統詩教的繼承與發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習近平《講話》清晰體現了這種繼承關系,其《講話》中與傳統文藝相關的詩文俯拾即是,直接原文引用的就有37處,僅提到篇名和作者的數量更為眾多;在對觀點的說明中,《講話》也以事理服人,中國傳統文藝創作的成果與經驗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下成為重要的理論來源。
充分認識和理解傳統詩教的智慧,及其對共產黨文藝思想的影響,對我們正確認識今日文藝存在的問題,把握未來文藝發展的方向,堅定文化自信,有著深遠的意義。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文學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