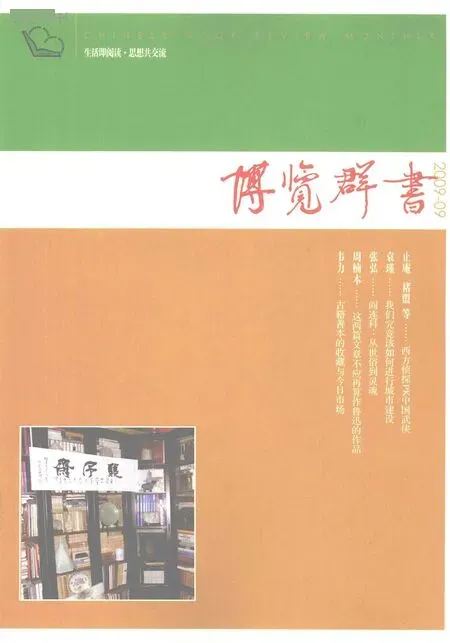寫在《走近魯迅》書外

從交稿到出版,經歷了4年的等待,拙著《走近魯迅》終于在這個多難的年份出版了。無論是疫情還是水患,無論是人禍還是天災,人類總是為生存抗爭著,正如魯迅所說:“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斗,但為的是改革。”(《論秦理齋夫人事》)
壹
我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了30多年,主要從事展覽陳列工作,關于魯迅的各種專題展覽辦過很多,有關于魯迅生平與創作的、關于魯迅讀書生活的、關于魯迅作品版本的、魯迅與同時代作家的、魯迅與美術的,等等。我對魯迅和他的作品的認識是逐漸從模糊到清晰的。此前課本中讀過的魯迅文章,完全沒有感覺。在多年的工作與研讀中,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思潮動蕩中,形成了我對魯迅的理解。魯迅是一部書,不同經歷的人會讀出他的不同面孔。
魯迅離世80多年了。80多年來,魯迅作為一種中國文化的符號,忽而擺上神壇,忽而拉下神壇,但他始終攪動著中國文化各個領域的波瀾。文學的、國學的、史學的、哲學的、美術的等領域都游動著魯迅思想的影子。以魯迅罵人的或謾罵魯迅的,選入課本的或踢出課本的,說他是什么家的或說他不是什么家的聲音也始終不絕于耳。80多年了,魯迅就在那里,任由折騰,他的影像也留在幾代人的心中,紀念魯迅的活動仍在繼續著。我常常想起蕭紅回憶魯迅的那句話——魯迅先生坐在那兒,和一個鄉下的安靜老人一樣。
貳
魯迅的公子周海嬰有一次到魯迅博物館辦事,保安不認識他,問道:“你找誰?”海嬰答道:“我找誰?這是我的家。”這話是不錯的,因為魯迅博物館是依魯迅于1924年親自購買的阜成門內西三條21號院而建的。新中國建立后,許廣平與海嬰共同把這處魯迅故居捐獻給了國家。
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人都有一種自豪感,哪怕是養花的工人,因為他們至少知道魯迅是大文豪,是被世人稱作民族魂的英雄。有一次花工向研究室的先生們請教,為什么魯迅要寫“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聽過解答后,花工端然拱手道:“謝謝!改日向您賜教。”研究室的先生們哈哈大笑。這故事說明花工文化不高,但對于知識,他們還是渴望的。
有一次,一個書商和我談編書的選題事,我建議:“現在魯迅的書很暢銷的,可以編一本適合青年閱讀的插圖本魯迅選集。”書商問道:“魯迅是誰?他的書煽情不?”弄得我無語。
以上是我經歷的的幾則真實的小故事。這些故事也說明,今天讀魯迅的人并不普遍,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魯迅的泛政治化的因素的退潮;其二是時代觀念的負面影響;其三是魯迅研究的大量文章越來越艱澀難懂,缺乏普及性、接地氣的作品。這些都是后來引起我寫魯迅故事的緣起。
叁
在北京話里,把會講故事的人稱為“故事簍子”。魯迅就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故事簍子”。因為他幾乎讀過十三經,熟通二十四史,又廣泛搜求野史雜說,寫過前無古人的中國小說史,對東西方的文學、史學、哲學、美術等都廣為涉獵,由于他的博覽群書,于是,他成了“故事簍子”。其實,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個個故事的連綴,人生不能沒有故事。沒有故事的生活是乏味的生活,沒有故事的藝術是蒼白的藝術,沒有故事的音樂是缺乏感情的音樂。故事能感染現實的人們,能讓人記住過去、記住愛、記住恨、反思過去、汲取生活營養并啟示未來。理想是從故事生發的。這本魯迅故事不是傳奇,故事是真實的,傳奇則有虛構。

魯迅身后的傳記,算起來已出版50多種,不同時期魯迅傳記的內容也不盡相同,作者的視角也不盡相同,寫作手法也不盡相同。這本書不是一本研究魯迅的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書,而是300個魯迅的故事。其中有魯迅講述的故事、魯迅同時代人回憶魯迅的故事以及魯迅身后的故事,還有作者的一些零星雜感。這些故事是魯迅的300個人生片斷,將它們連綴起來也是一種故事文體的魯迅傳記。雖說是故事,但都不是虛構的故事,都是依據真實可靠的史料構成的真實故事,還原一個活生生的肉身之魯迅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狀態,站在讀者的角度把魯迅講述給讀者。這300個故事并不能全部概括魯迅一生的每一個細節,但故事的細節卻會讓讀者更貼近魯迅的人生。這故事是魯迅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也是他的嬉笑怒罵、談古論今;也是我的。
肆
近年來,魯迅被邊緣化的假命題似乎很是流行,而這流言的濫殤常常來自魯迅研究界。但凡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會知道,金子總是金子,不管怎樣聒噪,魯迅仍然是20世紀最具啟迪意義的思想家,最具品格的文學家和最博學并包的學者。作家莫言曾說:“我愿意用我全部作品‘換魯迅的一個短篇小說。”畫家吳冠中也說過:“一百個齊白石也抵不過一個魯迅。”可見魯迅作品的歷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近年來圍繞中學課本中“去魯迅化”的思潮有很多討論,查看今年的初高中教材,魯迅作品確實少了,這關系到中國的未來,因為對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少了,對丑惡的現象批判少了,優秀的語言文字也少了。這是非常令人堪憂的現象。
魯迅的生前死后,對魯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經有100多年,關于他的研究著作也浩如煙海,主要集中在魯迅思想、小說、雜文、翻譯等方面。無疑,魯迅研究的專業學者們對作為思想文化資源的魯迅,有著豐碩的研究成果。魯迅做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被學習、被研究、被作為思想的利器而被尊崇。魯迅留給世人的,不止是他的文字,作為人之子的魯迅,主張立人為本,崇尚自由與愛,他具有普通人一樣的肉身。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魯迅研究是一門廣為社會關注的顯學。我在魯迅博物館工作了30年,因工作關系與個人的喜好,30年讀魯迅的原著基本沒有中斷過。研究魯迅的書出的越來越多,讀也讀不過來,許多的研究論文根本讀不進去,甚至也讀不懂了。時下論文中的“體系”“結構”“解構”“架構”“維度”“層面”“視野”等一定不是給大眾看的,用白話文作文章似乎已經不時尚了。還有一些研究,諸如兄弟之情就扯上弗洛依德,文學論爭就是你死我活,這恐怕也是魯迅厭惡的研究方式。個人看來,研究魯迅左的或右的或過度的解讀都不是正確的研究心態。所有的研究都不如讀魯迅的原著來得過癮。所以不如少研究,多讀書。讀魯迅,要讀原著,原著,還是原著。
畢竟,《魯迅全集》數百萬字,不是專業研究者,不一定就能讀下去,尤其是開篇就是幾篇文言文章,一般讀者,恐怕會被嚇住,太難懂了吧。即使是白話文,魯迅的時代與現今的白話文也存在閱讀上的障礙。所以讀懂魯迅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需要專業研究者們做出一定的努力,為大眾讀者做普及性的文字,才能使今天的年輕人產生閱讀魯迅的興趣。
關于讀書,魯迅在《讀書雜談》中曾這樣談起嗜好的讀書:
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系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后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于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魯迅強調讀書的趣味,由此“擴大精神,增加智識”。魯迅本就是一個有趣之人,如陳丹青講魯迅的有趣:
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長得和他們不一樣,這張臉非常不賣賬,又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里卻透著風流與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對著鏡頭,意思是說:怎么樣!我就是這樣!
伍
垂暮之年,完成了這本書的寫作。我曾出版的三部拙著:《魯迅美術年譜》有較強的資料性,也可以說是一本工具書;《魯迅的書法藝術》有較多的專業學術性;《魯迅與他的北京》資料性與文學性兼而有之。這本《走近魯迅》,因為是寫給年輕人看的,在史料確鑿的前題下注重文學性,從閱讀魯迅的故事走進魯迅的世界。這也是對我嘗試各種文體的寫作是一種挑戰,也是對自我的挑戰。這本書從我在魯迅博物館在職時開手,到在老北大紅樓中解甲歸田時結束,斷斷續續寫了3年。之所以拖延了時間,是因為用了很大的精力沉迷書法,這中間還寫了一本《魯迅與他的北京》。寫作本書的起因是年輕的小友們經常要我講魯迅的逸聞趣事。講故事能使人年輕,因為要眉飛色舞,而講魯迅的故事,確是能夠眉飛色舞的。于是我想,好吧,就寫一本魯迅的故事吧,讓更多的喜愛魯迅的年輕人來聽。書的內容較多的寫到魯迅和他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社會變革的影響等,讓讀者從另一個側面了解魯迅的生命軌跡,從而能折射他思想、文字的形成因素。
魯迅把中國的歷史用兩句話來概括: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并期望“第三樣時代”的到來。這“第三樣時代”是什么?魯迅沒有說,那應該是沒有奴隸的和“人立而凡事舉”的時代吧。魯迅一生的故事表明,他一生其實都在為實現這樣的時代而努力著。
人生的樂趣在于創造,人生的意義大約也在于創造。創造之于文學,便是寫作,寫作的歡愉來自于愛。魯迅推崇日本作家有島武郞的創作觀,他在《現代日本小說集》附錄中寫到有島武郞對自己的創作要求:“第一,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第二,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第四,我又因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魯迅也說:
“人感到寂寞時, 會創作;一感到干凈時, 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于愛。”
這部故事型的小書,來自于魯迅之愛與對魯迅之愛。
企盼讓愛傳播。
(作者簡介:肖振鳴,筆名蕭振鳴,魯迅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