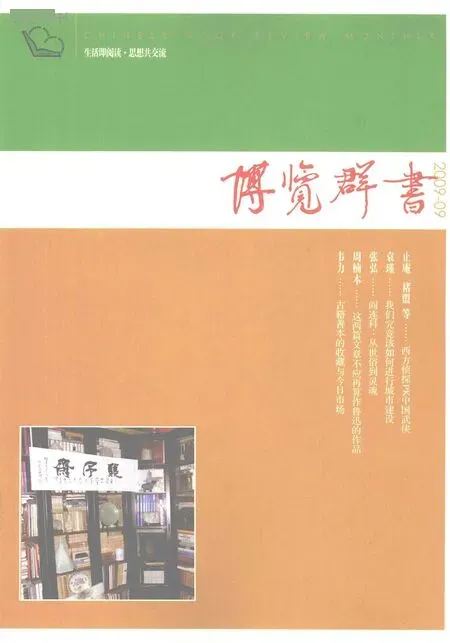李白與他所傾心的月亮
白彬彬
作為距離地球最近的天體,月亮與地球如影隨形,關系密切。當夜深人靜之時,一輪皎潔的圓月悄然升起,灑下清輝,映照著地球上的山川河流、千門萬戶。而在中國,月亮與生活在其間的人們關系似乎尤其親密,它是朋友,是親人,是戀人,甚至是另一個自己……事實上,正如美學家潘知常先生在《眾妙之門——中國美感心態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所言:
中國人那根極輕妙,極高雅而又極為敏感的心弦,每每被溫潤晶瑩流光迷離的月色輕輕撥響。一切的煩惱郁悶,一切的歡欣愉快,一切的人世憂患,一切的生死離別,仿佛往往是被月光無端地招惹出來的,而人們種種飄渺幽約的心境,不但能夠假月相證,而且能夠在溫婉宜人的月世界中有響斯應。
可以說,一輪皓月,見證了中國人最純潔明澈的詩思。
在中國古代的詩人中間,若要問誰對月亮最為傾心,李白應是無可爭議的不二人選。據統計,在李白的詩歌中,提到月亮的詩句不下三百處。李白曾寫下很多首流傳后世的關于月亮的光輝詩篇,《古朗月行》《靜夜思》《關山月》《峨眉山月歌》《把酒問月》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李白筆下寫月的名句更是俯拾即是,如“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渡荊門送別》),“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關山月》),“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玉階怨》),“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子夜吳歌》),“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等。甚至關于李白之死,民間都流傳著一個美麗的“李白醉月”的故事。傳說,李白晚年流落在當涂,有一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乘著酒意泛舟長江。此時,一輪皓月當空,滿江水色如銀,酒醉的詩人為眼前美景所陶醉,伸手去碰觸水中的月影,卻飄飄然落入水中,與明月、清輝融為一體。大概是人們知道李白太喜歡月了吧,所以才為詩仙安排了這樣一個美妙而又浪漫的結局。
太白筆下的月姿態萬千,具有十分豐富的審美內涵和象征意義,透露出強烈的生命感受和情感體驗。如《古朗月行》: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又疑瑤臺鏡,飛在白云端。
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團。
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
整首詩以兒童稚嫩的口吻寫就,似脫口而出,毫無羈絆,充滿了新鮮感。詩人以“白玉盤”“瑤臺鏡”作喻,生動地表現出月亮的形狀和月光的皎潔,使人感到非常新穎有趣。“呼”與“疑”兩個動詞,則準確傳達出兒童天真爛漫之情態,惟妙惟肖。“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四句,將眼前一輪明月與古代的神話傳說聯系在一起,既寫出了月亮初生時逐漸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又發問新奇,準確切合了兒童的身份。
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李白迎來了意氣風發的青年,而一首《峨眉山月歌》則將初次出蜀時太白對家鄉的思念寫得格外情致深婉:
峨眉山月半輪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
此詩最為人稱道者,在于四句之中連用五個地名,卻自然渾成,毫無堆垛之感。如顧嗣立在《寒廳詩話》中所言:
四明周屺公斯盛曰: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中連用峨眉、平羌、清溪、三峽、渝州五地名,絕無痕跡,豈非天才!
那半輪升起于峨眉山顛的上弦月,將皎潔的清輝灑向大地山川,似乎是一位多情的友人,在送別年輕的詩人離開家鄉,開啟闖蕩世界的旅程。它將月影映照到清澈的江面上,隨著李白一路漂流而下,也安慰著詩人那顆隱隱不安的內心。
關于此詩末句中的“君”所指為何,歷史上曾有過爭論,如朱諫在《李詩選注》中言:“所謂‘君者,其姓名不著,不知為何如人也。”顯然認為指的是太白的某位友人。而沈德潛、黃叔燦等人認為此處“君”指的是詩題中的“峨眉山月”。從全詩內容來看,私以為還是理解為峨眉山月更符合當時情境。詩中所詠乃是上弦月,上弦月升起得早落得也早,故而夜深時分已經隱沒不見,加之舟行峽中,兩岸皆峭壁層巒,山勢愈高,江水愈狹,詩人再望時那半輪峨眉山月已經難覓其蹤,于是心中不免平添了一份“思君不見”的惆悵與感傷。將空中的月亮徑直換作“君”,正可見李白對于月之親近。
月亮是昭然于天際凝然不動的鄉愁,而一首《靜夜思》,更是太白望月思鄉的絕唱,成為了億萬中國人的思鄉曲: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清人徐增在《而庵說唐詩》中分析此詩曰:
客中無事之夜,忽見一片之光。寒月色白,故疑是霜,意以為天曉矣。乃舉頭上望,見月之方高,始知其月光。首句是光,此句是月。見窗前光是無意,望月是有心。月方高,正在夜中,床前雪白,性急又睡不去,始知身在他鄉,故“低頭思故鄉”也。因疑則望,因望則思,并無他念,真“靜夜思”也。
詩人對故鄉的思念之情久蓄于胸中,因為床前的皎潔月光而被觸發,并且一發而不可收拾,在此月光成為詩人情感的催化劑。由“看月”而“疑霜”,由“疑霜”而“望月”,由“望月”而“思鄉”,詩人的心理與行動,始終與那一片皎潔的月光緊緊聯系在一起。
月亮不僅是高懸于天際夜夜升起的鄉愁,還是詩人心系友人綻放在玉壺里的一片冰心,在聽聞摯友王昌齡因事被貶之后,李白寫下了流傳千古的《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河岳英靈集》謂王昌齡“晚節不矜細行,謗議沸騰,再歷遐荒”。太白聞友人左遷龍標,遙寄此詩。“楊花落盡子規啼”所寫為暮春景象,目之所見為楊花落盡,耳之所聞為子規哀啼,詩人之心情已可想見。正在此愁苦之際,又得到友人遠謫的消息,沉郁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無奈此時友人已經踏上貶所,遠在五溪之外的蠻荒之地,詩人無法當面送上安慰,只好就眼前的一輪明月而設想:就讓我把滿懷的愁心托付給明月吧,讓它隨著長風一直吹送到夜郎之西友人的貶所。在此,明月化身成了詩人的信使,負責把詩人的牽掛與關切傳遞到友人那里。
從構思上看,“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二句或是受到三國曹植“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愿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等句的影響。但李白寄愁心與明月,別具一種明朗、飄逸之感,也使得愁苦的情緒在皎潔如水的月光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稀釋,仿佛友人可以挹皎月而知故人之懷也。
屈原在《天問》中發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月亮的圓缺引發了世人對于永恒和短暫的深沉思索,牽引出宇宙無窮、人生有限的喟然長嘆。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感慨如前響未歇,李白《把酒問月》的追問則如后音已繼。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
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
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云間沒。
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里。
此詩題下有自注:“故人賈醇令予問之。”朱諫《李詩選注》卷十一曰:“時白在長安,故人賈醇相與對月把酒,令白作詩以問月。”這位賈醇的生平事跡如今已不可考,但他真不愧是太白的知己,或許他知道,“把酒問月”這樣的事情,只有愛酒且愛月的李白才能做到,也多虧了他的這一次看似“無禮”的要求,才有了太白這首想落天外的奇篇。為此,我們要鄭重地感謝他。
“青天有月來幾時”,首句的劈頭一問,問得突然,問得新奇。“人攀明月”二句,乃就月與人之關系而言,在詩人的心目中,那一輪明月既高不可攀,又如影隨形,詩人對月亮那種既仰慕又親切的情感自然地流露了出來。“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二句則寫月臨中天、光照人間之動人景色,“飛鏡”就其形而言,“綠煙滅盡清輝發”描摹月光之皎潔純凈,細致入微,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但見”“寧知”二句,就月亮的運行發問,饒有趣味。宋代大詞人辛棄疾或許是受此啟發,將太白此問敷衍成《木蘭花慢》詞:
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系?姮娥不嫁誰留?
謂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愁。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殿瓊樓。蝦蟆故堪浴水,問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
稼軒在此接連拋出七個關于月亮的問題,可謂“踵其事而增華”。接下來的“白兔”二句,轉就與月有關的兩個神話發問,滿含著對神秘月亮的好奇。“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是此詩中流傳最廣的名句,語言雖質樸,卻蘊含著十分深刻的哲理。詩人面對一輪圓月,引起出一番對于人生哲理的思考。揆之于理,今月古月實為同一輪,而今人古人則不斷更迭。李白這里說“今人不見古時月”,背后隱藏著“古人不見今時月”之意;說“今月曾經照古人”,也隱藏著“古月依然照今人”的意思。此二句造語備極重復、錯綜、回環之美,且有互文之妙。“唯愿”二句乃是就月亮之永恒與人生之短暫而發,與《將近酒》中“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同一機杼。
皎月橫陳,普照乾坤。既然月亮成為永恒的象征物,那它便成為了世事滄海桑田、人間喜怒哀樂的見證人。站在“曾經照古人”的月光下,一種思古之幽情如月光一樣自然流淌,《蘇臺覽古》即是太白以月為證鑒照古今的代表作: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里人。
蘇臺即姑蘇臺,故址在今江蘇省蘇州市西南姑蘇山上,相傳為吳王闔閭所筑,其子夫差增建。夫差曾與西施及宮女們在此作長夜之飲,李白有《烏棲曲》專詠此事。昔日歌舞繁華之地,隨著人世的變遷,如今早已是人去臺空,詩人到此只看到“舊苑荒臺”的一片廢墟,以及周圍的青青柳色。當年的姑蘇臺上,歌舞追歡,夜以繼日,何其熱鬧!現如今,歌聲舞影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女子采菱時唱的婉轉清亮的民歌還在回蕩。以上是變化的事物,而亙古不變的則是西江上的那一輪圓月,它曾映照著昔日繁華熱鬧的蘇臺,也映照著如今的舊苑荒臺;曾照臨西施等“吳王宮里人”,也照臨著如今的采菱女子。西江月以其亙古不變的自然屬性,在此成為歷史變遷的見證者。“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詩人對歷史興衰、人世滄桑的思索全部凝結于那片燦爛的月光之下。
作為“謫仙人”,太白在人世總不免孤獨,而這時,能陪伴慰藉他的,除了葡萄美酒,就是皎潔月光了。于是在某個月夜,孤獨的李白提筆寫下了《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
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其一)
詩題曰“月下獨酌”,正可見孤獨之意。然太白本非常人,當此之時卻突發奇想,何不舉杯邀請天上的明月同飲呢?這樣再加上月下自己的影子,剛才還孑然一身,轉眼就變成了三人,氣氛一下子熱鬧起來。然而這熱鬧畢竟是虛幻出來的,雖是三人,月卻不能陪我飲酒,影子也只是徒然隨身。短暫的熱鬧,轉瞬之間又被清醒的認識所打破。但李白畢竟是李白,雖然有遺憾與失望,他卻能夠很快地化解,詩人把遺憾與失望拋諸腦后,在月與影的陪伴下起舞歌唱。醒時且盡情歡樂,醉后便各自分散,詩人在篇終更與月與影約定,彼此結成永遠的朋友,一起在天漢云霄之上遨游。在此,與其說月是李白的知己,毋寧說月就是李白自己的化身。
詩人余光中在《尋李白》中說:“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在詩仙李白筆下,一輪明月圓缺盈虧,見證著歷史的興衰榮枯、人間的聚散離別,也在詩人心頭投下永恒的光輝。那皎潔的月色照徹古今,成為中國文化中最迷人的符號之一。
(作者系文學博士,商務印書館編輯。)